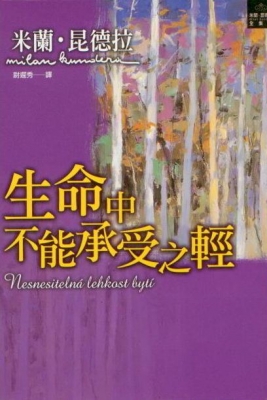愛情常態|荊棘的征途──柯姆.托賓《布魯克林》及其改編電影《愛在他鄉》
等光與影都成為果子時,
你便怦然憶起昨日了。──周夢蝶〈樹〉
愛爾蘭的年輕女孩移居紐約布魯克林,繫掛兩片土地在自己身上。從沒想過的鄉愁、死別、情愛糾葛,剽悍地冒出芽來,盤踞原來的一片空無。成長並非渴盼自由的野火燒盡蔓生的雜枝,而是匍伏荊棘之中每一次迴身承接刺痛,不再懷疑生命的坦白。
坦白這一路的追尋沒有盡頭沒有一刻不索求承擔。承擔什麼?承擔生命的光燦和暗影紛紛熟成,構成自己的一切才將猛烈浮現,被重新記起,被重新指認。柯姆.托賓的小說最迷人之處在於精細鏤刻女性從沒停止的自我反詰、自我推斷、自我否定、自我妥協……;進退維谷,她們拓出一個辯證的空間,學習承擔自由、承擔責任、承擔荊棘的征途。
她們難以察覺,多重擺盪之際,鮮明的自我已然浮現。翻開《布魯克林》的任一段落,盡是女孩的反覆思量,譬如離家前的深夜,她想,「如果是另一個人打開行李箱,穿上那些衣服和鞋子,她會更開心。一切的安排,如果有另一個女孩來應付會更好。」她情願每天早上在自己的床上醒來,在熟悉的街道走動,每個晚上回到母親和姊姊身旁。
「即使她讓這些想法飛快運行,但她還是逼迫它們停下,告訴自己要面對真正的恐懼或疑懼,接受自己即將永遠失去眼前的一切。」從自身的畏怯思及家人的顧慮,她知道「家裡的悲傷已經積累太多太深了,甚至遠超過她能理解的程度。她將不再為它添加任何痛楚與哀傷。」遠渡重洋之前,她決心不讓家人流下一滴眼淚。她要留下,她的笑容。
《布魯克林》及其改編電影《愛在他鄉》同樣戮力呈現 1950 年代那個揹負經濟壓力而移民求生的愛爾蘭女性樣貌,識清人際的牽累,維繫和諧的群己關係。即使《愛在他鄉》的劇情結構和敘事節奏近似原著,仍舊突顯了影像無法企及文字探究心理活動的媒介差異。當小說進行綿密迂迴的精神描繪,電影僅能梗概帶過「我無法買一個未來給妳」、「在這個國家,母親總是被丟下」這種直白的憾恨。然而,兩者揭示的女性自覺並非突破社會文化的侷限,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地持守進退轉圜的分寸,體貼地回應那些親疏有別的人們,最大限度地放掉自我,最大限度地守護安穩秩序。
這樣的一種愛,源於自我不斷在此境和彼方擺盪:在布魯克林掛念愛爾蘭的一切,在愛爾蘭掛念布魯克林的一切。《愛在他鄉》透過電影獨有的抒情手法進行影像和聲音分離的雙向敘事,同步展現了女孩的道德掙扎和情感衝突。結尾,女孩再度離開家鄉,來到布魯克林,擁抱她的丈夫。她的心聲成為畫外音:「你會找到一個屬於你的人,那就是你的安身之地。」而小說最後,女孩搭上離家的火車,想像那個匆匆被自己拋下的男孩追到家中,母親開門,「眼底的神情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哀傷,但卻充滿了無比的勇氣與驕傲。」她想像母親告訴男孩:「她已經回布魯克林了。」她知道,當母親的那句話對那男孩的意義漸漸流失,同一句話卻對她顯得刻骨銘心。「想到這一點,她幾乎微笑了,然後她閉上雙眼,再也不多想了。」
從電影和原著小說的最後一個句子來看,這也就是《愛在他鄉》和《布魯克林》的真正分歧:前者相信故鄉的存在,後者深知漂泊即是命定的故鄉。如果,情感投注之處皆為故鄉,那麼,故鄉即是自身不斷瞭望、懷想的心之歸屬;因而,人們的所在必定都是他鄉,沒有一刻能夠脫離鄉愁。這種雙重視野,既是柯姆.托賓的寫作筆法,也是小說人物發展自身主體性的辯證過程──探索遙遠的異地,尋獲一個反省的間距,回頭為熟悉的故土和自己的歷史命名。最終明白,生命無法走出荊棘的征途,無法脫困,無法不再徬徨,只能安於人事離散。等待光與影都成為果實,便能怦然憶起昨日。
【愛情常態】
我不知道愛情如果不是最暴力、最羞恥、最甜蜜的勒索,它還能是什麼?
這些是我在文學、電影、戲劇、舞蹈、繪畫、音樂裡所理解到的愛情常態。
【吳俞萱】
詩人。著有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電影文集《隨地腐朽──小影迷的99封情書》、攝影詩集《沒有名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