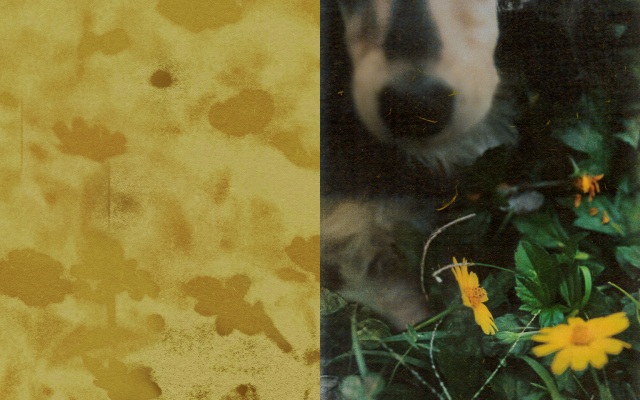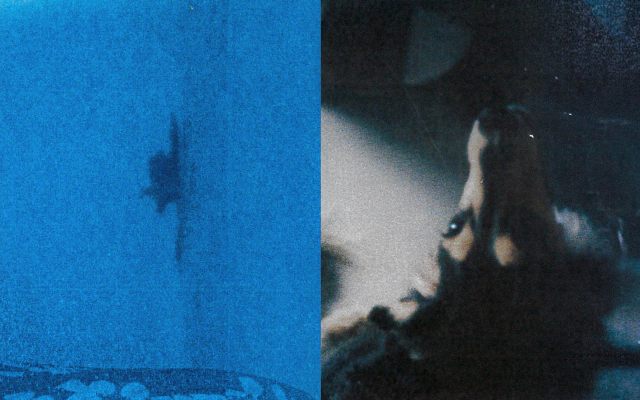#拜託已讀要回|盛浩偉讀《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文學與生命的答案,都是一場徒勞?
在我們既定的認知裡,似乎總容易將「嚴肅」和「娛樂」切割開來,就像是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對立,或菁英文化與流行文化的對立一樣,彷彿,只要通俗又受歡迎,就一定缺乏深刻思想;事實上絕非如此。嚴肅又帶有娛樂性的作品確實少見,但少見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兩者互相抵觸,而是因為要兼顧它們並不容易。在這層意義上,東山彰良《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可說表現得相當傑出。
這本小說雅俗共賞,有精彩且千萬不能透露半點線索的劇情,所以在這篇評論裡只能暫且按下不表,但除此之外,它內含的元素也琳瑯滿目。故事主要舞台設定在八〇年代末老台北,特別是西門町、小南門一帶,以青少年那時而童稚天真時而成熟敏銳的眼光,撫觸了當時臺灣社會的風貌,也討論到本省與外省的族群議題;不過整本小說的場景卻不限定於此,在劇情副線裡,還橫跨至美國、中國,更攝入現實的事件,展現了廣闊的視野與大膽的想像力。而就內容而言,有青春成長小說的迷惘,有動作與推理等類型的緊湊懸宕,還涉及性別、性向議題,難能可貴的是,這些紛呈的元素隨著劇情的進展,在某個點上全都自然而然地融會在一起,也讓故事更加飽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這本出自旅日臺灣人之手的作品,竟遙遙地和臺灣文學史上的一個主題相互呼應。
說到九〇年代之後的臺灣文學史,總脫不了「眾聲喧嘩」一詞。這個詞自有其深刻,尤其放到歷史脈絡下來看,確實是要等到了解嚴以後,政治箝制鬆綁,沒有哪股力量能再成為主導,文學與藝術才彷彿算是獲得了完整的自由,遂頓時百花齊放。然而,如今已將近三十年後,再回頭反省這樣的文學史描述,也不免感受到這個說法的侷限:
說這個時代的文學主題什麼都有,就跟說這個時代的文學沒有主題,是一樣的——當然,這不是事實。至少,在我自己的閱讀裡,就隱約感受到一個,姑且稱之為「直子之心」的主題。
敏銳的讀者肯定已經直覺聯想到駱以軍的〈降生十二星座〉。這篇發表於九〇年代的作品,揉合電玩、星座等次文化元素,透過帶點魔幻寫實的筆法,描繪了當代人對自我存在的質疑,以及內心的迷惘虛無。小說裡,駱以軍向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致敬,挪用其人物名與情節,在遊戲「道路十六」裡設定出了一個名為「直子之心」的彩蛋。它象徵著他人之心的難以進入、難以理解,甚至就算得以進入,也只會發現一片虛無,一個彷彿隱形的主體;同時,在面對到他人內心的真相時,也不禁會令自我主體驚覺:是否我自身也是如此虛無?
這個「直子之心」主題的表層,其實是當代情境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寂寞。正因為感受到與他人的距離、感受到他人種種行為的難以理解:「為什麼他會那樣做?為什麼他要那麼做?」進而有了索尋解謎的動機;而在駱以軍那裡,這個主題走到深層的答案是:原來疏離與寂寞,都是出於每個人自身的空洞與匱乏,最終化為對存在的疑惑。此後,這個主題遂在臺灣文學或長或短的小說裡反覆出現,時而深刻,時而閃現,它又經常與他人莫名的「自殺」或「死亡」相關,近期表現得較為明顯者,例如何致和《花街樹屋》或吳明益《苦雨之地》,都將這份對他人的困惑推到了前景。
然而,這個主題似乎太必然走向虛無的結尾,畢竟,還有什麼比讓人困惑起自身存在還要虛無的事情呢?只是,文學,或說創作,人們之所以願意投身於此,難道只是為了得到一個虛無的答案?即使那確實就是生命的謎底,生命的真相。回過頭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呼應了這個主題,精巧設置了一道關於他人人心的謎,但在解謎的盡頭,敘事者終究只是徒勞,無從改變什麼。不過在這裡,故事響起了「直子之心」的變奏。在結尾,小說寫著的:
「就是這樣,為了逃避某件事,專心做另一件事,用這種方法一步一步離開那件事。」
「只有這種方法嗎?」
「嗯,只有這種方法。」
是。「即使」那確實就是生命的真相,但是文學,或說創作,不就是在面對這個答案的前提下,仍舊奮力達成那個「即使」?那看起來是逃避,實際上卻是面對餘生的方式。作品如何讓人認識到虛無卻不虛無,在這層意義上,《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不只演繹了一則精彩的故事而已。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
.jpg)
作者:東山彰良
譯者:王蘊潔
出版社:尖端
出版日期: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