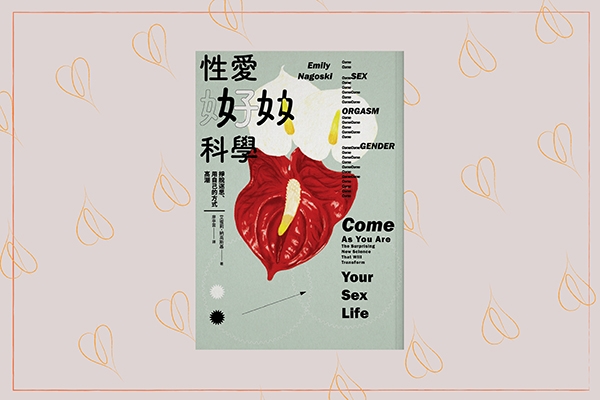背誦的身體哲學(二):
從「讀經教育」的爭議談起(下)
古人怎麼談教育?
面對反方的意見,王財貴未嘗沒有回應,但大多是一而再地重複自己的理論,將原本「有口無心,不可理解」的意思換湯不換藥,甚至湯也不換就把原本那碗再端出來。至於那些缺乏明證卻以不證自明的態度所提出的論點,他則多以口號而非論述重申立場,例如:
「我要重複地吶喊:我說的是兒童的教育!是兒童的教育!是兒童的教育!請大人們,請專家學者們,請大學教授們,要記住,你已經大人了,已經是大人了,已經是大人了!請不要以你的年齡,以你學習的特色,或以你的學問,以你面對世界的恐慌來看你的孩子!他們還小,他們還小!他們正要打基礎,他們正要打基礎!」
比較有意思的回應來自於北京千人行書院院長吳小東,他擷取經典的說法,作為支持王財貴讀經理論的證據:
「啟發教學也不能濫用,〈學記〉云:『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時觀而弗語,以存其心也』。因材施教、啟發教學其實主要適用於十幾歲以後青年階段的教育,那時真正的個性顯露,思考力開始運作,因材施教、啟發教育正當其時,在童蒙階段,其時並不需要太強調因材施教、啟發教學的。」
然而,他提出的證據看似支持「有口無心,不可理解」的立場,實際上卻正好相反。〈學記〉說的「時觀而弗語,以存其心也」是指教學者不直接給出答案,要使學生「憤憤悱悱,然後啟發」,這正與孔子所說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啟發教學」如出一轍。至於「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說的也絕非死記硬背,而是強調學生提問、老師解說的問答教育,剛巧與王財貴的立場相反。
〈學記〉明言「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因此只懂得操作複讀機或「小朋友,跟我唸」的六字真言者,絕不被儒家認同為老師,荀子更認為「入乎耳,出乎口」的學習方法最多只能稱為「小人之學」。
其實,孔子期望學生能夠「一以貫之」,在經典當中找到符合自己生命的常道,這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學無常師」、「事中磨練」的生活學習之上,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論語》開篇第一章「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並不只是一般理解的「學習了還要時時溫習」那樣,而是要我們將所學習的知識「適時地實行在生活當中」,這意味著必須以理解為基礎,同時發展出判斷情境、應用所知的實踐智慧。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則強調了與人相處、切磋琢磨的生活經驗對於所知的增長作用,這些都比王財貴的「三百讀經法」還要全面地符合人性。
王財貴自信他的理論符合人性的「全幅」與「全程」,但是對照儒家自身的說法,令人不禁懷疑他那遵循古法的理論,是否僅是一種個人的新創。事實上,王財貴所謂的人性,是一種抽離時空情境、取消個人實際生命體驗的形而上概念。他所謂的「全程性」,忽略了人性是會隨時間點滴增長改變,因此他所指的不是實際生命的總體發展,而是從他的理論推想出來的進程;他所謂的「全幅性」,也並不是參照具體生命活動的全面樣態,僅是符合他心目中削足適履過後的中國文化而已。

對於反對意見的反思
反對意見對於背誦的「材料」以及背誦的「方法本身」,都提出了看似相當合理的理由;也就是說,反對方認為有理由提出經典教育應翻譯為白話文,並且不應以背誦作為方法,至少不應作為主要或唯一的方法。
誠然,沒有理解的背誦著實令人難以信服,而語言作為理解的介質,應當以學生更為熟悉的白話文入手更為具有合理性。然而,脫離「是否讀經」或是「經典為何」的問題,單就「背誦」作為一種學習方法的意義而言,我們也不妨試著思考以下兩個問題:
1. 透過翻譯所理解的經典,與經典本身是一致的嗎?
2015 年 11 月 21 日台大電機系葉丙成教授臉書牆上的轉貼了網友將唐詩改寫成白話文的貼文,由於翻譯內容讀起來極為荒唐,非但毫無文學性可言,從題旨看更像是古人盡發一些沒內容的牢騷,因此這一系列的「翻譯改寫」便被戲稱為「古代廢文大賽」。隨後,文學評論者朱宥勳撰文提出反思,認為這樣的現象源自於文學教育的失敗,具體而言包含三點:
- 文學作品的文字操作,非常重視「歧義性」;
- 文學作品的形式和內容必須同時評估;
- 在翻譯的過程中,原文和譯文不可能百分之百等同。
文學文本的性質,在於讀者可以透過文字排列組合中意義解讀的多元可能性,去領略其中的美感與意涵的魔法,以及聲音、節奏和語氣等形式因素對於讀者感受內容的影響,還有表面上指稱相同或類似的概念的詞彙,指涉的範圍並不盡然相同。
「古代廢文大賽」所引起的反思,在於鬆動詞彙與概念之間簡單乾淨的對應關係。當我們將古典詩詞、散文改寫成足以表達相同概念的篇章時,雖然「讀得懂」,但很可能已經與躲藏在字裡行間那不可替代的美感與意義的歧義性擦肩而過了。雖然朱宥勳討論的對象是文學,然而,姑且不說經典當中也包含文學,即便是傳達哲理的文本,同樣也逃不了翻譯過後就變形的下場。因此,能夠翻譯成白話文是一回事,翻譯成白話文以後,我們是否忽略了原文當中其他同樣值得體會的意涵,則是另一個問題。

2. 即便未經理解的背誦是沒必要的,但背誦真的毫無意義嗎?
若以朱家安舉出的例子提問,則是:「即便現階段只會畫公主,真的代表完全不會畫畫嗎?」事實上,背誦一直是人類在教育上使用的方法,特別是在中國文化中,背誦被古代文人視為領會文本精神、啟發思想體悟或審美經驗、甚至是捕捉靈感綴為篇什的必要條件。
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其中的「讀書」,其實更接近於今日所謂的「誦讀」。古人相信文篇的「文氣」與人體的「聲氣」,在「聲音」的介面上可以產生內在的聯繫。可見古人的經典教育兼重內容與形式,甚至同時要求學習者主動的參與。
著名的先秦思想家荀子曾如此描述學習的效果:「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大意是說,真正的學習不只是一種「入乎耳,出乎口」的「記問之學」,且非但死背無用,只有概念意涵的掌握也遠遠稱不上完整。真正的學習,應當使文本在心中生根,同時又成為一種身體的記憶,從而改變我們四肢五官等行住坐臥的活動。換句話說,真正的經典學習,應當是一種兼含「血氣心知」的「身心之學」,而這一點,正與「背誦」息息相關。

綜整以上兩個提問,可以說,在語言與意義之間,以及心靈理性與身體感性之間,可能有著更為複雜的關係。所謂的意義是否能被語言的窮盡?或者說,語言所能表達的是否全都能以邏輯分析為清晰的命題?另一方面,語言是否單純屬於理性思維的管轄?或者,在語言的世界中還有一種「語感」,能夠呈現身心共融的生存感受?
可見,排斥理解的背誦固不可取,但在作出更細緻的討論之前,簡單地取消古典文本在語言上的不可替代性,並否定背誦作為學習方法的意義,就算不是弊大於利,也很可能形成另外一種偏見。以下,我們將沿著「身體哲學」的路徑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參考資料
1|任重:〈專訪王財貴:讀經是多元的教育,以全盤化西為標準〉。
2|朱宥勳:〈古文教育和文學教育的雙重失敗——從「古代廢文大賽」到「桃機賦」〉。
3|葉丙成 2015 年 11 月 21 日 facebook 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