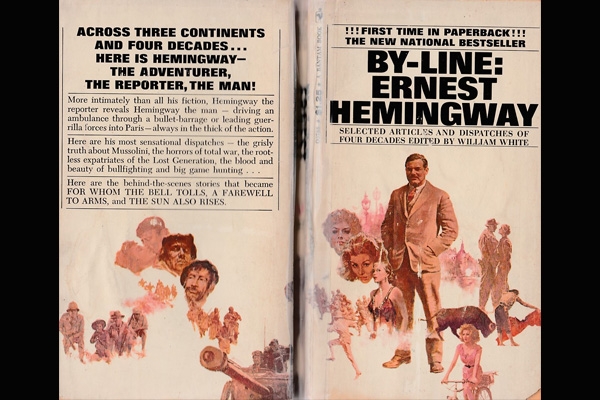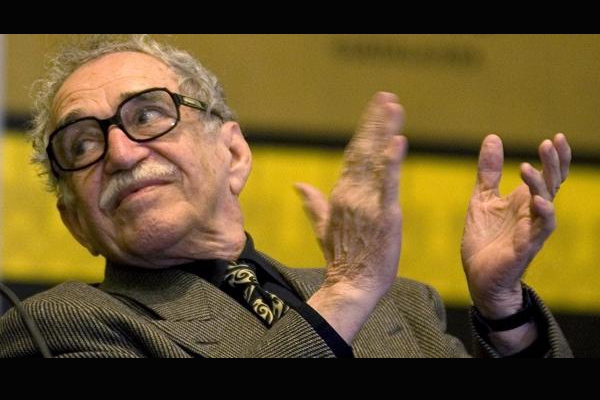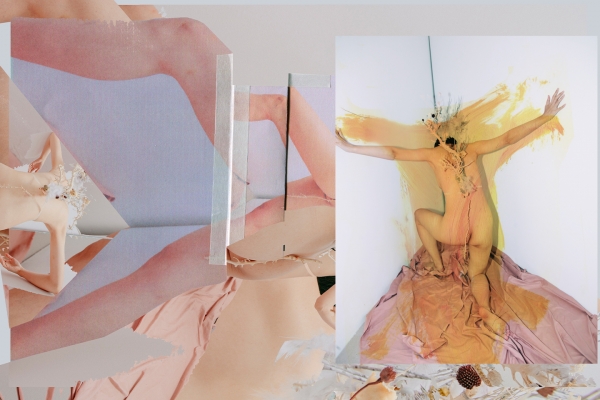有時看書|死難紀念碑式的詩
基於某些原因,我不怎麼喜歡讀現代詩。
我對耽溺於詩中的愛好者經常不以為然,大多是因為那些詩歌真的不怎麼樣;有時得到這樣的讚美「你的小說有詩的韻味」,我心想小說寫得像詩有甚麼好的;我特別討厭閒聊之間有人講出「Poetry」那個字,好像在隔夜蛋炒飯上放一顆松露那樣稀奇巴拉的;當我讀到偉大的詩句心跳一時狂飆,我會扶著書櫃在一疊即將退書的硬皮詩集上坐著喘氣,心想讀了一頁感人的詩會讓人五內俱焚,那又有甚麼用處;然而原本詩就不是為了服務實用主義而生,它早於工業革命前幾千幾萬年,以歌聲、以圖畫、以符號形式存在於人類生活中,而我種種與詩作對的行徑,除了提供給難相處的文藝同好們——但願有——少許惡趣味,其實也沒其他用處。
所以去年夏初,我決定洗心革面,重新面對詩,正好有人透過朋友拜託,於是接下一本詩集的翻譯工作。
Grupa Poetycka Rebjata(GPR)是三個波蘭大叔組成的團體,據說是波蘭國內成軍最持久(!)的詩團,在我認識他們之前便早已有「頑童詩派」(註一)的正式中文譯名。我帶著偏見與猜疑試讀詩稿,讀了前面幾首,閉上眼睛,已經準備在心裡向所有當代詩人道歉。
就像散文不能虛構,有些事情,是只有詩才說得清楚的。
我對詩的認識不夠深入,但我對波蘭歷史造就的民族性卻有直接的認識。整個二十世紀一百年間,波蘭被夾在蘇聯與納粹德國中間,先是好不容易復國之後又被滅掉,二次大戰期間有六百萬人口喪命,戰後終於在夾縫中重新建國,然後整個二十世紀後半,又在「受壓迫——反抗——被武力鎮壓——哀悼死傷——稍有改善——新的壓迫來臨」的輪迴中反覆。
某個旅途中遇見的波蘭女人 Monika 跟我說,波蘭婦女聊天嗑牙的內容,永遠環繞著身體的病痛,抱怨比慘就是他們表達愛與接受愛的方式,把自己說得越慘,同伴感情就越好。戰後的波蘭走過顛簸不斷的社會主義經濟道路,Monika 在童年親眼見識了改革開放以及經濟轉型,二十一世紀初,她嫁給了一個希臘人:「對波蘭女人來說,結婚結得好是很重要的。」她說。
波蘭男人則是另一個極端,他們從不說痛,總是喝最烈的酒,隨時做好長期抗戰(戰爭,結束了嗎?)(註二)的準備,至少,寫詩的男人絕不抱怨,他們用美感與詩意提出強烈質疑,且不容許你別開視線。以下是私心挑選的幾首硬詩,出自 GPR 最新詩集《International》(註三):
JOANNA
She was standing at the door and smiling.
Completely without pyjamas. Doesn’t my
hobby bother you? – I asked her, knowing
that some would prefer other hobbies. Not
at all, darling, I like it when you sit like
this and stare at the typewriter. It’s good,
and I find it relaxing. I’m very proud of
you, it’s more noble than embezzlement of
the EU funds, being cruel to animals, or
voting for idiots.
JOANNA 久安娜
她站在門邊微笑,睡衣完全沒穿。我的嗜好讓你
反感嗎?——因為有些人寧願我有的是別種嗜
好,所以我這樣問她。 一點也不會啊親愛的,我
喜歡你這樣坐下盯著打字機看的模樣,多好,讓
我覺得很放鬆。你讓我感到很驕傲,比起侵占歐
盟公款、虐待動物、或是投票給白癡,你做的事
情要偉大多了。
**
THE TAYLOR
He did one more fitting
marked something with a French chalk
When I came to pick it up
He was already hanging
裁縫
他又試穿了一次
用粉條做了幾個記號
我去拿衣服的時候
他已經掛了
**
POLISH PEOPLE, NOTHING HAS
REALLY
happened but please
lean the ladder
against another wall波蘭人,真的,甚麼事情也沒有
沒有發生,但是
請把梯子靠在
別的牆上吧
**
1198 mamsl
Not much is seen through the window
All you see are some small branches
Naked and dry
Like a prick
If I believed in ghosts
The ghost of Krzysztof Komeda
Would have drunk
Nut liqueur with us yesterday
Otherwise only from time to time
A small flash of light
A bulb over a sink
Or a station where you change cable cars
When I was a kid
It was called a Purgatory
Back then it was crowded
People were ready to kill to get a place
Nowadays there are no lines
So anytime I check out
A carriage
Will take me.海拔一一九八公尺
窗外看不到多少東西
只看得見少許短小樹幹
光禿且乾
像根刺
如果我相信有鬼
克里斯托夫·柯梅達的鬼魂
昨天必與我們同飲
喝堅果酒
要不從來就只有
一瞬間閃光
水槽上的一個燈泡
或是轉乘路面電車的車站
當我小的時候
這裡被叫做煉獄
那時總是擁擠
人們為了找個地睡願意殺人
現在到處都沒有界線
任何時刻,我一退房
一輛馬車
就來接我
翻譯完成後的某一天在柏林,我有幸與詩團中的兩位見了一面,跟隨造訪了住在西柏林的一位「波蘭地下大使」。按了許久門鈴,「大使」先生終於開門,探出一張白髮銀鬚的臉,發現有女士在場,說了聲等一下,等他著裝完畢,正式開門迎客,進門撲鼻而來烤箱內滋滋作響的德國肉腸,以及整齊排列在桌面上的,各種口味波蘭伏特加,有如等候領袖閱兵般的壯烈站姿,過了今晚,它們將一滴不剩。
沒有一個國家的首都像華沙有那樣多的死難紀念碑,每一個碑下鎮著的不是一、兩個亡魂,而是幾百、幾千、幾萬個在戰亂中、在抵抗中死去的波蘭人。波蘭男人寫的現代詩,不適合花前月下、不宜拿來排遣雅興,這是死難紀念碑式的詩歌,頑強地擋在下一波趁虛而入的坦克前。
.jpg)
Photo Credit:mlabowicz(CC BY 2.0)。
參考書目:《International》, Grupa Poetycka Rebjata, 2015, Czuły Barbarzyńca(波蘭華沙)
註一:頑童詩派成員/Stefan Laudyn, Tomasz Szafranski, Witold Szuk。
註二:就在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由於受到烏克蘭綿延戰火的威脅,波蘭東部的居民正熱烈歡迎美軍坦克過境。這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部隊在波羅的海沿岸完成演習,回到德國駐紮地的途中,特別繞行一千七百公里,穿越波蘭與捷克境內,以宣示保衛北約成員國的決心與準備。(來源)
註三:英譯者/Jeff Butcher, Stefan Laudyn;中譯者/你的女作家我。
【有時看書/有時跳舞】
從大動物園畢業之後,女作家開始關注人類的世界。
繞道十四個動物園後,回到美國紐約居住,「有時看書」、「有時跳舞」。這個「一動一靜」的專欄,主要目的是在作品與文獻資料中尋找、拼湊,建構出藝術家們在生活中的形象,換言之——找出藝術家們的「萌點」。
萌,日語漢化之後的動詞,簡言之,就是「被可愛的特質所吸引」。
【何曼莊】
1979 年生,台北人,著有《即將失去的一切》(2009,印刻)、《給烏鴉的歌》(2012,聯合文學)、《大動物園》(2014,讀癮),是作家、翻譯、紀實攝影師、數位媒體製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