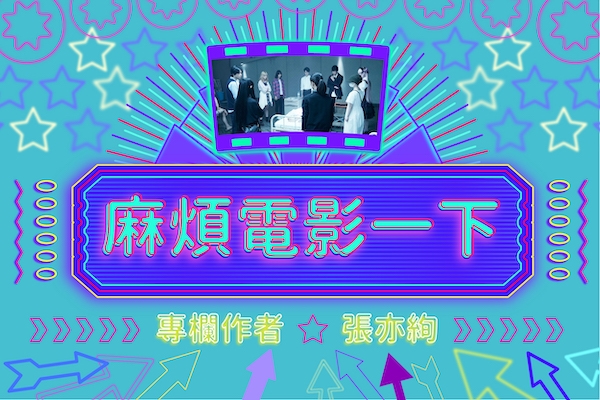麻煩電影一下|撩妹嗎?妹也很會撩妹——張亦絢看《燃燒女子的畫像》
在新浪潮的後浪都作浪許多年後的今日,看到四平八穩的《燃燒女子的畫像》,不免驚異。但且別太快下結論——看到最後一個長鏡頭,我對此片的所有保留意見一掃而空,在心中豎起兩個大姆指:五個燈全亮。
從頭到尾都有戲的電影不少,但要做到能用一個鏡頭「燃燒」整部電影,即便電影史上未必全無,但也屈指可數。難怪本片能奪坎城的劇本獎與酷兒金棕櫚——今年酷兒金棕櫚的參賽片,強棒不少——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編導的《燃燒女子的畫像》擊敗了《痛苦與榮耀》與《今夜我們無罪》——前者是引領風騷多年的阿莫多瓦的大作,後者出自導演手法卓絕的戴普勒尚(兩片都在「麻煩電影一下」的「小麻煩」中出現過)。《燃燒女子的畫像》如果僅止於訴說十八世紀同性情愛,或是顛覆藝術史的母題「畫家與模特兒」,不見得就能技壓群片。但那會名留青史的一鏡,無疑將是令人津津樂道的朝聖名段。
.jpg)
不過,即便沒有最後的一錘定音,這部略令我感到走珍康萍《鋼琴》或布烈松古典路線的古裝電影,也絕非學院派電影的謹小慎微——當酷兒電影如百花齊放爭妍鬥艷,結合各式議題與類型,繁複機智到彷彿觀眾個個都是一個羅蘭巴特加一個蘇珊宋塔——節奏平穩,鏡頭不搖,「更多柏格曼」的《燃燒女子的畫像》,力圖讓藝術電影不與大眾電影切割,不能不說慧心獨具。
十八世紀的刻骨銘心
情節很簡單:刻骨銘心的愛情如何發生以及如何(不)結束。但電影的另一個「主角」可說是「十八世紀」。「不是修道院就是婚姻」——是那時女人二選一的命運,如果非要多選一項,也有為抗婚而自殺的。
電影中,雙女主之一艾洛伊茲(Adèle Haenel 飾)的姐姐就選擇了自殺,而使艾洛伊茲得以作為姐姐的替代而從修道院出來。在修道院可以唱歌讀書,但是封閉環境也使她只認得風琴一個樂器。
十八世紀也是歐洲女畫家展露頭角的年代,最為人知的有考夫曼(Angelika Kauffman,1741-1897)和勒布倫(Elisabeth Vigée-Lebrun 1755-1842),她們的作品與生平尚可查考,但更多歷史細節,就只有藝術史的專家才能告訴我們了。透過本片另一女主瑪莉安(Noémie Merlant 飾),導演為我們勾勒出,當時可以外於強制婚姻的女性面貌:在公共場合,她也穿誇張的蓬裙,但她到處旅行,乘舟渡海遇到需要時,也能二話不說躍入海中游泳。她繼承父親的畫家事業,自己決定要不要婚姻。
.jpg)
是什麼讓兩人相遇?原來在照相未發明時,除了家世,男方也要求畫像以見女方相貌。肖像畫不是純粹的藝術表現,也是性別政治結構中的環節:詩歌總傳說漢代宮廷畫師毛延壽權力大到決定王昭君的命運——差別在於,昭君因畫遭冷落,電影則是畫好為促婚。換言之,強制男女婚姻的「禮俗物」(肖像畫),使得待嫁女與女畫家交錯:她們相遇在——就會拆散她們的文化設計中。
不過,最能代表那個時代的,或許是這兩個女人要幫助懷孕小女僕蘇菲流產的場景,她們站在沙灘兩頭,令她折返跑,期待這就可以幫到她。這個古早流產的插曲也帶來了絕美的另一段:冓火夜會的歌舞(合唱曲為當代作曲家 Para One 與 Arthur Simonin 新譜,並以拉丁語為詞,製造出詭譎親密的效果),宛如「電影中的電影」。電影欲向古老民間結社與女性記憶同時致意的用心明顯,但表現不落斧鑿痕跡。
撩妹嗎?妹也很會撩妹
艾洛伊茲不能拒絕婚姻,只能拒絕畫,拒絕了一個畫師,又來一個,且還銜命以類似偷拍手法偷畫她。諷刺:某些電影拍攝女人是否也是違背女人自由與意志的「選秀」?《燃燒女子的畫像》的另個令人大呼過癮之處,是幾乎只以眼神與對白,讓我們看到今日蔚為「顯學」的「撩人術」如何在雙姝之間上演。
我才剛看過波特王撩蔡英文總統的影像,覺得挺好。「撩人術」反應社會的開放,也顯示大眾對社交技能精進的興趣。但它可能被質疑,透過「男撩女不撩」(這是為什麼我們經常看到「撩妹」ㄧ詞,而少見「撩弟」出現),而形成另一種刻板印象與性別分工。《燃燒女子的畫像》中,妳來我往的雙撩雙殺,則如勢均力敵的網球開打,令上述有可能僵固性別氣質的假設,不攻自破。
.jpg)
在這些「撩是我,撩是妳」的場景中,進行的不單是語言巧藝的應用,除了就地取材的試探、剖心、邀約外,它也開鑿精神並重塑靈魂,催情不是只是官能生活,它是所有生命。作為模特兒的艾洛伊茲,至少啟動了三個面向:如果不是她,瑪莉安不會知道繪人者也在被繪者的凝視中、不會有機會留下給情人的自畫像——不會——最後一個「不會」較為隱晦,但非常有意思。兩人陪小女僕流產完畢,艾洛伊茲不肯就寢,學幫流產者的姿勢將雙手放在蘇菲雙腿之間,對瑪莉安說,「我們要畫。」這一幕乍看費解,這個動作看不到生殖部,也應該不是愛慾的表現——瑪莉安就算畫了,恐怕也不能示人。
要了解這一幕,必須憶起瑪莉安對身為女畫家的自述,她為不能接近男性裸體,從解剖角度理解男性生理構造而沮喪:「不能掌握男性生理結構,就被排除於所有偉大主題之外。」——藝術也有它的性別歧視傳統與閉鎖性。雲遊四海的瑪莉安並非如想像中自由,她教了艾洛伊茲許多事,但艾洛伊茲也教她:其實存在有「偉大」的女性主題,那是我們共同見證的經歷,ㄧ個女人為另一個女人的性自由與身體自主而伸手——這個主題在十八世紀會是驚世駭俗的醜聞,但看在二十一世紀的眼中,這不偉大嗎?艾洛伊茲給出的三課,瑪莉安即使學會了,也「無用武之地」,這是時代的限制,但在我們的新時代,難道還要繼續隱下(女性)知識嗎?
「她沒有看見我」
法語的「看」(regarder),本身就有保存(garder)之意,在電影中,其語意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至:除了有希臘神話奧菲斯回首的新詮,瑪麗安也自述,多年後,她有兩次再見到艾洛伊茲。這兩次「見到」,都超乎我們日常對「見到」的想像。在瑪莉安說出:「她沒有看見我。」之後,就是點亮整部電影的不朽一鏡,它也是對莒哈絲在《廣島之戀》中名句的遙映:什麼也沒看見/看見一切。這是超越視覺的視覺,既惟電影所能及,也是藝術與愛情「超越生死」所追尋的不二境界。
.jpg)
《燃燒畫像的女子》
導演|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
主演|艾黛兒Adèle Haenel、Noémie Merlant
上映日期|2019.12.20
【小麻煩】
蜷川實花的《人間失格:太宰治和他的三個女人》,也可叫作「我們與文學的距離」。美知子是妻也是無情文學評論家,靜子是有競爭意識的繆思,富榮是有如自我鏡像的為愛尋短者——個個都與太宰形構了星叢,好似人人都參與了創作。但下筆的焦慮,如令他痛哭流涕的稅單,仍是絕對的孤獨。這是一個互相課(感情)稅(睡)求大作的悲喜劇。三島由紀夫與坂口安吾都來了。求見文學史?歪頭沉思吧:這可考?可不考?有趣就隨它去吧。電影勁爆太宰不,影音華麗太宰不,有見解,有風格,輕快,殘酷,安迪沃荷多於溝口健二,傾向法斯賓德所定義:好的壞電影。
【麻煩電影一下】
電影之道在麻煩。不製造麻煩的電影無可觀,生出了麻煩的電影才可愛。嗯,有點麻煩⋯⋯,當我們談論一部有趣的電影時,我們似笑非笑,表面怪罪,心中深喜。它或許還有些難懂,它可能已讓人吵架,但就是如此,我們心嚮往之。麻煩是多麼親愛的字眼啊,當我們想從陌生人那裡問到一點資訊,當我們希望身邊人遞給我們什麼,我們就從這一句開始:麻煩你/妳⋯⋯。【麻煩電影一下】每個月會挑出一部有麻煩的電影,與你/妳一起不厭其煩。
【張亦絢】
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小道消息》、《看電影的慾望》,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 / 巴黎回憶錄》(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