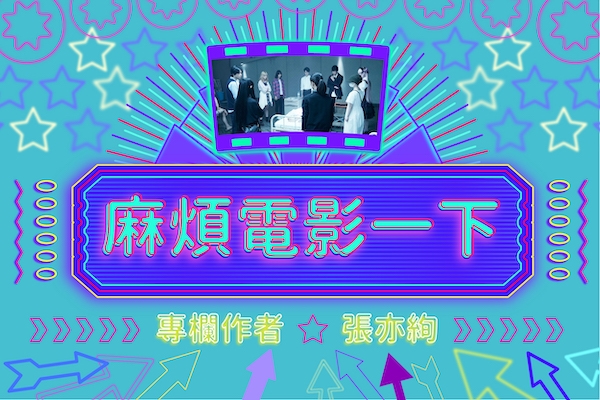麻煩電影一下|痛惜致命的寂寞:張亦絢看《金手套虐殺事件》
《金手套虐殺事件》是一部出奇明亮的電影。
出奇明亮,因為,光直到電影最後一刻才出現;因為,光走過了「沒有光的所在」。
「留級少女」(以下簡稱「留女」)推著單車離開火災現場,渾然不知她與出入金手套的虐殺犯洪卡擦身而過。
若不是洪卡大意弄出火災,已被盯上一陣子的她,很可能會被誘進洪卡的公寓。如果僥倖,她或許能逃出公寓,如果不幸,她可能被虐死或燒死。
法提阿金拍了那麼長的虐殺事件,此刻我們才恍然大悟,「留級少女」才是電影的真正主角——不是因為她貌美,而是她可能就是「所有那些被虐殺女人」的過去翻版,她現在的存活像個奇蹟,但未來呢?
.jpg) |
喝可樂的與喝酒的,來去金手套
電影出現的人物可大分為兩組,喝酒的與喝可樂的。喝酒的有茫到只跟著酒走的,有還保持一點理智,會發表「至理名言」的酒客。比如酒吧老闆,他說,「必須偶爾檢查一下人們是不是還活著」(電影中有許多這類對白相當精采)。這指的不只是某些酒客狀似睡著,其實已停止呼吸,也是這個宇宙的最好註解:醉生夢死不是暈陶陶而已,行屍走肉,有的也早成為他人的刀下俎。而成了「活刀」的如洪卡,也很難說這就是「活著」。
如果有其他機構領她們去他處安睡,受害女人未必會跟洪卡走:但問題也沒有那麼簡單,精神奕奕的女傳道師,也來到了金手套酒吧,但雙方格格不入的感覺很明顯。酗酒的型態,不是只因為酒精可令人上癮,往往還有更深的心理史。阿金拍這些寂寞眾生相,介於尼德蘭畫家布魯哲爾(Pieter Bruegel)與美國畫家霍普(Edward Hopper)之間,既不美化其衰敗醜陋,也不忘呈顯其恍惚風霜。
除了喝酒,電影中還有喝可樂的。喝可樂的少年少女覺得紅燈區很酷。遊玩的一組少年說,要去紅燈區玩:當「留女」問希望與她作伴的「小威」(髪型貌似北海小英雄中的小威),他說兩個人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是什麼事?小威的答案也是「去紅燈區」。
這意謂什麼?最大的可能就是,小威的家庭是比紅燈區不酷的地方。不酷可能是什麼?沒有空間(狹小)或沒人都有可能。「金手套酒吧」聚集了會被當作下沉至底層的人,但對來此消費的人,這又是底層的上流世界,「上與下」的想像在此交錯。這是我們說的「龍蛇雜處」,其中的女酒客不說二話就請付不出酒錢的女客(後來被洪卡帶走分屍)喝咖啡,說明酒吧也不光有頹廢,也是抵抗孤絕的最後堡壘。還在喝可樂的小威與留女更天真,當這些成人將恐怖灰暗的想像擲向他們時,留女感覺莫名其妙,小威則朗聲問「為什麼?」可樂族與酒精族的對照,不是為寫「小白兔誤入叢林」,而帶出了這樣的疑問:人們是從何時失去有光亮的生活的?
留女與小威都是《麥田捕手》所言「懸崖上的孩子」,有一幕老師對留女訓話,大意是老師們很勉強才能不放棄她,點出留女心不在焉的危險。學校該不該只保護能融入學習的學生?需要另作辯論。但迫切的問題不是學業表現,而是「離群索居」的少女,容易被當成性獵物。沒有學業的自信也能長成特立獨行的大人,但在這之前,她先要有機會長大。
未解決的食與被食衝動,以及「輕輕的一個吻」
洪卡不像老師看留女,會擔憂她心思渙散,他迷上的是她的香氣與美貌,兩者都是他最缺乏的,他的住處有藏在牆中的屍臭,他的臉有殘缺。他的其中一個受害者描述自己女兒職業是屠夫時,畫面出現洪卡的性幻想,美女生吃生肉。洪卡最原始的慾望應該在這,一種未解決的食人與被食幻想。我聽到過一個小姐姐對她三歲左右的弟弟說:我要把你放到烤肉架上沾上所有的醬,把你吃掉。小弟弟高興地咯咯笑,抱住他姐姐。吃對方表示對方是好東西,好到可以通過口腔進入體內。吃與被吃的雙方都快樂,因為這象徵了親愛。但大部份的人,後來都抑制或轉移了食人衝動,畢竟吃下對方,會觸犯不可謀殺的律法。食人衝動常先於殺人。食人衝動難以昇華,在電影中還有跡可循。
.jpg) |
.jpg) |
清潔女工的失業先生,在三人喝酒胡鬧的瞬間,嘴對嘴地親了洪卡。洪卡一下安靜了。這當然有喝多了作為掩護,導演也沒交代洪卡的安靜是震驚或安慰或害怕,但是下一鏡,接的是洪卡就著餐盤吃早餐:人模人樣了。有說酒是奶的替代,那這一幕,洪卡就是稍離吃奶嬰兒期,不但吃起固體食物,還文明起來了。這個吻如果來得更多或更早,或許能扭轉洪卡的命運。這是電影的暗示。
不久,洪卡在與清潔女工獨處時,說道:「我愛妳。我要上妳。」本可能在考慮以軟性勾引兼職賣淫救房貸的女工嚇壞了。這可不是霸道總裁的幻想劇本,洪卡對驚慌的她又攫又打,讓人「想笑又笑不出來」。如果這是「老鷹抓小雞」就很好笑,但問題這是男與女,是人。較之洪卡過去的行為,粗鄙求愛其實已是他文雅的上限了。估計洪卡若正式去嫖,也嫖不長久。被物化成可買的女人與物化成動物或球之類的物體,還是不同。不能怪有點感覺的女人會嚇跑。洪卡的執拗令人想起不願離開乳房的「嬰兒蠻橫」。
洪卡虐殺女人的殘暴,並不始於殺人分屍,而開始在更早之前。一個男人如何長成不能抑制本能的人?阿金認為男人也有責任。當小威在金手套的廁所對成年男人說「嗨」,就被羞辱說是牛郎,這是恐同,也是殺害較溫柔的靈魂。小威因羞恥躲進廁所不肯出來,導致留女落單,讓我們看到每個柔軟神經被切斷,都會影響到整個社會身體的其他部份。
.jpg) |
死在春天,是多麼艱難
「在法提阿金的電影裡,青椒會給人感覺特別青。」——這原是我對法提阿金的喜愛感想,在這部電影中也不例外。洪卡的公寓裡有兩張毯子,一張灰頭土臉,一張色彩斑斕,色彩代表了感情的投入,彷彿法提阿金從不停止痛惜,所有邊邊緣緣的人,原都有兩條路,一條黯沉,一條艷麗。當我們看到最後的破敗,仍不要忘記,在最初,總有另一個可能:那個比較有感情,比較明媚的生命。比如小威在酒吧門口沐浴到的陽光,比如片尾伴隨留級女生的音樂——如果德文是照法文原版翻譯的,其中一句就是:「我就要死了,但你知道,死在春天,是多麼艱難啊!」
【小麻煩】
「殖民體制是勒索與無能的混合」——《夜鶯的哭聲》 心無旁鶩地處理了此一主題。正因對原住民族的本土文化「比一知半解還不如」,英國殖民者勒索的方式更殘暴愚蠢。但若只說這部份,有的是記載更詳盡的書。除了為構成敘事的鏡頭,愛爾蘭女囚克萊兒與澳洲原住民族人「黑鳥」的主觀視線鏡頭,不只可看到攝影嚴謹的執行,更是比情節更重要的「第一敘事」,傳達了電影與被壓迫歷史在一起的立場。感情與正義交會的尊嚴之時,震撼,又免煽情。這一類的到位,幾乎不露痕跡。
【麻煩電影一下】
電影之道在麻煩。不製造麻煩的電影無可觀,生出了麻煩的電影才可愛。嗯,有點麻煩⋯⋯,當我們談論一部有趣的電影時,我們似笑非笑,表面怪罪,心中深喜。它或許還有些難懂,它可能已讓人吵架,但就是如此,我們心嚮往之。麻煩是多麼親愛的字眼啊,當我們想從陌生人那裡問到一點資訊,當我們希望身邊人遞給我們什麼,我們就從這一句開始:麻煩你/妳⋯⋯。【麻煩電影一下】每個月會挑出一部有麻煩的電影,與你/妳一起不厭其煩。
【張亦絢】
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小道消息》、《看電影的慾望》,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 / 巴黎回憶錄》(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