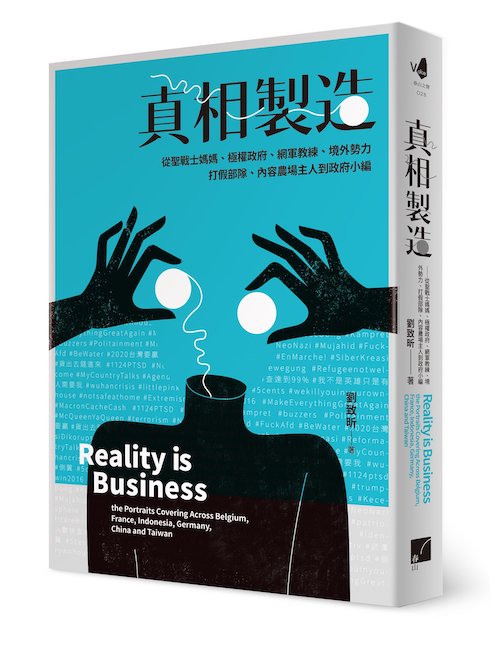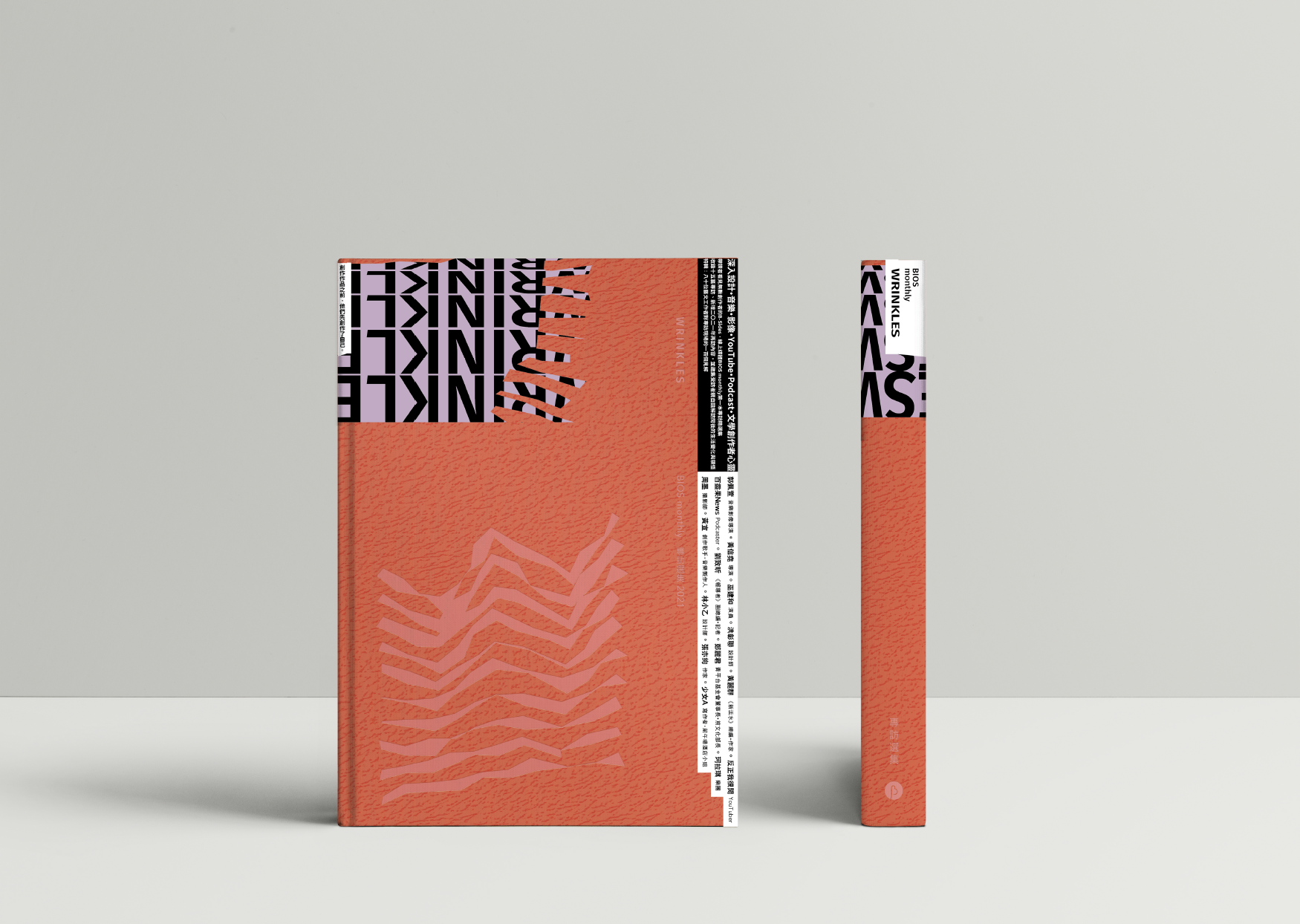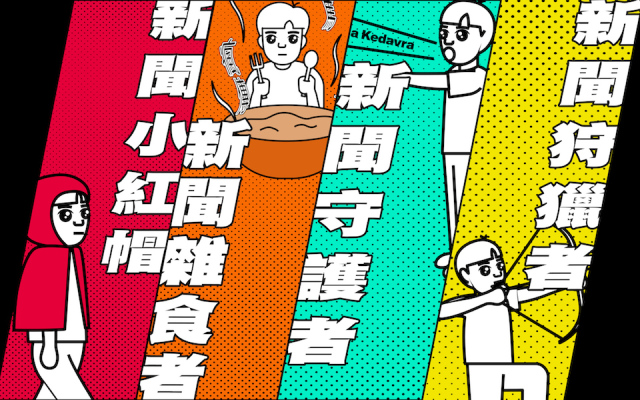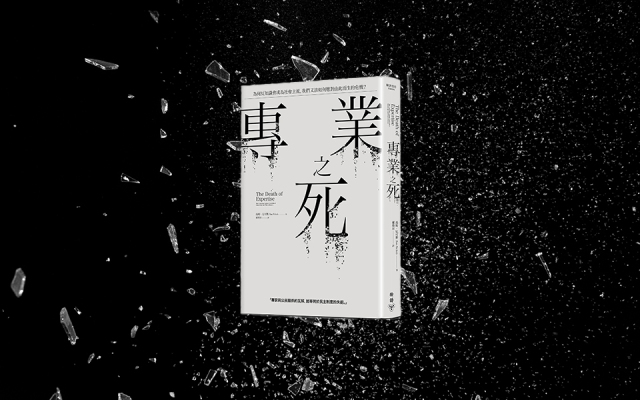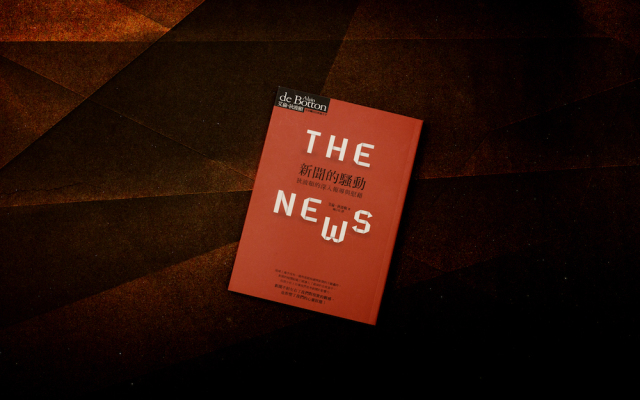如果這還不是最終的答案——專訪《報導者》副總編輯劉致昕|封面故事 2020 輯五
BIOS monthly 以創作文化為核心,持續發展多元深度的線上內容,深入且兼具視覺美感的人物專訪有幸受到讀者喜愛,成為招牌欄目。2021 年我們出版《Wrinkles —— BIOS monthly 專訪選集 2021》,全書收錄站內精選專訪 15 篇、新增再訪內容,並邀集受訪者親自註解訪問後的生活變化與領悟。
本篇專訪即為書中收錄篇章,全文精裝典藏現正販售中 ➤➤ 點此購買
那你就做吧
事前提供給他的訪綱打滿了筆記,劉致昕說是記給自己看的,怕採訪現場沒好好回答問題。前一天,他正好上完一堂聲音課,請了一位從事聲音教學的學弟來調整自己。學弟告訴劉致昕,他說話時總在韻腳用力,這樣聲音會糊成一片;又太仰賴麥克風,發聲時太過放鬆。聽完建議的劉致昕走在夜裡的忠孝東路,把路邊的招牌全部唸過一遍:華—南—銀—行——
這僅是劉致昕為了主持《報導者》的 Podcast 節目《The Real Story》所做的幾項準備其中之一。然而訪問當下,這系列由《報導者》與 SoundOn 團隊共同製作的節目已經上線八集了——身兼部內 Podcast 團隊統籌與主持人,劉致昕同時仍跑編採、位在台南福吉路上與另一半共同開設的午營咖啡也繼續營業;今年七月他升任《報導者》副總編輯的消息公佈,那時他三十三歲生日才剛過不到兩個月。從 2010 年進《商業周刊》跑網路線開始算、十年記者生涯,從來不是每件事都能充份準備之後才開始。他是認了。
「行銷部半年前做了將近一千六百份問卷,百分之九十九讀者希望我們做 Podcast,那沒什麼好說的,就是要做。但因為是新項目,籌備很久一直無法啟動⋯⋯其實沒有誰必須要去推這件事,但你看到大家都卡住了、看到市場這麼明確期待的東西沒有做出來⋯⋯那你就做吧。」
句子裡的「你」,代指的是劉致昕自己。三小時訪談中,他時常轉換人稱來敘述,一開始以為只是為了把我們放進新聞記者的視角裡來理解他的說明,後來發現他也總與自己的陳述中帶有個人意志的成份輕輕保持距離;Podcast 上路後,他自己找來賓、主持、寫腳本,並寫四個社群渠道的宣傳文案,「因為我們沒有增加任何一個員額,用原本的團隊多做一個每週更新一集的節目,你怎麼忍心叫編輯做這些?也因為這是第一季啦,第一季可能就是唯一一季,我不想在這個情況之下就給團隊工作⋯⋯」
《The Real Story》8 月 6 日上線首二集「安毒幽靈」系列報導幕後談,8 月中就衝上 Apple Podcast 台灣區第一名。直到我們與劉致昕見面的這一天,《報導者》與 SoundOn 之間的合作備忘錄甚至尚未簽妥,第一季十二集的額度就即將錄完,「你就知道這一切有多麽倉促」。嘴巴說倉促,劉致昕按著節奏一面確認下一次錄音邀約的鄭竹梅女士,私下也把前幾集節目丟給學弟聽,請學弟持續給建議。
「就是⋯⋯不怕死啦,就是不怕死。」他這樣為自己半年來的奔波作結。


沒有前人
劉致昕不是第一次身在新媒體的浪尖上。許多網友第一次看見這個名字,是在 2014 年台北市長選舉時由沃草主辦的「市長給問嗎」線上直播,請來連勝文、柯文哲、馮光遠在鏡頭前回答網友提問。那時坐在候選人身側負責主持與提問的他,是應沃草共同創辦人林祖儀之邀,接下這個沒人坐過的位子。一直到了現場,他才發現除了鏡頭和麥克風是架好的,其他一切都要由他來填滿。
「現場沒有製作人、沒有人幫我報時,PTT 的人就站在後面看我跟連勝文兩個人面對面,我還要自己把所有題目印下來、自己寫腳本,然後主持,主持時還要自己抓空檔看網友的反應。唯一得到的現場回饋是有人遞紙條給我,說網友抗議連勝文一直咳嗽,所以我就幫連勝文倒水⋯⋯」
他第一份媒體工作在《商周》,當時連 LINE 都沒有,臉書尚未公開發行。一般財經雜誌只在意上市櫃新聞,網路線是邊緣單位,剛到任的劉致昕自然被擺在那裡。自稱當年「網路線大部份處理的都是小新聞」,劉致昕做了 LINE 在台灣第一個報導〈一支 App LINE 竟敢向臉書、雅虎宣戰〉。在 LINE 台灣活躍用戶衝破兩千一百萬的如今讀來,這標題算是半個預言了。
《商周》時期,劉致昕也做了 Google Data Center 到彰化設點的報導,在 2012 年便指出 Google 這一步將成為促使台灣轉型綠電的關鍵——而這個觀察,也在 2018 年成真。
因為邊緣,所以有空間做主流較不關注的題目。當時的劉致昕,不像資深記者需要配合公司方針,也就專心提案各種報導的可能。2011 年,德國非典型政黨海盜黨靠著網路串連與政治透明的訴求,拿下十五個地區議會席次;劉致昕隨即電訪到海盜黨主席 Bernd Schlömer,在《商周》推出〈一群宅男工程師 攻下德國議會殿堂〉,並在離開《商周》後前往德國追問出〈德國的「遙控民主」實驗──海盜黨總部現場觀察〉。
待臉書上市發行、電商在台灣普及之後,「網路」已一躍成為政經領域亦關注的焦點。如今加入《報導者》,劉致昕參與「打不死的內容農場」報導專題,也寫滲入 LINE、Telegram 的訊息輿論操作,其中一支關注的命題仍是網路。「從關注網路,到見證網路不只是網路,一旦開始了,你就會想要持續地寫下去,其實是那麼單純的想法而已。」
致昕,有需要訪那麼多人嗎?
翻開劉致昕執筆的報導,除了網路,也關心政治、科技與人權,議題廣泛。早在十五歲就想當記者的他,大學推甄同時通過政大外交和新聞系初審,但同校兩系面試安排同一天,逼他做出選擇。「我就被雄中校長叫去談話,他跟我說,如果要當記者,技術之外也要有視野,去外交系也滿好的。」
外交系學生的終極試煉,是參與模擬聯合國。學生被分派為聯合國各委員會下的國家代表,提出屬於該國家、某議題下的提案,最後以聯合國正式議事規則開會,為自己的提案爭取支持——成為記者之後,劉致昕做的題目也幾乎全部是自己提案。不只網路科技,他也寫過海岸開發、塑化劑,「每個題目,你都要研究完所有的東西之後,在面對受訪者時提出你的角度。接著,寫文章時要拋出觀點給你的讀者。吸收資訊、培養觀點,然後提出報導的價值。」
至今,劉致昕的前輩同僚,仍常常勸他別這樣做新聞——對不同主題懷抱好奇,下筆範圍太多太雜,一來無法累積專一領域的人脈與知識,二來巨量的閱讀與研究傷腦傷身。但問劉致昕為什麼選擇關注那麼多樣的主題,他卻說:不是我選擇的啊。
「作記者,是題目來找你。你不這樣覺得嗎?」他反問我。
對記者職業的仰望,與他自我懷疑的性格相剋相生。他拿出背包裡的一疊七十幾頁的英文報告,是針對中國資訊戰的研究,上頭一些專有名詞旁有他手寫的註釋,「要提出觀點,就要唸很多東西。在《商周》有時候你只是寫兩頁的稿子,一千五、六百字,你就要讀這麼一大疊。我記得跟我出國採訪的攝影記者都很痛苦,會跟我說:『致昕,你有需要訪那麼多人嗎?』」
.jpg)
.jpg) 「因為不斷自我懷疑,所以你不會覺得自己得到的答案是答案、不會覺得自己完成功課了、不會覺得自己可以休息,只會覺得要一直看到更多東西。」
「因為不斷自我懷疑,所以你不會覺得自己得到的答案是答案、不會覺得自己完成功課了、不會覺得自己可以休息,只會覺得要一直看到更多東西。」
自嘲「這樣很痛苦」,卻也說「這是當記者的正面特質」。他的新聞嗅覺,不是天賜靈感,而是肉體的勞動換來的。
然而,被現在的上司評價為「對致昕,我只要負責拉住他就好了」的他,卻也曾經中途止步,從記者身份登出過一陣子。
提早回來
2012 年 8 月,劉致昕離開待了一年半的《商周》。他說,當時不成熟,找不到平衡的工作方式跟態度,對自己的工作出現許多懷疑。那幾年即時新聞當道,同業搶快有之,流量至上,消磨讀者信心,也耗著新聞產業的內力。「我看到很厲害的前輩記者,他可以用自己跑二十年台塑新聞的經驗,一個晚上就寫出一個封面故事,吿訴你台塑這家企業的利弊是什麼。可是,我回頭看我的工作環境,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待二十年,去累積成像他那樣。」
「我覺得自己心理上、技術上、體能上可能都做不到。所以就去做其他工作。」
離開,但也不算走遠。告別每週二開編會、三四五採訪、六日寫稿、週一改稿、週二再開編會的生活,劉致昕加入英國《金融時報》成為駐台助理記者,每天早上十點整理中文媒體三到五個題目回報,待記者回覆追哪條線、聯繫缺漏的受訪者,有行程就跟著跑。
《金融時報》的內部規範,求證時要求每一個重大事實和說法必須經過兩到三名互不相關的受訪者證實,否則再重大的發現也不能刊登,劉致昕對此印象深刻。但除了對內容與切角的要求外,他也對媒體應對新時代的做法有了更明確的認識,「《金融時報》也要求故事好看、要 juicy,也開發出不同文體,比如第一人稱的訪稿,或者和誰吃午餐、跟誰散步這樣的企劃內容。當時大眾會批評台灣媒體做這種事情,但去過 FT,就知道不用太在意這些聲音。」
在《金融時報》一年後,劉致昕輾轉被華揚創投的董事長延攬成為特助,接著加入該創投成立的公司「我知好學網」擔任專案經理,但也只待了一年多。訪綱筆記上打著一句「金字塔頂端的生活」,問他這句是什麼意思,他說當特助時既要倒茶、提包包,也要代替董事長出門看案子,不僅看到光鮮亮麗的那一面,也有辛苦的時候:「你會看到商業世界運作的規則,和金字塔頂端生活的難。」
離開新創,劉致昕短暫加入社企流一年;適逢家裡出狀況,他回到台南,開了午營咖啡,同時以 freelance 模式接案。除了 g0v 和《商周》等單位,也接一些「寫起來很療癒」的案子,例如旅遊景點手冊。
開咖啡廳原是劉致昕的退休規劃,沒料到提早實踐。所幸他大學時就為了這夢想到星巴克打工,算是稍稍過了水。回到台南,他和朋友花了半年時間了解社區需要什麼樣的空間,最後訂定了「社區咖啡廳」的方針。


「我很喜歡柏林,只有在柏林我可以感覺到完全的放鬆,可以完全做自己。」劉致昕說,「我們希望做出一個像那樣無壓力的對話空間,它不能太精緻、太文青、太明確,要讓每個人坐在那裡,都覺得可以放鬆跟外界連結。」在午營咖啡,年輕人帶著長輩一起參加假新聞調查報導分享、討論納粹後的德國。長期來咖啡聽講座的聽眾從高中生到六十歲都有,尤其珍貴的是這些人都希望聽見與自身不一樣的觀點:
「比如我們講同志議題,講的是為什麼有人會恐同,而不是『同志是基本人權』;還有性別教育是否完全適當、會對小朋友造成什麼影響,午營的聽眾都希望聽到不同的意見。」他說。
劉致昕沒想到,自己有一天必須與這個提早實現的退休夢保持距離。
2018 年,九合一選舉前,家人發現他是同志。他跟咖啡店只能搬離家,給無法對話的家人們一些空間。
讓他們說話
一切不在計劃裡。事情發生之後,他決定重新尋找正職工作,回到體制內,和午營咖啡拉開關係,不讓自身與家庭的糾葛影響店的運作。
他淡淡笑著,說這倒也吻合他雙子座的性格:「freelance 很自由沒錯,但如果沒有遇到好編輯,很容易陷在自己的世界⋯⋯如果想要做更大的題目,跟更多方面的讀者對話,一個人做不到,進團隊有可能⋯⋯」
與《報導者》前往瑞士交流時,劉致昕與 SWISS Info 的副總編輯聚餐,聊到午營咖啡出借場地給香港主辦人籌劃反送中說明會,來了一百多人。會後劉致昕將五名香港人與一百名台灣人的 QA 整理成報導,社群上一千多次分享。
「這就是地方媒體啊!」副總編輯這樣對劉致昕說。
原來他回台南一遭,仍在做媒體。

與鄭竹梅牽上線,也是因為午營。一開始,鄭竹梅沒有表明身份,偶爾借幾本轉型正義的書走。直到有次,她帶了一本全新的書回店裡,說借的那本不小心打翻茶潑到了。劉致昕才知道,這位常常帶人來聽講座的女士就是鄭南榕的女兒。後來,也才有了鄭竹梅在午營咖啡分享閱覽父親監控檔案的座談。
會上,有聽眾舉手發問:這些檔案有什麼好藏的,為什麼不直接全部公佈呢?
在午營,劉致昕擔任分享者與聽眾之間的護城河:「我就告訴那位聽眾,我有個德國朋友的父親是東德飛行員,兩德統一之後那位父親去看了監控檔案,從此再也沒有交任何一個朋友。因為他發現,原來他身邊的每一個人,鄰居、摯交⋯⋯,全部都是國家派來的。」
劉致昕對當時在場的聽眾說,檔案開放,要顧慮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政治正確。開放給學者多少、開放給家屬多少、外人多少,都應該要惦記著人。
他與我們談起有次聽朋友做的 Podcast,請來一名少女自敘。少女說自己為了國家考試放棄一切待在家裡、過著肉渣般的生活。為了可以唸更多書,買了一台平板,結果有了平板以後開始追劇,越來越像個肉渣。經過一年,沒有考上國考,不知道怎麼跟父親開口,於是對著平板,把這一年多的心聲講出來:她的夢想是當便利商店店員,因為每天都可以吃剩下的關東煮。
不到二十分鐘的錄音,裡頭是一個平凡人的自我懷疑、家人的支持、對日子的最私密的幸福想望,他聽了三次,感動三次。
「Podcast 在做的事,是文字做不到的。它可以傳達人嗓音上的各種變化,讓大家體感可以感受到,那是一個人。我想要把說話的麥克風遞給更多人,讓更多我無法用文字詮釋的、沒有辦法說服別人聽他講話的人,讓他們自己說話。」
這也是他心中開放編輯室概念的重要意義所在:編輯室裡,不能永遠只是同一批記者在討論問題,否則,就無法避免少部份被忽略的群體,仰賴一個強人或民粹政客代言的惡性循環。
「面對這個時代,媒體能夠做的,就是編輯室裡的多元性。」
為了將麥克風遞給他人,自己必須站在這裡。鄭竹梅在分享會後,卻主動找劉致昕談問答時發生的事。於是,兩人共同決定做一集 Podcast。起心動念到實踐,不過一個月的時間。

By the way 他是同志
採訪前,我們與劉致昕約在 SoundOn 錄音室碰頭。錄音結束時間比預期稍晚,劉致昕說,練習在聲母上用力果然有點不習慣。每一集節目上線後,《報導者》團隊會一一檢視每一則聽眾留言,列出檢討後的改進方式。有人說主持人不該隨意發笑,他也惦記在心。
所以最近才都吃中藥嘛,晚上都睡不著。他又笑著說。
「《The Real Story》的中期目標,是希望作為《報導者》的子品牌,走出台北。」訪談中不斷強調自己非新聞本科出身、無法代言所有記者的他,對閱聽人卻有一份不帶身份的溫柔:「在新聞產業,成為一個記者還是有既定的訓練過程,但你要想辦法讓不同背景的人能夠進來這裡,提出問題。我隨便亂講:我們去聽台灣十六個縣市明星國中裡的最後一名的困擾,每個人十分鐘。如果能夠呈現出這件事的話多棒?」
有一集預錄好的節目,他們邀請一位法師與他的另一半做分享。雖然因為對話太過家常,目前尚未上線,但這是劉致昕對節目的另一個目標:「大家在報導同志的時候,都會加上同志的標籤,來訴說同志的故事。我覺得這個過程就是在強化同志跟一般人的差異。我想要用 Podcast 來試試看,找一位法師來談他的生活,只不過 by the way 他是同志。」
這陣子,劉致昕台南台北兩頭跑。問他,後來有和家人說上話嗎?「有啊,不過不停地失敗。我只能等。」等什麼?他說今年罷韓投票後,他寫過一段筆記,「我大概是最希望韓國瑜可以把市長做好的人,因為我希望他真的是一個很好很好的政治人物,可以照顧我支持他的家人。如果他可以照顧我家人,我非常感謝他,因為我覺得這個往前的社會遺落了很大的一批人。如果他們能夠被好好照顧的話,那是我衷心所期待、而且我自己做不到的。」
做得再多,仍有什麼做不到。被行程填滿的他,一面樂著說自己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題目,一面分享稍早和另一半聊天,說自己要是真會心臟病發的話,「大概就是今天」。
他手上要處理一則人權影展的新聞,關於難民,「這個我不必處理,因為沒有新聞點、沒有時間,可是我想要處理,因為我寫過難民」;訪問隔週,他要做同志諮詢熱線在南部的募款晚會,「一樣的理由,這題不一定要寫,但我覺得我是編輯室唯一的同志,所以我應該要做」;一份假新聞國際報告,談中國資訊戰在武漢肺炎之後走到什麼程度,一樣不是「必要」,「可是我有寫假新聞,所以我應該⋯⋯」
我想起他反問我:你不覺得,是題目來找你嗎?
他為他寫過的發聲。儘管有時候,不是每件事都能充份準備之後才開始。他盡力追補進度,但不得不說時,還是認了。
他始終擔心他所分享的一切太過個人,但,個人的故事也從不只是個人的故事:「我不相信權威,我不覺得記者寫的就是對的,媒體說的就是對的。我只是很明確知道我作為同志這個身份,使我一直想要讓沒有被聽見的人被聽見、沒有被看見的人被看見。這對現在的我來說,是最根本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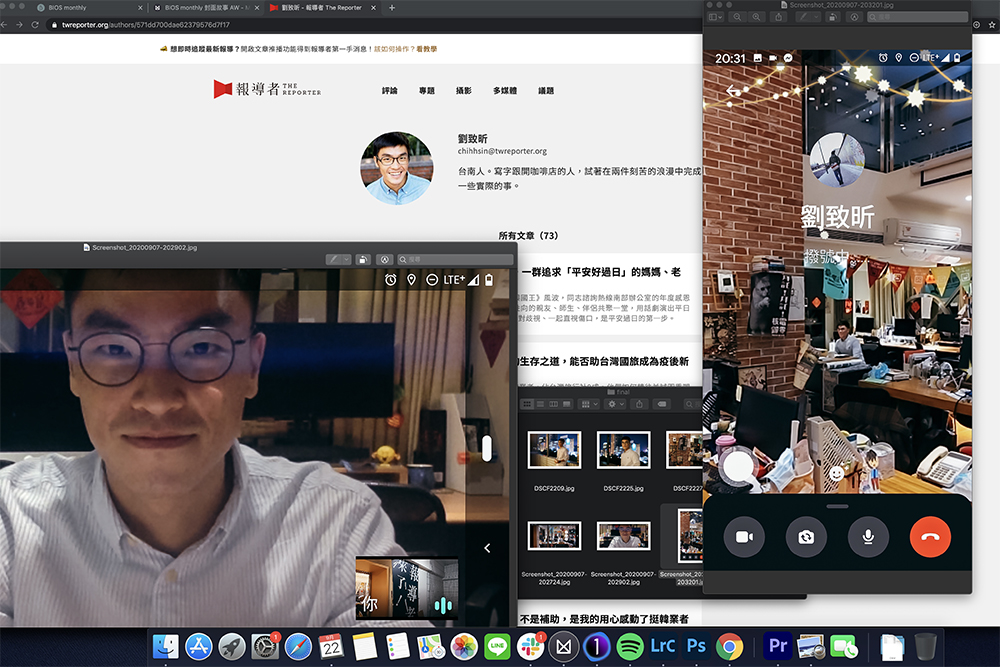

【後記】
劉致昕所關注的題目,在今年集結成冊。書名很長——《真相製造:從聖戰士媽媽、極權政府、網軍教練、境外勢力、打假部隊、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副標那麼多字,也確實因為他在意的有那麼多:光是「製造」假新聞的人,就有各種視角、各種原因來到這裡。書中也收錄網站上沒有的篇章,談政府小編的不得不然與為難。在公民社會想出更成熟的解法以前,他以《真相製造》逼近問題的現場。
【劉致昕的新聞推薦讀】
《海上焰火》(Fire at Sea , 2016)
記錄義大利一個六千人規模的小島,默默處理二十幾萬非洲往歐洲的難民,但島上只有一個醫生。我很喜歡這部片的記錄方式,它從那位醫生的日常切入,拍到了這個醫生的堅持,也拍到了政治不正確的船裡面的情況。有時視角看一個義大利小孩的日常生活,有時也很血淋淋地讓你看到難民船艙裡面全部都是屍體。
Tilly Remembers Her Grandfather /The Daily
這則報導用非常溫柔的方式讓大家想起來,很多人正在疫情中受難。主持人帶著小女孩回憶外公,小女孩說「我有快樂跟難過兩種情緒;快樂比較簡單,因為我不知道難過的時候該怎麼辦」。又說,如果大人都可以在她面前告訴她,他們也很難過,或是告訴她難過的時候可以做些什麼,她就會覺得比較容易。講的是肺炎之下集體的 trauma,為了「維持正常」而沒有說出來的。
《立場新聞》7.21 直播錄像
這個直播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媒介,我覺得可以拓展大家對於報導的想像,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書籍
《背離親緣》、《重返天安門》、《我必須獨自赴約》
◤ 帶讀者看見無數創作者 B-Sides 的台灣媒體,第一本專訪精選集 ◢
收錄受訪者
音樂影像導演・郭佩萱|導演・黃信堯|演員・巫建和|設計師・洪彰聯|《新活水》總編輯、作家・黃麗群|YouTuber・反正我很閒|Podcaster・百靈果 News| 《報導者》副總編輯、記者・劉致昕| 青平台基金會董事長・前文化部長・鄭麗君|樂團・珂拉琪|攝影師・周墨|音樂製作人・黃宣|設計師・林小乙|作家・張亦絢|寫作者・前午場酒店小姐・少女A
- 全新再訪|訪問做完了,然後呢?我們再度聯繫訪後半年到數年後的受訪者,聽他們再談自身的訪後境遇。初訪時曾想像的未來或尚未解答的探問,如今是什麼模樣?
- 親身回望|如果可以親筆修改一篇關於自己的訪問,你會如何下筆?本書提供收錄受訪者修改、註解專訪文章的權利,並將修改與原文一併保留,展示此刻與訪問當時受訪者心靈的錯動與輻合。
- 職人特輯|「Sprinkles ——現場一百答(不是專訪心法)」邀請在台灣編輯.攝影.企劃・訪問領域深入經營的執業者,收錄「對自己影響最深的訪問」、「被要求修圖最離奇的地方」等十五問一百答。
- 精裝收藏|設計師莊皓操刀精裝全彩裝幀,以皮紋荔采紙暗示時間的壓刻與皺摺,如同歲月的肌膚。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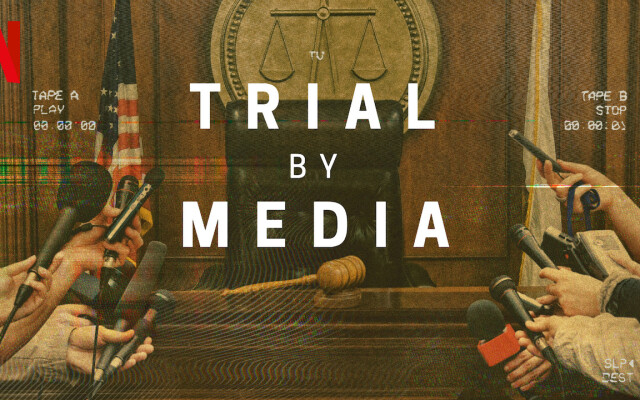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