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做婊子了——專訪小說家白樵,舞者被手術刀切開以後
「十三歲那年,他決定成為一名婊子。」
我問白樵,在自己第一本小說集裡,真正最喜歡的句子是哪句?他用書中輯二唯一一篇作品〈婊子,十三〉裡的句子回答我。
我和他都知道,在新書甫出版的宣傳影片裡,當他回答同一個問題時,答案不是這個。影片裡他唸了另一個句子,然後說:「其實我原本自己最喜歡的話是另外一句。可能有尺度關係,就不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寫作資歷五年,跳舞資歷二十年。2009 年他與政大熱舞社歷屆社員合組舞團 Lonely Taipei,首戰參加台灣舞社之聖杯台大盃,就拿下第二。2017 年,Lonely Taipei 與同為舞賽常勝的舞團「小少女」成員,以及《時下暴力》導演廖哲毅合作的舞蹈劇場《陰性書寫 l'écriture féminine》讓多少文青跨出觀舞舒適圈,於是有了 2020 年的《陰性書寫ll 黴》。節目簡介上,與「舞者、演員、牙醫韓寧」和「戲劇指導鄧九雲」並列,他的頭銜是「鬼才白樵」。
何以才?寫作第二年,他就拿了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去年三月,大學雙主修廣告的他自行研究台灣出版社新人行銷佈局,最後決定把書稿投給時報出版,彼時他前有時報、鍾肇政兩大文學獎加身,後有阿盛、袁瓊瓊寫作班人脈,卻硬是要把稿件寄到出版社公開信箱。「我媽說,你為什麼就不叫他們幫你推薦一下?我說我不要!我想要完全靠自己。」稿子竟是這樣孓然一身地被時報主編羅珊珊從信海中撈出,走了一趟自主海選兼晉級的路。
何以鬼?他說自己編舞奇快,一天可以交出一分鐘的編舞。不只舞,他交件時一併把舞者要穿什麼衣服、妝容如何搭配、燈光氛圍什麼全定下來。早些年 Lonely Taipei 裡學弟妹們練習,他雕舞時叫他們停:「欸,妳那個動作再不調,看起來就是公園大媽。」有個學弟身材豐潤,白樵朝他叫:「欸XXX,你跳舞真的很像肉圓。」本來團裡還有幾個非政大成員,被他這樣一叫,全離開了。
現在說這些是話當年,他三十六歲了,不當婊子了。長長的過去摺疊為一句話:「生病之後,脾氣變好了。」三十歲那年他被一場病一刀切開,鬼之白樵被那病超渡煙消雲散。剩下的白樵走進文學寫作班,才發現原來自己可以寫。
殼
出一本文學書是在心願清單上打勾。《末日儲藏室》翻開第二頁就印著「謹以此書獻給我的母親,陳淑娟女士」——新人首作就這般今生今世地獻詞,要嘛多情,要嘛是真有了沒第二本書的打算。
兩三個月來,他在 Instagram 上連發打書文,貼文下朋友們的留言對他忽然成為作家都訝異,有人還問「你寫的嗎」。
他說自己從小朋友就多,但他「是那種事情還沒做到一個程度,就不會想去說它的人」。寫作伊始,身旁鮮有人知,大家心中還是那個從巴黎回來之後接案編舞的白樵,直到他的 IG 某日出現一張剪報,是他的作品刊在聯合副刊;一如 2013、2014 年他準備到巴黎讀研究所,朋友們都以為他是出國去玩,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我就說,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欸,我是去唸書的。他們又問,白樵,你什麼時候會法文的?」
提筆寫作唯一的線索,是他多年來在臉書上談陳淑娟女士 a.k.a. 白媽媽對他的閱讀啟蒙。白媽媽帶小時候的白樵看崑曲《牡丹亭》的錄影帶,書架上是莒哈絲,嘴上的教誨是「你要看台灣文學的話,看張愛玲跟白先勇就夠了。」極其偶爾,白媽媽才會「徐國能的〈第九味〉,你給我一個字一個字讀完」或者「去看楊邦尼的〈毒藥〉」。
「我們不是母子,是摯友。」除了文學,白媽媽(「同樣是水瓶座的白媽媽」,他強調)顯然也言教身教。白樵臉書上曾有一系列白媽媽驚世語錄:
「關於一夜情 白媽媽說:不就是被對方當了小便桶嗎 有什麼好值得說嘴的」
「『你要知道,要我在書店幫你買李昂的《路邊甘蔗眾人啃》,對中老年婦女如我,需有多大勇氣。』」
「白媽媽語出驚人又一章:男同志?不就是哪裡好吃好玩哪裡好幹就往哪去嗎?」
母親很近,但文學依然很遠。成年白樵懂得回推白媽媽以《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和《世界是野獸的》,但少年白樵對台灣文學,越讀越失落:「我沒有在別人的作品裡面看到我正在經歷的,不管說污濁的,或者是很悲下的情緒和情景。世界很美好,大家都是粉粉亮亮的,我覺得這個東西跟我是完全背道而馳。」
污濁之於他,是小五小六租錄影帶時偷偷把《家有囍事》外殼裡的帶子換成《異種》和《從地心竄出》帶回家;是大學畢業時在陳界仁《殘響世界》展中一幅清朝末年接受凌遲酷刑的犯人照片出神;是國中時發現自己的性慾如斯巨大,大到想著要伸手去摸街上的流浪漢、幻想即便自己被陌生人侵犯也搞不好是開心的。
那時他最想要活在裡頭的電影是《老師不是人》:「就是帥哥美女,然後外星人跑到他們體內,那怎麼分辨他們是不是外星人呢?拉 K。如果你拉 K 之後沒有爆掉,就是正常人。」喬許哈奈特費洛蒙最盛時出演的 cult film,金髮、藥、觸手、斷頭、性,藏在 YA 片的殼裡,如外星人藏在高校生的身體,亦如對性與穢的慾望藏在白樵。
巴黎,萬華
外在白樵是殼,藏成了他的習慣。分手時他常從伴侶口中得到一句話:「白樵,我完全不懂你」。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很傷,但是我知道他們的意思。我每次約會都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好,保持在很精緻的狀態,然後我們去看電影啊、吃飯啊、發生性關係啊,我的狀態都一直很穩定。他們覺得這個東西有點恐怖,覺得這個東西的背後是我在拒絕他們。」
父親的家族在中美斷交時移民美國,母親的家族多在香港,白樵同輩的表兄弟姊妹多赴美留學,童年時的白樵週末幾乎與外婆一起在萬華度過。還未改建的剝皮寮滿是破舊平房,賣豆漿、蒸包,小吃攤和站壁小姐與遊民在街上鄰居。西門町還衰敗的時候,白樵聽大人說千萬不要去那附近,不然會被「怎樣怎樣」,但白樵喜歡那種古老破敗和髒醜。反倒是台北其他地方灰濛濛的,連破敗也不擁有。
去巴黎,原本打算再也不回來。與愛人朋友之間的疏離感並非故意,只是二十多歲的他總是沒辦法放鬆。「那個緊張好像已經深深地鑲嵌在我的肌肉裡。有次我媽來巴黎陪我住,睡同一張床,結果隔天早上她嚇到,因為鬧鐘響一聲我就直接跳起來,整裝出發做事。她說,你知道這樣很不健康嗎?」
.jpg)
他半開玩笑,說搞不好正因如此,他才對性愛如此執著。成年後他成了 Trysexual,人類學般地和各種性別、人種、身體的對象做愛,想要知道那是什麼感覺。性高潮的瞬間,那幾秒鐘的放鬆令他成癮。《末日儲藏室》裡,小說人物的初始動機往往有對「潔淨/不淨」「神聖/不聖」的迷惑或叛逆,而性則是這個動機轉化為行動後的展現。〈少女伊斯蘭〉中寫到街上遇到陌生男子自詡性器奇大,〈Leïla〉中寫到與非法移民交往,都是白樵自身經歷,也正如白樵自己在實踐幻想後常有失落,原將某種世俗的骯髒視為掙脫或抵抗的方向,卻在嘗試後發現骯髒也不過如此。
「那個在路上遇到的陌生人,現實中我真的把他帶到我房間。可是看了,摸了,滿足那個好奇心之後,我發現我對那個人一點慾望也沒有。」他終將再次回到尋求下一次高潮的歷程,在那之前再次歸返矜持與壓抑。
若非有出書的計劃,打算藉由優勢題材在文學獎有所斬獲,白樵根本不會在散文裡寫自己的家族史:父親是同志,在白樵出生前患思覺失調,這兩件事連熟識十年以上的朋友都並不完全知道。「我不喜歡販賣悲傷,說欸我爸是精神分裂加男同志,小時候我被我爸家暴過,大家來認識我,怎樣怎樣的。」
「以前我會覺得,你的事情對別人重要嗎?為什麼要去聽你的事情呢?我對別人透露我很在乎或者困惑的事情,對別人來講可能不痛不癢啊。我乾脆就放在我心裡。」
家與家族對他而言從不在此地,慾望的無人可說和無須說則讓他急欲逃離台灣,「我一直想要到一個沒有任何人跟我有關係的地方。我想要切斷所有一切的連結,在一個全新的環境去過生活。」
巴黎倒數第二年,他得了肺炎,日日咳嗽。但歐洲看醫生要排兩個星期,他想算了,吃成藥壓著,把病也放在身體裡。母親為什麼會決定和男同志結婚?他從前是一百個不理解。白媽媽認為婚姻並不一定由愛情組成,用愛維繫的關係也不長久,更需要的是陪伴;婚前的白爸爸身高一百八,長相酷似黎明,懂打扮,待陳淑娟女士如閨蜜。咳咳。他對她也有感覺,兩人協議結婚,婚後他想要有個小孩。咳咳咳。肺炎拖了一年沒好,後期白樵竟連爬一樓樓梯都會喘,不管去多近的地方都叫 Uber。2014 年 12 月,他的咽喉發炎嚴重,無法進食,到了連喝果汁都在灼燒的地步。白媽媽在電話中對他下最後通牒,以斷絕金援要脅他就醫。
白爸爸在白媽媽懷白樵時確診思覺失調,白媽媽說,那好像把所有禮教賦予一個人最好的東西都奪走,剩下最原始的部份。巴黎診所裡,醫生檢查完白樵,說他無法處理,要叫救護車轉大醫院,於是白樵連人帶椅被救護人員搬出診間,上車前他看見聖誕假期前夕的巴黎街頭,像他初從戴高樂機場降落,搭計程車要到住處時看著車窗外想,天啊,好醜,好糟糕的一個城市,與歐陸同樣迎來許多移民,巴黎卻顯得特別狼狽。怎麼會是這樣子?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我怎麼可能 drama 到這種地步。我到底把我的生活過成什麼樣子?」
醫院裡,醫生說白樵得和一台機器一起睡一陣子,大概兩三天。他傳簡訊給白媽媽報備,然後入睡,再醒來是三個禮拜後。
期間歷經氣切急救,體重剩四十三公斤,無法說話,連 iPhone 都拿不起來。醒來第一眼看到母親,他眼神只有困惑:妳怎麼在這裡?
白媽媽每天幫他拍一張照,秀給清醒的白樵看,「我跟你說,大體就是長這個樣子。」兒子差點死去,依舊語出驚人。白樵後來才知道,昏迷時父親來過電話給母親,談著談著,說:「好吧,我可以匯三千塊美金過去,但我要先和主治醫生說話。」為什麼?「我怎麼知道妳們是不是在騙我!」白媽媽氣瘋,誰要拿兒子的性命開玩笑?從此她再沒和白爸爸聯絡。
白樵自己則瀕臨崩潰。一個跳舞的人連筆都拿筆不好,站著如廁時渾身發抖,旁人告訴他氣切後講話可能要練習半年才能恢復。所幸身體比想像中堅強,復原情況好。真正改變的是他的心。
「雖然研究所的老師因為我先前表現很好,所以期末論文沒交也讓我過;但那時我媽簽證要過期了,我沒辦法想像當時我要一個人待在巴黎等她重辦簽證再過來照顧我,然後把書念完。我只想回到台灣,一個我完全可以熟悉、完全可以放鬆,什麼都不管的一個地方。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台灣像家。」
歸返的他者
胸前那一刀,切開的是他的殻。昏迷時,他不停作夢,夢中自己一直在巴黎到處奔跑⋯⋯2015 年的大安森林公園,白媽媽帶著白樵一步一步走路復健,想找回他可以跑的那雙腳。而甚至直到這時,還有朋友不知道他到底發生什麼事。自己前半生的藏身與排拒,病後睜開雙眼看得更清。

不能跳舞,倒也不是提筆的理由。復健後報名寫作班,為的是追星:年少時對台灣文學疏離的白樵,獨愛袁瓊瓊、蘇偉貞、蕭颯。剛回台灣見袁老師開班,報名時已經額滿,承辦人說隔年再來,白樵本以為是客套。第二年真收到通知,只不過課程主題是詩。他倒也坦然,反正是去看偶像,管它詩不詩的。
在班上,他下定決心,課程結束前至少要寫一篇小說給偶像看。「其實很單純,就是想要寫自己喜歡的東西,給自己喜歡的人看。被打槍就打槍無所謂,反正人生清單打勾。」
寫給偶像看的第一篇小說,正是〈Leïla〉:
「她一直不瞭解,為什麼是蕾拉。可能是月亮聯想起夜,而那一整片悶黑就這樣砰地重壓她肌膚上,墨傾了,她滿身濕淋。她是一個頸子上被套著阿拉伯名字的黑人,她想,為什麼母親不挑個阿依薩塔,阿敏娜或是她姊姊法杜那樣稀鬆平常,來自黑暗大陸之心的名字呢?逃亡時,母親仍眷戀哪個摩洛哥青年吧,她想。蕾拉不敢過問姊姊關於早逝父母的種種,她感謝雙親在躲避盧安達內戰時一路成功遷徙至巴黎生下她們三姊弟。」
「『為了穿越,你必須先被穿越。』是誰的格言呢?這是在哪本書抄下的句子?蕾拉記不得了。」
無畏地將異國經驗和語境作為陌生化敘事,揭示角色作為他者與其所在世界的距離,同時也是白樵作為他者,與抽芽於台灣鄉土的小說作品的距離。袁老師告訴白樵,他已經寫得比不少線上作家好了。是這句話,才讓白樵覺得自己說不定可以繼續寫。
小說路並不全是簇擁。後來參加小說班,他有點驚嚇:「為什麼大家寫出來的東西都這麼像?二十幾歲的女孩和年長的阿姨,作品情懷都一樣,想在生活中找到某種微小的幸福。」讀慣外國文學的他,也被前輩指教過「寫些和本土相關的東西比較好」。
倒是白媽媽喜歡他的小說,討厭他戰略用的家族書寫,於是只推書不推散文。散見於聯合副刊、《文訊》和《字花》,命名上總以「XX者」為題的隨筆,寫著寫著竟也自成一個世界。相對於小說的繁複、遮蔽與性揭露,寫實的白樵不避談各式「遺事」,抽屜似地拉開自己:
「小學末梢時光,熟絡於同性中的,不是我,是陳。永復迴盪於前三排,孱弱腿腹上裹覆無血色的肌,並喊著拔尖聲音的我,在班上,並非全然孤寂。我佔領兩名,比我更瘦更矮聲音更細近似異性的同性傭兵。我們歃血,成團體,異形畸零人怪胎相濡以沫,抽屜深處藏有幾支紙條驗證我們的情誼。」——〈共慾者〉
「相片上,母親的姿態讓人印象深刻。三、四歲的她獨坐外公臂彎,短髮微捲,短袖白衣深色短褲,單手叉腰,眼裡,卻瀰漫成年女子獨佔感情時的傲。外公寵母親,能為她花上公務員單月薪資的蕾絲洋裝,和風糕點與對岸禁書。他扛她,揹她看野台戲南北管。身、性靈、物質三層面完美佔據。幼年的她瞇眼,鼓著腮幫頭微仰時透出的,是睥睨,而非孩子的任性。那神情激惹嬤,與同母異父的大阿姨。」——〈啖鬼者〉
奇妙的是,儘管書寫過父親許多次、不斷與母親查核各種時序問題,直到現在仍有什麼阻擋白樵將那些東西重組起來。最深的記憶仍是一團霧,好像他必須拒絕它們變得清楚。

公園大媽,超嘻哈的
舞還是跳的。雖然 Lonely Taipei 的團員們隨著年齡,打拚事業生兒育女去了,白樵仍在編舞。近期操刀罕病基金會的肢體發展計劃,為病友開發劇場身體,頗為感動,只因與 Lonely Taipei 當年成軍的理念相似:想讓身體並不拔尖完美的人跳舞。「為什麼只有身體好的人可以跳?當時就想要反抗這件事。」
他身體也沒有以前好了。去年回政大演出,生平第一次在舞台上跌倒。但他依舊是白樵學長,團員們喚他精神領袖,「我就說,就是因為跳舞無法當領袖,才只能當精神領袖了吧!」
高中時受小甜甜布蘭妮感召,想跳和她一樣的舞,因而加入熱舞社,卻發現世界並不允許他那樣跳。「男生就是學嘻哈之類的,女生才學爵士;那時候男生跳這種舞都是插花性質,認真跳這個的人會被視為變相出櫃,整個團體的壓力是很大的。」直到某日,他看見某位陌生學長在台上跳了一整支 jazz。2014 年,大病前的白樵在 Facebook 發文回憶:
「有一位來自基隆的長髮男子在街舞比賽中跟其他女生組團,當眾跳 jazz,他沒有其他名字,他就叫做爵士男。⋯⋯那是一種比拿著麥克風對大家吼叫我是同性戀還需要勇氣的情境 。但,爵士男,一百六十公分左右的身材,飄逸的長髮在台上打出比女生更精準強大的力道,那些瞬間,在台下的我,高中生,感動異常。很像目擊某種先知,在告訴你,在傳導一種極私密的微小眾信仰,他用他不畏忌人言的行動告訴你,做自己。」
後來白樵成為政大熱舞創社以來第一位男性爵士教學。而大病之後,他更理解在舞中做自己,比跳到盡美更重要。「公園大媽的舞,我現在完全喜歡看。朋友傳抖音廣場舞給我笑,我就回說:我覺得這個超嘻哈的。」
「你的身體、心理為什麼不協調?那是沒有人可以模仿的。你之所以會不協調,是你的生命當中某個東西造成的,那個東西就是你。我覺得那個非常非常珍貴。」
病讓他領悟,也讓他鬆開。「生病後我朋友們責備我,為什麼你病成那樣子都沒有跟他們說。我說我打擾你們心裡會很愧疚,他們就告訴我說,如果你不向我們發出一些訊號的話,那才是真正傷害人的東西。」
《末日儲藏室》是他對台灣文學的叛逆,也是歷劫後學著蛻殼的他初次發聲。「我一直相信最污穢的地方可以找到最神聖的價值,而神聖的東西也有污穢的地方。我去寫很多大家覺得挑戰到某種道德極限的東西,有時候也不一定是要去找那個神聖的芯,但至少我想要像穿耳洞那樣,越穿越大,讓大家再接受多一點,再多一點。其實文學可以,它可以講這些東西的。」
縱然在宣傳影片裡礙於尺度,朗讀了另外一個句子。但他心裡知道,自己也在等一個什麼都可以說、不必藏身的時候。
「每件衣服,像不同形容詞,碎落在顏色、材質、剪裁、針法與紋路間。妳伸手扳開沉甸的門,咿呀作響。妳乾咳,擤嚏,撢去服飾上積累的塵。妳思索是夜該將自身扮成何種句子,好敘述 cela。cela 一詞,中文直譯『這』。能將繁複長句摺疊,收納為簡單的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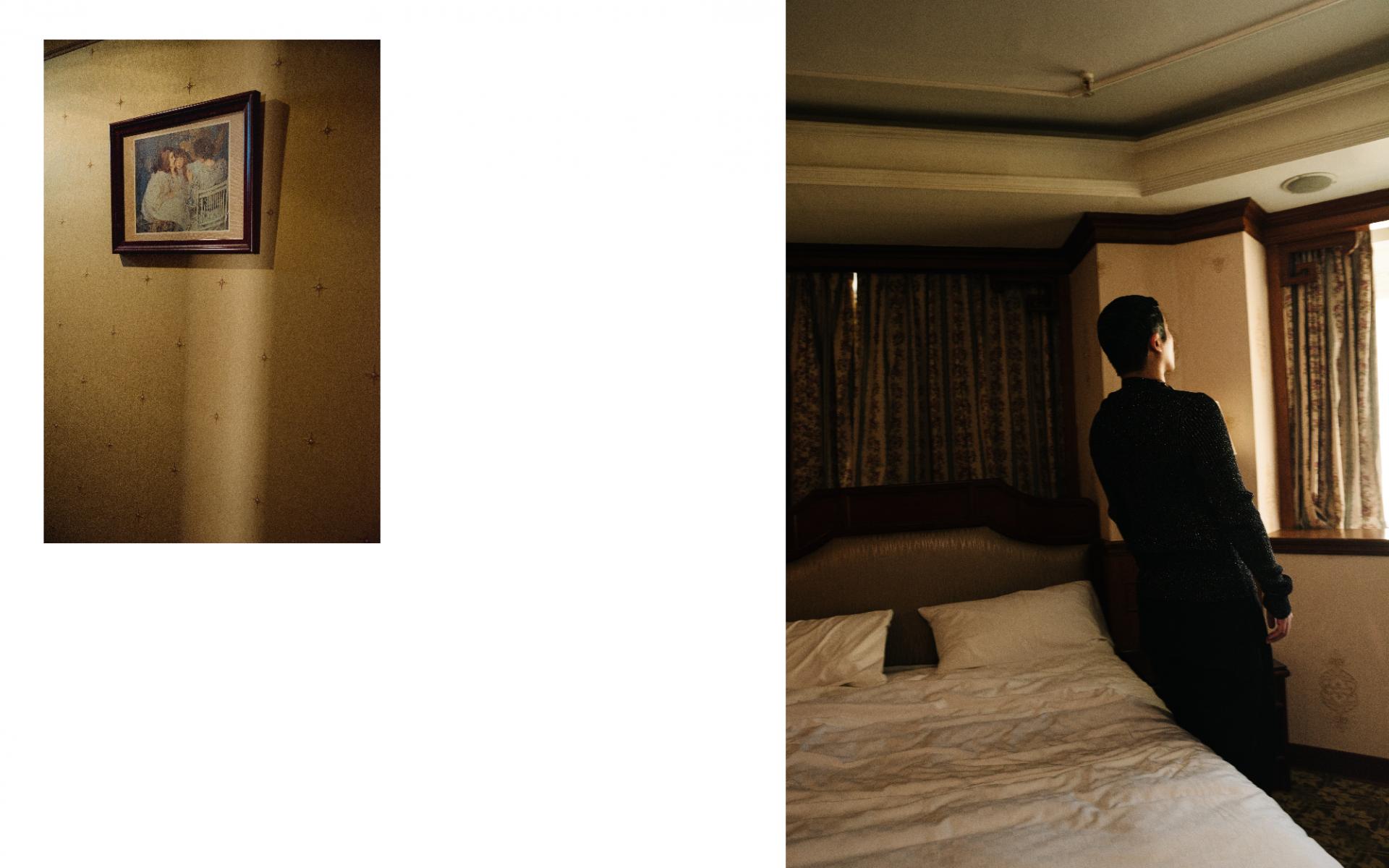
【白樵】
一九八五年台北生,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廣告學系畢,巴黎索邦大學斯拉夫研究碩士肄業,現從事翻譯,編舞等工作。曾獲時報文學獎首獎、鍾肇政文學獎首獎等。作品散見《中國時報》、《聯合報》、《幼獅文藝》、《聯合文學》各大副刊及文學媒體。
《末日儲藏室》

作者|白樵
出版者|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2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