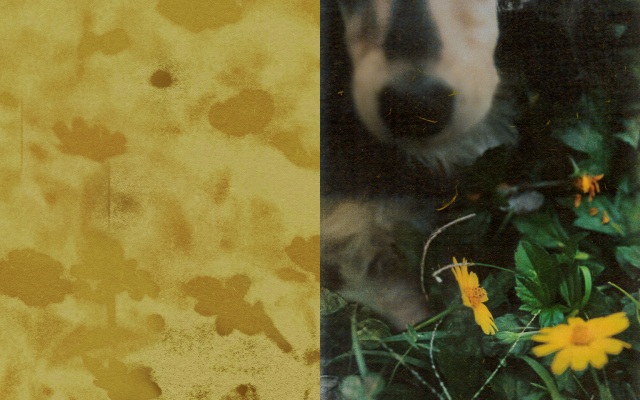廢墟|
身體上雕刻的花:側記 RCA
「不甘被欺負/很痛/所以抗爭」
──RCA工人、黑手那卡西〈美麗的花朵〉
距離 2014 年 12 月 15 日的一審結辯,在寒風中唱出心聲的冬日已過去兩年,2015 年 4 月 17 日雖宣布勝訴,但她們仍在這裡,仍有話想說。2016 年開始,二審揭開序幕,開庭前,來自各地的 RCA 工人搭著火車抵達台北車站,在捷運上她們聚在一起轉車,早早就在高等法院門口等候,裡頭的法警們望著外頭群聚起的女性,她們等待著午後的開庭,人數眾多,排隊登記、領旁聽證,這一次,她們不再遭拒,可以坐到位置上。
法庭分成主法庭跟延伸法庭,坐在主法庭裡的是律師團以及自救會的主要成員,只是預備庭,位置上僅有一位法官,聆聽兩造說法。律師每說一句話,便會與法官反覆核對記錄的內容,重複一次、兩次,一審時已經言明過的內容仍在此處不斷複述。午後的時光,令人忍不住打起盹,但席間的工人們仍是努力睜開眼睛、打起精神,希望看清楚、聽明白,自己究竟經歷了什麼。
「RCA 桃園廠於 1992 年關廠,在 1994 年發現污染案後,RCA 訴訟代理律師指出 RCA 自當時起即積極參與整治、花費鉅額費用,並無逃避責任,對此,RCA 員工關懷協會律師指出:於 1998、1999 年時,RCA 員工關懷協會前身自救會成立不久後,RCA 在台公司匯出 32 億台幣至法國,去處不明,RCA 訴訟代理律師說明此為「合法的資金調度」,儘管勞委會、環保署在污染事件爆發後,皆要求投審會發函至 RCA 不得匯出資金但未果。截至今日,RCA 在台仍保持名下近無資產。土地已然受到傷害,而在其上的人所受之傷害至今仍未獲平反。
因尚有許多證據以及股權資料不明,法庭上的攻防仍持續,下次準備庭於 4 月 15 日下午 2 點 10 分於高院舉行,RCA 工人的路繼續前行,在法庭中旁聽的工人們,聚精會神地看著庭上,儘管可能法庭上的交戰難以辨明,仍一心企盼著在廠房中所耗費的年輕歲月與病痛,能夠得以清償。」
──2016年3月21日台北訊
在一審宣判後,追加起所謂的「二軍」,RCA 關懷協會趕在二審開始前,繼續尋找曾經在 RCA 任職過的人們,可能是員工,也可能是親人已經離世的家屬,人數從原本一軍的五百人,多了一千多位的二軍,每一個人的資料整理都成了浩大工程,必須有勞保投保資料、還有病歷,一落一落地,從四散的各地啣回來,這些資料收整回來後的歸檔、分類,也是由 RCA 關懷協會的志工、幹部們進行,因此儘管不是開庭日,曾任職於 RCA 的大姊們也會出現在辦公室,只為了把累積的文書資料細細分好,這對於曾經在工廠中進行各類加工的她們,似乎不太是件難事,除了已經進入電腦文書的時代,還是造成了些困擾。
每一次開會都是大陣仗,要核對多人的資料,準備的電腦至少都要三、四台以上,查詢 A、B、C 組別,從已逝、發病、未發病與眷屬一路羅列下來,員工的資料、投保勞保的資料,有些是已經逝去,便只能以戶籍謄本來辨認存在的痕跡;有些囚困在疾病中,病歷資料連寄來的資料夾也承載不住。這些是大姊與義工們,一個字一個字地 key in 入電腦,為的是一個都不能少。
一日,抵達工傷協會進行訪問,雖不是訪問 RCA 女工,但這一天的早上,劉夕霞大姊跟馬大姊就來到協會整理資料,在訪問結束、準備離去時,夕霞姊順了順我的頭髮,說:「要多保重。」站在門口,夕霞跟馬大姊正準備去買午餐。女工們的年紀隨著時間過去,從少女變成母親,年歲過去、臉上的丰采淡去,但溫柔依舊,這裡頭的她們有些是母親,有些曾經想要成為母親。
在 RCA 工人的量化調查中有許多人曾經流產、不孕、產下死胎,化學藥劑的影響也證實了與此些疾病相關:氯化乙烯等物質在職業病流行病學研究中,曾告知與流產率增加有關,而在 RCA 廠中的主要物質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裡,以三氯乙烯致肝癌、四氯乙烯導致不孕與高流產,滲入土壤與地下水,化為每一個日常會碰觸到、長存的物質。
資料中,有著每一個曾於 RCA 任職過的工人,無論男女,附上當年的投保資料、幾年來的體檢資料,若已然逝世,便會附上戶籍資料,證明眷屬關係,一大落的資料之中,能夠起多少效用,依憑著律師、法庭的判斷,可能到最後也只能棄去,存下薄薄幾張。
2016 年末的法庭裡,終於來到了傳喚專家證人的時刻,面對著 RCA 等公司請來的專家證人,言之鑿鑿地舉出毒理、病理、公衛相關資料,指出工人的罹病與工廠無關,可能是自身的病史或遺傳的可能。儘管,美國北卡樂瓊營的資料被用以佐證,相仿的例證已在美國獲賠償。面對法庭裡專家們的背書,協會的念雲仍不放棄地對著 RCA 工人們喊話:「他(RCA 的專家證人)覺得自己是權威,可是我們是不是權威?」她說,「我們在 RCA 工作他沒有;我們聞過三氯乙烯,他沒有;我們喝過(汙染的)地下水,他沒有。」
我想起了一個年輕的藝術家,她在 RCA 廠廢止後,仍找了個機會回去,帶著已經認識的、女工們的記憶。她挖掘出廠區的泥土,自行燒窯成食器,在碗身刻上 RCA 三字,銘刻下的字也代表著生物分解度低的化學物質在土地中的長存,無法被去除,環境中的、身體上的。帶著這些器皿,她幾次用這樣的碗承裝食物,遞給前來參觀的人們,一碗簡單的魯肉飯,但是用受污染的土壤燒製而成的碗承裝,是吃?還是不吃好?
但在彼時,她/他們是無從選擇的。每一口空氣、每一口水、每一口浸潤身體的組成,都是污染物,從未知悉,也從未有人為此感到抱歉過。
會有人感到抱歉嗎?
每一次見到 RCA 的大姊們,我總是忍不住低下頭,儘管,她們總是笑得比我還要燦爛。
在二軍抵達的時刻,有些面孔是陌生的,在第一次戰役後加入,找尋宜蘭廠、其他廠房的工人也並不容易,許多是透過人際的紐帶才找到。來到櫃檯前,有些面容就這樣相認了出來,問起彼此過去是否在同一個單位,而現在,又到了哪裡。
假日時分,聚集在借來的桃園市政府大廳裡,一名曾是 RCA 女工的女子這樣匆匆趕來,身上還穿著印有現在工作場所廠牌的衣服。她說,做到今年滿第十四年,明年終於可以退休,但在這十數年的過程裡,沒有辦法請假,要做一天十幾個小時的班,今天能夠來參加與訴訟有關的說明會,也是請假出來的。工廠與工廠之間的過渡,似乎已是自然,為的是想要持好一個家。
幾次的說明會,得力於最多的仍是身手依然敏捷的幾位女工,但隨著年歲逐漸增長,也不若以前那樣靈敏。
仍恨著嗎?忍不住這樣問道。
雖然仍有阿姨留著 RCA 當時送的黃金戒指,以及幾紙證書,在當時潮流的發展社會裡,她們是打扮得風尚的女工,就算到了今天風采也依舊未減。病後,有些癒合的,但仍留下些什麼。其中一位說:「疤痕是身體上雕刻的花。」只是那花開得豔極了,有些人看不到就已經離去,倖存者只能如此與之共存。
每一次說明會後,大家都留下來餐敘,看看彼此的模樣。學生與志工們受阿姨們照顧甚多,常常提出要載我們回到火車站返回台北的提議。其中,有位女工的先生開了三十幾年的公司,是自己的公司,不必再在生產線中度日,能夠專心面對眼前的戰役、扶起身旁的人們。
風中美麗的花朵,以工人的生命構築。有些人的花已然綻開,也許是無虞的生活,也許是孱弱的病體,在一片花海中,每一朵花都是堆砌如今社會樣貌的其中一朵,無法忘記,也不應被忘記。
【廢墟】
不知怎地,人離去後的建物因為失去人氣,會逐漸變得歪斜、傾頹,最終化為一片廢土;而人儘管離開,仍有部分殘存在那裡。我想寫的,也許是建物,也許是人,而這兩者其實並無二致。
【佩妮誰】
1990 夏天生,來自高雄,讀關於農業的科系,卻始終不務正業。書寫散文、小說,以及報導,喜歡聆聽人與老屋的故事,以書寫抵抗遺忘。
部落格:日常之愛與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