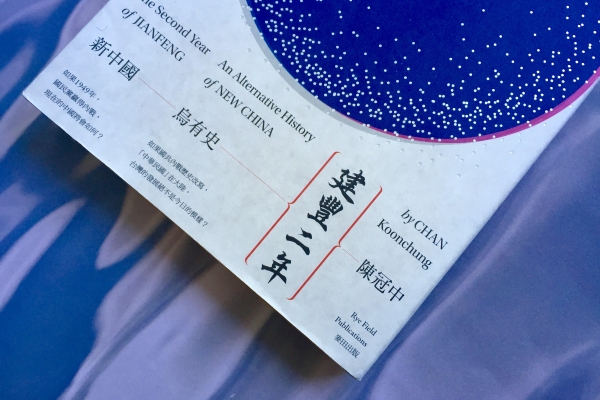把寂寞暫時地安放:馬欣對談鄧九雲(下)
火花不斷的對談來到後半,我終於有機會切入正題:延續去年《反派的力量》,馬欣在今年四月再發表《當代寂寞考》,從上一本寫反派到這次關注孤獨者,我問寫作的出發點改變了嗎?她想了想之後說,其實她寫的都是「怪胎」,沒有什麼正派反派之分。「我想寫給自認是少數的人,可能像我這樣,看起來無害沒什麼太大的適應問題,但內心覺得自己是怪的,不同於主流。」當她發現自己的想法和別人分道揚鑣,就盡量在社交上掩藏,「會收得好好的,但是它變得很巨大的時候就必須寫出來,那是天生的衝動。」
這東西累積多了,就想出一本給怪胎的書。「當社會處在一個巨變的狀態,很多人都無法接受或定位自己,感覺到無盡的焦慮,就想寫書告訴大家:其實怪是正常的,因為這世界比我們更怪。它已經整個歪掉了,如果你還是跟著危險的價值走,那才是最怪的。」
她說其實台灣的變化,她在兩三年前就嗅到了:「寫作跟時代脈動有關,那時候我感覺所謂『正能量』和它產生的排他性,已經滿載了,整個檯面上溫情洋溢,但明明有些人很孤獨很邊緣」,她看到小丑和《踏血尋梅》,覺得如果不把他們的想法寫出來,做一個寫作者又是為了什麼?「又不是要討好社會。」這時候,她就會很想用針去戳。
當然,最常得到的回應是:「幹嘛那麼沉重?」但其實她一點也不覺得沉重。「有點像舉重,你舉得上來就不覺得重,就會發現還可以挑戰更多,而且總比你一直害怕、不去直視得好。」面對過度樂觀的社會,她覺得一定要有個力量平衡,「不一定是悲觀或冷冽,但如果大家都裝作沒看到黑暗那一面,那就變偽善了。」
所有的文字都是必然
馬欣還舉前陣子討論度極高的《哭聲》為例,說那部片正中我們這個年代的中年人,「不論在什麼崗位上,都處在一種焦慮(panic)的狀態」,九雲聽了直附和:「我現在 33 歲,回想我小時候看書上寫 33 歲,都覺得那已經是很成熟、很穩定了吧?結果根本沒這回事!」她有時會懷疑,是不是自己的問題?但馬欣觀察她身邊多數在身份/生活上比較「長大」的人,覺得他們也缺乏足夠的內在去撐起。「成家後壓力是更內化的,但其實我們這一代中年時剛好碰到時代轉型的路口,那種自我懷疑的壓力其實更強烈。長大了其實不見得變聰明,反而是發現要學的更多了。」
我轉而問九雲創作的動機,她想了一下說,自己的創作也是剛剛提到的身份、身體等等焦慮的出口。她不是為寫而寫,是「真的很想要什麼而開始去寫」,所有的產出都是必然,「因為是必然所以我完全不會懷疑它,寫作這件事就是要從體內流出,很自然的,完全沒辦法偽裝。」
這樣的九雲,加上多年來經歷的各種「直播」,讓她練就了沒有包袱,不去在意別人的評價。「我整個人最能抵抗批評的,就是我的文字,對我而言那是發自內心真實的模樣,如果你看不懂或覺得『到底在寫什麼?』那我是完全沒有感覺的。」別人不理解、或不能接受真實的自己,她完全不在乎。
令我們羨慕的是,她總能很自在地寫自己想寫的,而且很會抓時間:「每次劇團去巡演,一週一個城市,只有三天工作一天移動,剩下幾天就窩在旅館裡寫東西。每天吃完早餐就躲進房間。」因而九雲的幾本書都是在舞台劇期間寫出來的,或譬如在機場過夜,時間很零碎又必須保持警醒,就拿出來寫。「但現在漸漸無法了,因為寫越多越容易重複,需要有準備,或有 reference 在旁邊。」
鄧九雲:「我需要一個第一時間的讀者」
這樣源自憂愁,和源自抒發的兩位寫作者,共同點是都在文中放進真實自我的切片,讓我想問:出書之後,「作家」的身份帶來什麼人際上的改變?馬欣說她的人和文章是兩回事,所以出了書朋友還是原樣,但到了打書和演講場合,就會有另外一些人出現,跟她分享也是卡繆《異鄉人》的心情。「像兩隻腳踏在不一樣的世界,但我無法把另一個世界拉到日常生活裡,因為那是必須下課的時間。」她說一開始的確需要適應,尤其任意門一穿梭,到了某個地方突然被叫「老師」,會覺得一驚,心想那我能給你們什麼?「一方面覺得恐慌,一方面又有個責任感,必須迴轉門過去就扮演好那角色。」
九雲則說:最可怕的是不敢見爸媽,躲得遠遠的。「尤其上一本(小說)是真的放了很多真實經驗,靠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但如果不記下來,搞不好二十年後就忘了。而父母一定也知道哪些是真是假,「但因為加了我的觀點,會比較害羞,他們可能從來不知道原來我這樣想,譬如原來九雲對哥哥的感情真的很深,(他們)會很想讓哥哥知道,我就覺得『不用吧⋯⋯』。」
她還寫了很多外婆的事,但外婆已經走了,「可以想像我媽媽看的時候一定在哭。」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她也清楚知道只有第一本會這樣,把從小面對、沒辦法處理的很多情感一口氣寫出來,之後就不會了。我接著問那朋友的反應呢?她的回答「我的朋友大部分不看書⋯⋯」讓馬欣大喊:「好悲傷喔!你不是藝文界的嗎?!」
但九雲說,出了書才發現真的是如此。看書的朋友不一定看戲,會來看劇的不見得愛看書。「所以我出書很開心,因為遇到很多喜歡看書的人,真的可以交流、溝通!」她說平常自己很孤單,「寫的東西沒人可以談,現在終於找到一些雖然不熟,但可以聊創作聊生活的人。」她還提到在寫作上,其實很需要一個討論的對象,「我需要一個讀者,他必須是我身邊的人,要能在我寫的第一時間、或到一個關卡的時候跟我聊一下,有點像編輯但更了解我,是一個伴的感覺。」她提到瑞蒙卡佛說他每次寫完,就會請老婆先看看,覺得非常嚮往。「我覺得那實在太酷了!但真的非常需要緣分。」這讓現場的攝影師 Pan 也忍不住開口,說她拍照一樣需要一個伴幫忙看,不然會失去方向。「而且這個人必須是了解我的。」
冷靜的男性筆觸
然而,被問到這題的馬欣,想了想之後說:「可能從前在新聞業受到的訓練,就是自己的文章自己負責,只有當總編把稿子丟到你頭上,叫你去買檳榔的時候,你才知道代誌大條了。」她說二十年前,那個新聞業還很蓬勃的時代,就是一排卡夫卡的辦公室那樣所有人都在打字,「如果誰隨便可以問主管『我這篇寫得好不好?』下個月就被革職了吧!」
她進一步舉例,後來到男性雜誌去,原本女性筆觸的她被要求改男性寫法,「一開始沒聽懂,怎麼學都學不像,就隱隱感覺自己黑掉,後來副總編約我去茶水間,印給我一大疊《紐約客》還有海夫納的訪問,說你這個月把這看完,如果還寫不出來就走人。」她回想當初對方的口氣其實是很冷靜和婉的,但是對「從小作文就很好」的馬欣來說,這打擊比被總編丟檳榔還嚴重。「因為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只知道原來寫法還有分性別!」她至今記得那個茶水間有一扇大落地窗,她就看著外面的世貿中心一直掉淚。後來全部看完就真的寫出來了。
大家當然超好奇追問:所謂男性筆觸到底是什麼?馬欣解釋:女生寫東西一定是有情有款,有些情境和畫面,但男性的筆觸雖然也有畫面,卻不帶那麼多情,「比如川端康成寫《雪國》,沒有說這女孩多衰多可憐,或像《伊豆的舞孃》,你要看到第五頁才知道女主角的處境有多慘。」對那些殘酷面的事,是用非常平靜、日常的寫法,不足為奇的感覺,也不下判斷。「比如海夫納酒池肉林,它就寫得沒有任何批判,比較像手術刀,切入點是非常冷靜的。而女生就會用包覆性的寫法。」
「要在黑暗中有光,那才是現實」
這時候九雲舉宮本輝為例,說他也是如此,問馬欣喜不喜歡他的作品?沒想到神奇的事發生了──馬欣竟然從隨身的包包拿出宮本輝的《月光之東》(還配上音效「登登!」)讓九雲邊驚叫邊說:「我昨天剛看完!」兩人聊起宮本輝,九雲眉飛色舞:「他的《春之夢》把貧窮寫到入骨,因為他自己的命真的很苦,所以反而輕描淡寫就過去了,不必灑狗血。」馬欣附和說川端康成也很苦,還有蕭紅也是,讓九雲非常贊同:「像《呼蘭河傳》,在那麼慘的狀態下,竟然還能帶著幽默!」那種生活的殘敗面,一寫下來都是荒涼,可雖然心裡面荒涼,面對文字的時候還是抱著期待。「像宮本輝完全在講很黑暗的東西,但他可以在黑暗中給你光,那才是現實。」
九雲說她覺得,寫作者必須負一點社會責任,不可以真的寫得很黑,「你如果寫完一本書讓讀者看完很想去死,那是不道德的,是危險的。」她笑著說自己小時候一直覺得,《蒙馬特遺書》應該要是禁書!
然而那些孤獨和黑暗,卻是馬欣安全感的來源。幼時家裡經歷了異變,後來在書店翻到村上春樹的馬欣,終於有得救的感覺。「他的文字是根本性的孤獨,讓我發現原來世界上有人跟我一樣,他的呼吸是我可以感受的,他的海豚旅館是我們這一代的鄉愁。」她在十幾歲開始讀蕭紅,讀張愛玲,才能理解「目送家裡的長輩漸漸凋零」該怎麼自處。「後來臺灣文壇的很多小說,對我來說反而太溫暖,溫暖到對幼小的心靈是殘忍的,我明明就在另一個時空,不想被硬生生拉到這個世界,一定要進到海豚旅館,或進到蕭紅的生死場,才可以呼吸。」
至於《蒙馬特遺書》,馬欣說那的確影響了一代人,甚至拯救了一些人,終於有人為他們說出一些什麼。「當然隱隱會覺得,這作者危險了,就像看三毛的小說會慢慢覺得危險,她就是懸於那一線間,那一線如果斷了,就什麼都斷了。」
對「美」的追求需要自律
順著性別的話題,我也好奇問兩人各自的讀者群,性別的分佈如何?馬欣說開始演講之後,才發現一半一半,九雲也說上一本都女生,但這次發現男生也跑出來,不再害羞了。兩人都說結構正在改變,而九雲又補充:「男生是抱著某種期盼,想找到一些答案而來的,比較是解決問題型,提問也都單刀直入。女生則是問一問就會講到自己很寂寞,變成在分享(笑)」。
我最後問九雲接下來的計劃,她正在準備把《暫時無法安放的》書中的同名短篇搬上舞台(編按:兩人的對談發生於夏天,九雲後來將收錄於《暫時無法安放的》中的幾篇小說規劃成一系列名為「溫聲細語」的讀劇會和舞台劇演出活動),她在這個故事中碰觸了極端的題材,自己其實蠻怕的,「前幾天拿到劇本,讀了一遍,更是頭皮發麻,覺得我到底寫了什麼?」雖然惶恐,言語間仍藏不住躍躍欲試。我回頭問整場對談下來,對馬欣的印象如何?她說原本想像既然是記者,而且還跑娛樂線,應該會很犀利很聰明,「實際上相處果然很聰明──我最喜歡跟聰明的人講話了!──但是沒有想到那雙眼睛裡有很多稚氣。」馬欣笑著說:「因為沒有社會化啊!都是國父思想社害的!」
那天的對談到此,早已遠遠超過預定的兩小時,三個寫字的人聊不完,話題又回到我跟馬欣去年談過的,彼此的時間管理術。九雲最健康,可以九點就關機準備就寢,還跟中醫師學會了「十五分鐘午睡技巧」;馬欣則說她訪過一個音樂界前輩,對方也曾經靈感一來,就待在錄音室都不走,後來身體出了狀況,他才意識到「美」這個東西是除非你能夠自律,不然會被迫停止追求的。「如果工作是要採礦,太過燃燒自己,最後就會失去了繼續挖掘和下載靈感的機會。」
而我在旁忍不住想:不只要逼迫自己休息,像這樣偶爾爬出地洞,讓思緒在朋友間釋放、碰撞,也是不論愛不愛孤單的人,都需要的呼吸吧。這次對談讓我見識到,寫作真的不只是「當下」,而是多少記憶、體認和對世界的感知⋯⋯通通加總,成為這個你,而你能寫的、想寫的,以及最重要「不能不寫的」,都在訴說著你是誰,以及你想成為誰。
而我們,都在彼此面前,在這暫時能夠安放寂寞的下午,更瞭解了自己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