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水傳話的異鄉人:專訪馬欣《反派的力量》(上)
在專訪馬欣的整整一週前,我在週五夜晚潛入台大誠品,參加她的新書發表會。一開場,她先說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演講,過程裡也幾度說自己很緊張,但她的內容——從童年的孤寂、世事的虛構到性別的框限,從「無時無刻在人群中藏著獨處的自己」,到資本大神開的慾望清單,再到女性身體的「廢墟化」,我坐在最末排,邊聽邊讚嘆,清楚辨識出一個熟稔於文字者,邊講邊腦袋停不下來在超鏈結、跳躍的速率。
一個禮拜後,我們相約在「自然醒」咖啡館,前一晚熬夜的馬欣,帶著她自己形容「棉絮般的感覺」出現。我趕緊坦承,說那天偷偷去參加了發表會,換來她的驚叫「幹嘛偷偷啊~」我說那演講非常精采,一如書中文字給我的感覺,是「內功深厚」。我是認真的。在讀《反派的力量》的過程裡,那文字操控的寫意,思緒的聯想和詞彙的豐富開闊,都讓一個同樣想把影評寫成散文的人,豔羨不已。
在發表會上,她也談了很多關於寫書的動機,也有好心人打成逐字稿放在網路上了。於是我直接切入私心最好奇的一題:在演講裡,她提到自己「小學三年級就立志一輩子寫作維生,而且最後成功了」,這麼浪漫的故事,究竟怎麼辦到的?
「其實,一點也不浪漫。」一開始,馬欣就把我以為很勵志的故事,變成修煉和苦行。「首先要體認到大環境的現實,是這社會並沒有給寫字的人多少錢。稿酬始終沒有上揚,你必須培養出一個不至於清貧,但很有彈性的生活,否則會害怕。」祖籍山東的馬欣,笑說自己真的實驗過囤積肉包、饅頭配乾辣椒(就差沒有二鍋頭)過一段日子,她形容這產業其實很「寒涼」,有志成為其中的環節得先想想能不能適應。「另外,我一出社會就訓練自己不拖稿,不要造成編輯的麻煩,也要針對不同單位給不同風格的文字。」過去她喜歡到書店去,把好幾本雜誌攤開成一排,研究各自的欄位、段落、編排,這樣累積了一兩年,自然對產業有初步概念。「我常碰到一些後進,被退稿覺得很疑惑,其實不是你的稿子不好,是編輯難以處理。要考量供需量和風格,齒模對了才能用。」說到底真的不浪漫,是很工業化的過程。
而不只認識環境,源自興趣的浸染、不知不覺的自我充實更是關鍵。寫出一本專談反派的書,作者必定是個影癡,馬欣將這歸功於她的童年,父母很忙沒有空理她,哥哥姊姊大她很多,又早早去了美國,「他們留下一些希區考克的片,我媽媽也會買《慾望街車》,我看了覺得有趣,就慢慢搜尋到那年代的電影。」長大後,這樣的吸納變成「看完某部冰島電影,會好奇北歐片是不是都長這樣?看了漢內克的片,會想蒐集他其他作品。」她形容自己看電影非常、非常衝動,會蹺課去世新旁邊的僑興戲院窩一整天,看四、五部片,或去信義路上的「十月 MTV」,那裡全世界的片都有,比國家電影資料館還齊全。「我們這一代很幸運,當年的 MTV 產業就跟現在的錢櫃一樣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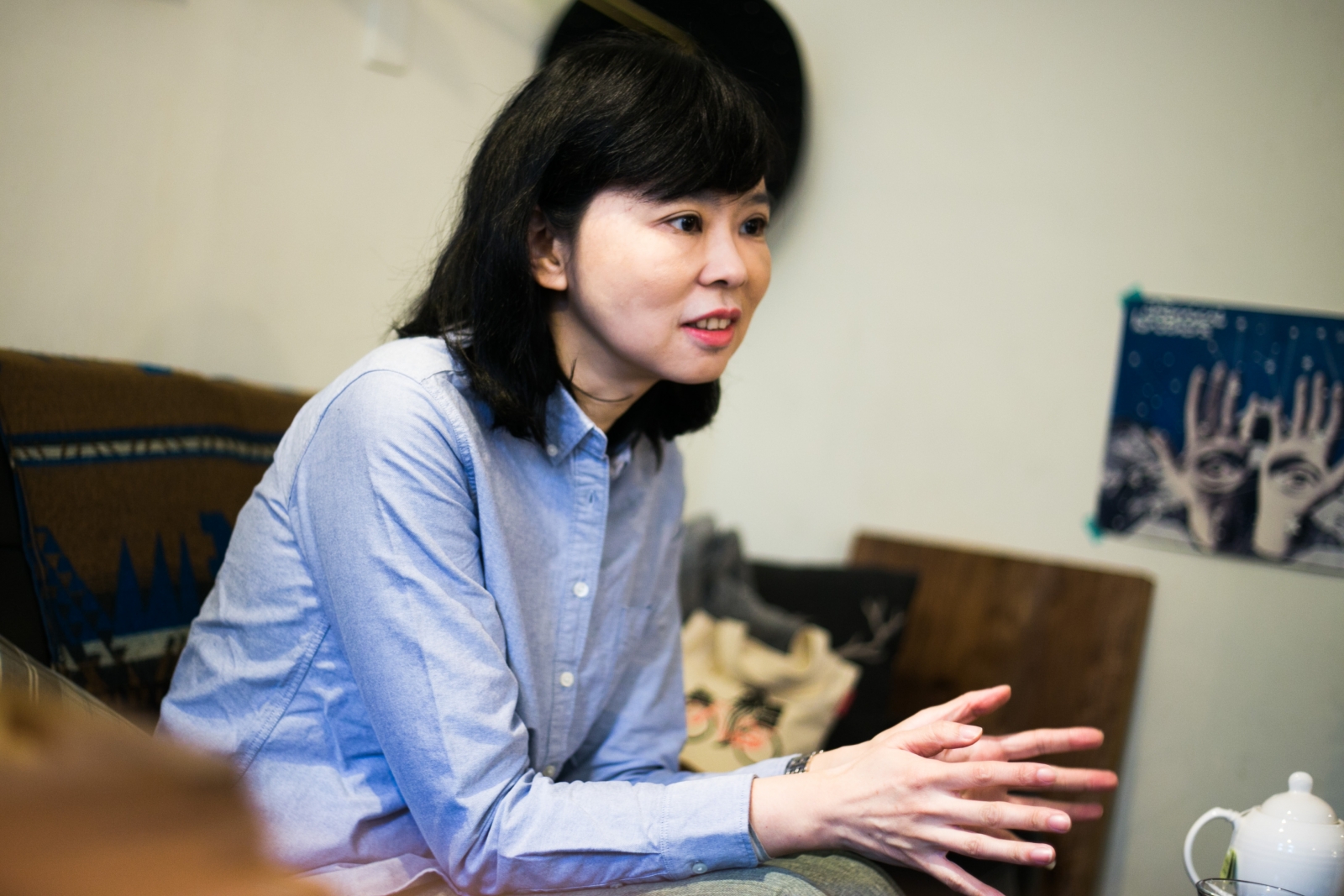
人與人的溝通斷裂造成「反派的思維」
回頭談書,馬欣不只一次提到她寫書是想作為某種「時代的提醒」,我請她多談談,她說:「我們常講這是多元社會,可是我不覺得,我覺得我們越來越單一化,多元只是表象。」她指出網路社會的民粹性,對任何議題都毫不保留地表達內在喜惡,這樣的直白溝通本是好事,但是當過大的能量一次次在留言板上炸開,會造成「看齊」的反效果。「當所有人意見一致,你就會想跟從,而網路讓這更加發酵、密室化,變成我不敢講不一樣的,一講就被公幹或被笑。」這造成兩種人,一種深怕跟別人不一樣(於是停止思考),另一種亟欲跟別人不一樣(所以為反抗而反抗),但其實兩種都是盲從,中間值則越來越小。
在無遠弗屆、無所不在的網路效應中,有勇氣和時間去獨立思考的人越來越少,很多議題吵一吵,大家又馬上忘記,「還有各種懶人包的出現,更是像《超譯尼采》一樣可怕。這讓我覺得一定要寫個《反派的力量》。」馬欣說現代人很懶,就像《鳥人》裡的評論家,幫別人貼上各種標籤,讓自己便宜行事,「明明是自己懶得改,就幫對方貼標籤說你金牛座固執,然後就天天說反正我們合不來,或說我是水瓶座所以很跳躍,你們跟不上我就是你們不夠跳躍等等⋯⋯」她從小就觀察發現,人們傾向用自己的邏輯去解讀別人,這些方便行事也造成人際間溝通和理解的斷裂,最後變成一些小小的惡意在孳生。她稱這叫「反派的思維」:
「他們無處可去,而且一思考就被笑,邏輯跟別人不一樣就被說你很奇怪,你這樣找不到伴侶,你不適合這工作,然後被剔除。」她說其實反派會誕生,是因為正派的世界有很強的排他性,「我們已經建立好一個樹狀體系,你別再弄些小枝小節不然會被修剪掉!」但那些被剪掉的到底是什麼?是可以掉落土壤另外生長的嗎?還是變成惡意的溫床?她寫這本書,正是為了照出光明背後的偽善。
我進一步問,所以寫這本書是要幫壞人平反囉?她卻回答:「其實沒有誰是真正的好人或壞人,我們每個人都不太好也不太壞,只能說多數都在尋找一個安全路線。重點是,我們這些平庸者憑什麼去 judge(評斷)別人?為什麼不試著體會人家的心情?」她指出其實多數大眾只是在模仿好人,卻很容易變成道德警察,或陷入米蘭昆德拉說的「道德亢奮」狀態(而非真的行善)。更多人模仿好人,則是因為這樣比較安全,只是這一來又掉入了(早被講爛的)漢娜.鄂蘭的「平庸之惡」的危險。

帶領異鄉人走出自己的路
但我不死心,繼續追問有沒有哪個正派是真的經過思考,而非只是扁平、熱血的英雄?馬欣想了想,舉卜洛克筆下的馬修.史卡德為例:「他其實是個軟弱又酗酒的懶鬼,卻被使命感驅策去聽、去感受紐約這座索多瑪城裡的小人物發生什麼事。所以他敢『行過死蔭的幽谷』,面對那些鬼魂,明知不可而為之,這是很偉大的情操。」她也提到《教會》裡被流放的神父,當他去到那個部落,坐在樹下吹一曲單簧管給自己,那打從心底發出的樂音,是萬物都能感知的善意。
她還提到《駭客任務》的尼歐。尼歐原本可以繼續當他的工程師,卻選擇吞下紅藥丸,而直到最後都沒有人告訴他這是對還是錯,也沒有得到任何獎勵。「那心態有點像卡謬的《異鄉人》,就是你發現自己是異鄉人,也知道後面一定還有別的異鄉人,你要怎麼帶領他們走出自己的路?異鄉人不可能真的有故鄉,但他們必須要有人在前面帶他們走。」
說到異鄉人,在那天發表會上,馬欣說過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她說「身為五年級,我對你們這一代(八、九年級)其實有虧負感。」我忍不住追問這點,她解釋道:從二十多年前進入唱片界,就可以感覺全台灣處於一種錢淹腳目的狀態,那些熱錢造成大家失去理智地往同一方向走,「但那時就會隱隱約約覺得,這棵樹可能什麼時候會被搖掉吧?只是不知道會在哪一代。」但畢竟無力可回天。「你不可能告訴業者說,不要看到新人立刻出片,或不要一直塑造同類型的音樂。像現在韓國不斷出現相似的團體,你不可能叫他們停下來想想,那群男孩在他們的青春歲月裡,可能被搖掉的是什麼?」
她接著說出一段讓我感動萬分的話:「我自己的個性剛好相反,從小就害怕去人多的地方,所以從沒走進熱錢的隊伍裡,以社會價值來說是很弱的人,競爭力也不強。但我又是看《異鄉人》長大的。我的虧負感在於,我們那一代有這樣的書,還有《猜火車》那樣的電影告訴我們當一個異鄉人是合理的。但我們似乎已經忘記要把這些傳給下一代了。我很想告訴他們,活在你的很原始的心裡面,不是個不正常的狀態。在這一代面臨教改的情況下,可能沒有人有空好好講個故事讓他們知道,其實這世界有很多異鄉人,他們都是這樣子長大的。身為一個五年級的異鄉人,我該怎麼隔水傳話下去,把這些傳送給他們?」

女性心靈的自由與超脫
我們還聊到女性在社會上受的種種限制,包括一生下來就有各種「訂單」(被指定的各式角色框架、特質)可以選/必須選,卻又處處是刻板。她也在書裡列出幾位女性的反派:《告白》的森口老師,《渴望》的加奈子,《控制》的愛咪,都是透過把某一類訂單執行到極致,反過來撼動父權社會。我問,影史上有哪些女性角色,是非反派的身份卻仍有這樣的影響力?她第一個就提起偉大的梅姨:
「在《穿著 Prada 的惡魔》裡,她是人人懼怕的總編輯,握有一切權勢,任何時裝秀都可以被她打槍,但梅莉史翠普一直企圖還給這角色一些骨肉,演出她的不自由,和逃離這身份的路徑。」此外《麥迪遜之橋》、《遠離非洲》、《八月心風暴》都是,還有《親情無價》裡的媽媽,死前一直要告訴女兒怎樣努力活下去⋯⋯「雖然活在一個主婦的軀殼裡,但一直在強調精神上的自由:你可以禁錮我的身體,身份,際遇,但不能禁錮我的心靈。」
她也提到凱特布蘭琪,和她的《伊莉莎白》:「那是多麼殘忍的事,我必須去掉所有個人特徵才能成為女王,無性別的,要拆掉所有人投擲的標籤才能執政,但她演起來非常自然,沒有悲情或哀嘆。」還有《藍色茉莉》,為了進入一個自以為富有、美麗的狀態,反而被自己的美貌困住了。「要扮演自己的美是最痛苦的,因為那不是妳能掌握的。有太多女生都是如此,要怎麼在美麗中活出別的價值?那是更大的掙扎過程。」她指出,這兩個演員經手的角色都會告訴你她不只是表面的形象,還有超乎常人的堅持。「每個女人都需要對自己心靈自由的承擔性。不能在十幾歲的時候發現自己是美女,就覺得僥倖,或發現自己很醜就活成一個悲劇,那是活在別人的劇本裡了。」

我接著問馬欣,她在書裡三番兩次寫到水手服、夏日單車、馬尾、芭蕾舞衣,甚至是蒼井優等等意象,這是在說《花與愛麗絲》嗎?沒想到她回答,這部片雖然也算,但那其實早就是復刻了。真正的源頭是《四海兄弟》裡的珍妮佛康納莉:
「那時候我還小,被那一幕嚇到,天哪怎麼會有那麼出塵的事物?才發現原來那形象會停留在不論男生女生的記憶中,變成你永遠記得那氣味,那舞步踏起來的感覺。」那之後包括蒼井優,或曾以一套芭蕾舞寫真震驚日本的中山美穗,都在復刻這形象。「《四海兄弟》裡,他們的成長那麼苦,只有黑道一條路,那樣的生活裡不會有藝術、畫廊,也沒有人帶他們去聽音樂會。那種精神上的貧瘠,讓他們在看到那一幕時,得到某種超越性別的『美』的震撼,那是超越人生一切困難的救贖。」
她進一步說,其實岩井俊二也有這意圖,當蒼井優跳起舞步,那不只是女性的美,更是一種「人」的精神性純淨,甚至是逃遁。「所以那樣的意象:水手服、肥皂香、馬尾、一輛單車『叮~』地過去,我相信你們男生在那瞬間想到的不是性慾,而是種莫名的救贖感。『原來天地間有這樣的東西呀!』就像小王子看到麥浪,覺得世上原來有這樣的東西可以救贖我。」
聽到這段話,我有種被徹底看穿的感覺,幾乎就要臉紅了。想起當初第一次看《花與愛麗絲》,那分不清是被治癒還是被掏空的感覺,原來有些形象可以穿越一切時代文化,打中每個人內在的缺口。

《反派的力量:影史經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開的自己》
作者: 馬欣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15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