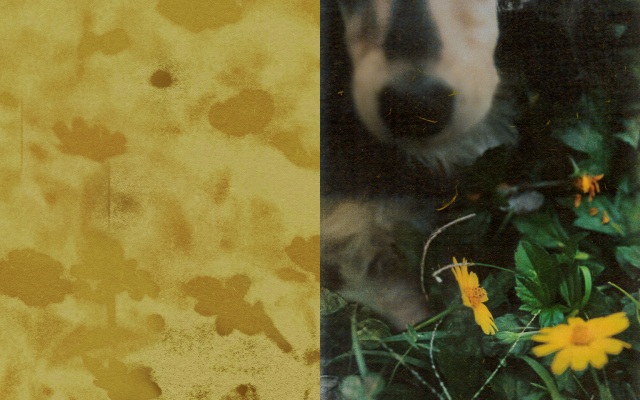「媽的,丟不掉了。」專訪倪祥
倪祥說是老家。真踏進來,卻怎麼看都是廢墟。
老家是高中之前全家人住的舊公寓,位在嘉義市區的中心地帶,標準的三房兩廳加前後陽台。後來搬走,有段時間換成大伯住,如今已是空屋很多年了。
但空屋其實一點也不空。一進門灰塵與霉味撲面,任何有檯面的地方全都被雜物佔滿,層層疊疊,面目模糊,只剩輪廓依稀可辨:這裡是餐桌、那裡是沙發,還有大概是客廳和餐廳的地方。只是在廢物滿溢的空間裡,這樣的區分也沒什麼意義。


整間屋裡的東西泰半都是爸爸沒丟掉的和撿回來的。後來大伯入住,兄弟倆同病相連,接手囤積。想在房子裡找個像樣的地方坐下來訪問,環顧四周,勉強在沙發上挪出一個位置,倪祥卻毫不在乎地一屁股坐進椅子,沒有髒,沒有亂,彷彿那是一幅最尋常的家庭風景,
他只是用最平常的語氣說,「這都算很好走了。」
垃圾的時態
2024 年,倪祥在北美館的展覽《大家都來看你了》,展場幾乎像是囤積症的移地搬演,垃圾般的雜物四處散落:印著紀念品字樣的保溫杯、成套的老氣陶瓷杯盤;有些被他動手改造:紅色的小豬撲滿被肢解掛起,成了市場肉舖上的豬肉,新郎新娘玩偶脫下婚服穿上古服,擺成兩尊金童玉女。
還有更多無以名狀,介於堪用與無用之間的閒置物品,都是倪祥請爸爸隨便挑選家裡的東西,打包寄來佈展。「當初有一半真的是抱著幫家裡清垃圾的心情。」最終爸爸寄了 10 箱,換算體積噸,大約是三噸半。
展覽以囤積為題,但生長在那樣的家裡,很難意識到什麼是不正常。他甚至沒覺得有什麼不方便。「小時候只有一個印象:媽媽把東西丟下樓梯,然後我爸在那邊閃那些砸下來的東西。」
沒有像媽媽那樣爆發,也沒有像哥哥一上高中就離開家裡,搬到台北。他反而就這樣尚稱舒服地活下來了。
.jpg)

而囤積症是沒有起點的,也沒有潛伏期發作日和確診日期,真正意識到的時候,只是在某一個瞬間,「當你發現走路開始沒有那麼好走的時候——怎麼了?為什麼那麼多東西?」
囤積症的人病根不只是囤,更是撿。爸爸曾經是鐵路局電務段的員工,對電器最是在行,只要看到路邊被丟掉的電器,總要撿回家測一測。能修的就繼續用,不能修的也留著,反正總有機會用。然後從電器,到各種棄之可惜的東西,家裡成了廢棄物的收容所,不管有沒有用,先撿回家再說。
況且對爸爸而言,答案永遠都是有用。爸爸最經典的作品,是把撿回來的椅子拼拼湊湊,包裹上不要的抱枕和衣服,變成一張只符合他人體工學的躺椅。遠遠看,簡直是個藝術品。「這樣的躺椅已經出現至少四五張。只要他在這個地方待久一點,這種椅子就會出現。」
2016 年,全家人因為爸爸罹癌而搬到林口,北部房子小,甚至不到老家的一半大。囤積一下子被壓縮,「那已經是誇張到很難走路了。」
不是沒有嘗試丟過。有幾次爸爸出門,倪祥和哥哥趕快整理了十幾袋垃圾丟掉,有時候被爸爸發現,就要拚命。另一次發脾氣,是爸爸撿了一尊如來佛像回家,「我唸他不要撿類似佛像的東西,上面一定有什麼鬼東西才會被丟掉。」
後來那尊撿回來的如來,被他動手改造成一隻鋼彈。一來是陪病期間有時手癢,做點東西權充發洩。二來,或許也是想對抗些什麼。
「如果你撿的東西,我在你面前摔爛,好像這樣就結束了——那如果把它弄成另外一個樣子放你面前,那會是更大的對抗嗎?」
這尊如來鋼彈後來出現在 2022 年的個展《間奏請稍候》,「本來是沒有想要展,但就是很想要⋯⋯是嘲諷他嗎?還是怎麼樣,我也不知道那種感情。」
出乎意料,爸爸也沒有生氣,甚至覺得撿回來的東西,是真的有用。「他其實是可以接受這種改造的。他只是很討厭浪費,他覺得大家都在浪費,那他就要撿回來。」
挑釁無用。曾經在吵架時說著「媽的要不是學藝術,誰有辦法跟你相處」,如今卻在垃圾裡找到對話的起點。
「反而是那個時候這樣改造,才好像跟爸爸莫名其妙地有了交集。」
.jpg)

得獎了——不公平
動手改造創作,是很後來才被啟蒙的事。最一開始,倪祥只是喜歡畫畫,小時候被媽媽帶去參加畫畫比賽、寫生比賽,拿了好多張小獎狀。有些至今仍掛在老家的牆上,剩下的被爸爸拿去貼在鄉下舊厝的牆,不為張揚,只為了補牆上的破洞。
是因為這樣,才讓他從不在意那些獎狀獎盃嗎?
大學考上高師大美術系,入學沒多久,就發現教育現場的權威和標準未必可信。「那時候高師大系展,入選的東西都是重複性、機械性,還有連作型的東西,那都很好歸納。」
他看穿系展的標準,不外乎做工細、有耐心、重複性,100 號的油畫連 4 張,好像就能保送入選。「那你當然會質疑啊,因為這個太好抓了——那我抄佛經也可以嗎?當然不是說抄佛經不對、或是抄佛經不可以是藝術形式,而是好像只要掌握這些機械性的東西,你根本不用放任何想法也可以得獎,那你當然會覺得這個有問題啊。」
是在那時候想起了爸爸。用廢物東拼西湊做出來的,也能算是作品嗎?或者,那也能算是創作嗎?「我不覺得他一定有創作的意思。他都是出於功能性的,或是便利性、習慣性的使用,但是在我自己看來,就覺得很帥。」
於是念頭一轉,他拿起攝影機,回到家拍爸爸。大二那年,他拍攝錄像作品《倪國倫的小兒子倪祥拍攝》,鏡頭裡是他跟拍爸爸到公園,把各種手作或現成的小物散落在公園角落,再加上爸爸煞有其事的作品自述。他說,這不就是大地藝術季嗎?
《倪國倫的小兒子倪祥拍攝》錄像作品(2003)
「聽我爸在那邊講,就覺得很有趣。只是我不知道,它原來對我的後座力這麼深遠:其實他就只是要娛樂自己,他的第一個觀眾就是自己,他要爽才成立——這樣的方式我很喜歡,這不就是創作的核心嗎?不要管其他人啊,也不要管媒體、也不要管會不會成功,很開心很投入,就對啦。」
後來那卷錄像,他沒有再拿回系上,只是自己收著。「我覺得他們不懂。那時候我也不懂,我只是很喜歡。」
內心開始隱約感覺到什麼是創作方法,然後轉過身回到系上,做的還是那些技藝的競逐。當時他想的是,照著這個規矩走到畢業,就好了。
結果大四那年,倪祥拿到了系展設計類的首獎。
那是一幅四連作的作品,最初想做的其實只有一個畫面,是關於 911 和雙子星大樓。「也是很假左派的東西啦!」但為了系展的潛規則,還是一口氣做了 4 張。先用鉛筆繪圖,然後照相,再丟進以拉(Illustrator)裡描圖。當時以拉技術還不算太熟,拉近一看,作品甚至還有破圖。
但終究是得獎了。「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時候拿到油畫首獎的朋友,他畫了四百號的油畫。他那時候就說——『你這嘛首獎,我畫到欲死,你這個用以拉拉一拉,你就結束矣。』他們覺得畫油畫畫那麼久,不公平!」
2009 年,倪祥又以《很快就補償》拿下臺北美術獎首獎。
錄像作品裡,他扛著攝影機和透明壓克力板,在各種面臨拆除的建物前,當怪手敲下一角,就用麥克筆在壓克力板上補上被毀壞的邊角。「大概為期一兩個禮拜,就是到處拍,真的很爽。而且你很確定這個對象就是你要的,當它在那邊發生,你就很像在跟它玩。」
那大概是大部份藝術家都渴望的狀態:只做自己想做的東西,卻又能得到體制的認可,好像就能和獎項和解。
以及,真正開始看重獎項的重量。「得獎當然很開心啊,一定很開心,你說不開心一定是騙人的。而且可能現在年紀有了,你會覺得如果沒有辦法換錢,這個才華是不是不太行啊?這才華很虛啊!」


那年臺北獎的報紙剪報至今還貼在老家牆上。「那時候拿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賄賂家人——我說一半給你們,以後不要管我在幹嘛。想起來怎麼那麼笨呢?那時候臺北獎錢超少,但是我是很慷慨,我直接給他 10 萬。」
用 10 萬塊把獎項的光環典當出去,換到了自由。2012 年,他來到高雄紅毛港旁的大林蒲,垃圾一樣的地方。
垃圾之地
被石化重工業包圍的大林蒲,各種污染長年籠罩,八〇年代拍板定案南星土地開發計劃,以各種廢棄物填海造陸,但沒有救回邊緣垂死的漁村。在污染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大林蒲被迫啟動遷村計劃,根據 2011 年高雄市政府的民調,高達七成以上的居民願意遷村,但還是有一成五的人,不願意就這樣放棄離去。
倪祥是在那個時候來到大林蒲的。
「雖然大林蒲名氣可能很小,但它未來可能是全台灣史上最大遷村案——可是真的要有人駐點在那邊嗎?沒有啊,頂多來一下又回去、來一下又回去。公視也來很多次啊,很多紀錄片導演都去過啊,但是誰受得了?誰能夠真的生活?」
那幾年倪祥稱之為「自主駐村」的日子是這樣過的:出入只能開車,一回鐵皮屋住處的第一件事,是開冷氣。
「為什麼?因為你經過中林路,先是鐵鏽硫磺、石灰味,整路都是化學的味道,不開車你根本受不了,騎摩托車會瘋掉。之前還沒裝冷氣的時候,每一兩個禮拜會有一天,瓦斯混合石灰味,會把你臭醒。」「你家的陽台大概一兩個禮拜,就會有一層亮晶晶的。是鐵鏽、爐渣粉或是石灰?不知道。」
那種地方,他斷斷續續住了 4 年。「那這樣,是不是垃圾的狀態?」
但還是留下來了。因為,「你也會想要看看自己到底能做什麼。」
剛進到大林蒲,看到什麼都是奇觀。廢輪胎疊成海岸,海水被重金屬污染成一整片超現實的藍,爐渣填起的土地龜裂,「對居民來講是每天都在看,他們已經不會想要拍了,但你剛剛才進去,很自然就會有辦法把它們串在一起。」
於是他舉辦「2012 大林蒲國際公害攝影大賞」,又仿照《蓬萊仙山》的風格拍 MV,讓比基尼辣妹在污染的海岸奇景上擺弄姿態。後來幾個朋友在這裡辦小港開唱、辦西南瘋音樂祭,倪祥也組了個「小嫩豬」樂團上台玩。
把痛苦玩得粗暴一點、鮮活一點,就能過得去嗎?
2013 年,倪祥和當地漁民在即將被拆除的魚塭舉辦「老闆不爽,免費吃魚」活動,在魚塭上架起高高的投影幕,上頭在傳授法律知識,底下的人在魚塭釣魚兼喝魚湯。結果活動舉行到第三天,開來十幾輛警車和怪手,當著他們的面把工寮壓爛。
「那時候是我自己衝擊比較大,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對方會來真的啊!我們本來還有在玩 camera,說什麼 321 警察怎樣怎樣——玩到最後自己都心態崩壞了。幹,來真的喔?啥潲啦!那個衝擊很大啊!我是講不出話的。後來幫我們攝影記錄的邱子晏,他就說他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人會自殺——你看到你家被推掉,你會受不了的。」
但一開始,他也沒有抱著「一定要達到什麼效益」的心情,只要在那裡玩得開心,就有辦法繼續做下去。
只是後來,好像也沒那麼開心了。「一方面也是,你好像找不到自己。你還是想做作品,但是你不知道要在這裡做什麼,你會很像在做美工,很像在滿足大家的期待——比如說做個環保抗議的道具,我會希望把這個東西做成我喜歡的樣子,但這個道具在新聞裡可能只出現不到一秒,久了你就會覺得,在裡面失去了自己。」
甚至連那些最初的奇觀都逐漸死去。2013 年廢輪胎海岸發生火災,悶燒了 12 小時,毒氣沖天,整片海岸從此封鎖。那片被化工染色的海,也不再有那麼驚心動魄的藍了。
再後來,爸爸生病,倪祥離開大林蒲,跟著全家人一起搬到林口。


對活屍開槍
起初搬到林口,是想就近治療爸爸的癌症,再加上外婆年紀實在太大,需要找間有電梯的房子,於是順理成章地搬到林口長庚十分鐘車程的電梯大樓。
沒想到,爸爸的求生意志極強,再怎麼不舒服都會強迫自己運動,「不用管他死活,他自己會活得很好。」真正需要照顧的,反倒是精神疾病爆發的媽媽。
還住嘉義的時候,媽媽的強迫症就有跡可循,「比如說她會拖著一個行李箱,裡面都是她的藥,然後她會打開來數,如果有人干擾她,會跟你翻臉。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這其實已經是很嚴重的強迫症了。」
反覆發作吵鬧,到各家診所拿藥騙藥,吃了瀉藥又吃止瀉藥,最後只能送急診,如此循環。最終爆發是在 2019 年,當時倪祥人在澳門駐村,接到媽媽的電話說爸爸不要她了、還把她的錢都拿走。最後媽媽報警,住院。倪祥悠悠地等到駐村期滿才回到台灣,因為失控早就是可以預見的事。
在精神科住院的 40 天,每日八點送早餐、吃藥,在交誼廳搶電視遙控器,然後做操,接著下一餐。所有線都不能帶進去,連同手機也不能用,每日只能跟媽媽鬼打牆般地聊天,還能用筆,有時寫點東西。後來那些監獄日記都被貼在展場裡,作為某種倖存的見證。
我起碼知道我體內有一顆神經病定時炸彈,加上父親那邊罹癌的高機率,我的物防和魔防會在某刻歸零,更可怕或說更解脫的,到時候沒有小孩照顧我。
好想知道炸彈現在倒數到哪了。
——〈遲早與自己對撞〉
但炸彈終究還沒爆炸,他還是得撐起照護者的責任。
媽媽出院了,但那 40 天的住院,在倪祥眼裡是,「沒有屁用——她一開始的確有一些重複性、強迫性的症狀沒了,但是大概兩個月之後,又全部都捲土重來。」
「我也不是在揬膦(tu̍h-lān,常寫作「賭爛」)健保,但是那些精神科藥物,其實我在家人身上看不到療效。因為吃了之後她沒有自己的意志,變得更笨、認知能力變得非常地差。它唯一的效能就是好睡。」
到最後,那些藥也不吃了。「寧可她在那邊練肖話什麼的,我們都覺得這都好一點。」
取而代之新的平衡狀態,是倪祥會對媽媽設下各種規矩:比如吃飯的時候不能吵藥,否則就沒收手機;比如一天要走完 15 分鐘的路,就獎勵 LINE 貼圖。「那時候我也很走火入魔,就寫在紙上,貼起來:就是這樣子,給我做到。」

《大家都來看你了》的展場裡有一間巨大的藥袋,是倪祥為自己的陪病開的各種症狀診斷,其中一欄寫「【外觀】讓我想到那些對家人(已經變成活屍)開槍的人。」藥袋的標題上大大的「你也沒有比較正常」,那是所有被長照困住的人的共同素描。
面對活屍,大多時候只能殘忍。「其實陪病的人本來就不可能是電視上演的那麼溫柔,你一定是很火大啊,但是你還是得壓住那個怒火。比如我爸在帶我媽走路,我媽說不想走的話他就算了,但我沒辦法接受這件事情。我覺得我的心態其實不健康,很殘暴,但你總要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
展場裡的其中一區,倪祥架設了體驗裝置,試圖還原媽媽口中的「覺得冷」「覺得熱」「覺得腳很重」。「你要說那是同理也對,我真的沒辦法知道這樣是冷還是熱。但當你覺得自己沒耐心、殘忍,可是你其實也是在他身邊啊。」
那是孝順嗎?好像更像是責任。
在長照面前,孝順兩個字往往不堪一擊,現在倪祥追求的不是當孝子,而是讓日常能夠如常運轉。「心態開了之後,好像就可以更幽默一點、可以找到更多拿捏她的方式,在不吵架的狀況下,讓她走完這 15 分鐘。」
死亡與日常
以為日子逐漸走向平衡的時候,外婆走了。
外婆還在時,倪祥會去市場買豬肋骨熬湯,加上打成泥的紅蘿蔔、馬鈴薯和番茄,分裝成一袋一袋冰進冷凍庫裡。「我自己覺得生活好像已經有個平衡,但其實也沒有維持太久,外婆就走了。」他至今還不願意記得她是哪一年離開的。
「是做完展覽之後,才有一種欸我婆婆真的走了的感覺。就很奇怪。明明已經過了兩年。那時候沒有意識到她真的走掉,直到展覽完成,有時候開車去美術館,會不自覺地在掉——欸,為什麼會這麼難過?然後你才知道,她真的走了。」
直到現在,失重感依然不時發作,他已經習慣病是日常,但死亡還不是。

日常是家裡被囤積佔滿的客廳,死亡像是電視上模糊的背景聲,又近又遠。從《大家都來看你了》的展場入口遠望,遠處電視一般投影在一片果菜紙箱上的,也是死亡。
錄像作品《有空》裡,死亡是臉上抹著白粉的人,鬼魂一樣在湖上駕駛著墳墓出航,那畫面超現實地像林正英又像洛伊安德森。
那是十幾年前,倪祥騎著機車到雲林找朋友,行經省道,路邊是一片因為地層下陷而泡在水裡的墳墓,當下「人在水中開墳墓」的畫面就直接灌進腦海中。後來正好雲嘉嘉營視覺藝術連線的策展人找上他,於是請好友吳彥宏製作了一艘墳墓快艇,帶著攝影機到雲林萡子寮漁港的沉水地景拍攝。
畫面詭異,但倪祥想拍的,其實是日常。「就很像一個人騎著摩托車出去回來,他就開著墳墓遊艇,一開始在耍帥,後來越來越狼狽。他好像要回家,但也沒有回家,沒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邊,這樣的結尾我覺得最好。」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展裡,它其實反而離死亡最遠,只是意象上很接近而已。他就是某個人的一天啊,好像也沒幹什麼、去了幾個地方,就這樣而已。真的沒有要講什麼。」
或者說,死亡不過就是這樣,駕著墳墓出巡一趟的日常。

[後記]紀念意義
倪祥說,老家年底應該就要全部清一清了。畢竟是閒置十幾年的老房子,不如整理後租出去來得實際。
哥哥已經想好要請專門清運的人來整理,但這個家畢竟算是大魔王等級,費用想必不便宜。「我自己的想法是,我會把有紀念價值的東西裝箱打包。」像是哪些?「照片啊、獎狀啊、字畫啊、紀念品啊⋯⋯。」
但難道,囤積症的起點不正是出在「紀念價值」這四個字嗎?他笑了,自己也覺得懊惱,「對!很恐怖,只要這個是誰誰誰送你的——媽的,丟不掉了。」
囤積症原來會傳染,這是有情念舊之人逃不了的詛咒。拍照途中,他提前開啟斷捨離之眼:這隻基多拉一定是絕版了,我就不會丟。這個鏡子我也會留下來。還有桌上這個裝東西的——上面的垃圾會丟掉啦,但我可能會留下面這個。棄之可惜嘛。
你完了,我覺得你什麼都丟不掉了。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