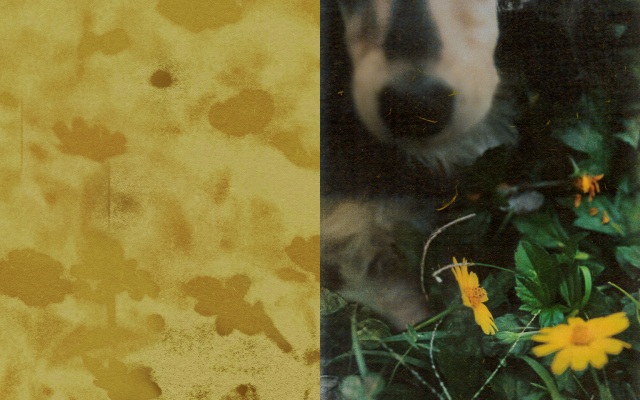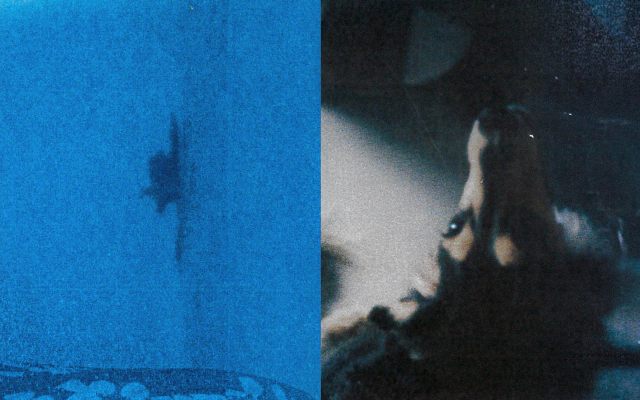東雨・有一種性別認同叫迷彩 EP1|營區浴室,露屌 or 不露屌,that is a question
「他媽的!廁所刷乾淨,再讓我聞到尿騷味,你們就等著漱林北懶叫(欶恁爸膦鳥)!」
盛班是你在軍教片裡看過的那種班長,粗俗、莽漢一條,吼起來像悍馬車的引擎。當他喊出立正口令,新兵會像被電到似的,馬上指節貼齊褲縫、屁股夾緊、大氣不敢喘一下。而他的口頭禪,三不五時就來一句「他媽的!」、一言不合就「吸我老二!」,整天把髒話和性器官掛在嘴邊,好像不加點語助詞就沒辦法好好講話似的。他就是這樣的班長。
偏偏是這樣的粗人,卻有著潔癖。衣服每天要洗、沒洗澡絕不躺上床、馬桶不能看到一點屎垢、廁所要用洗髮精或沐浴乳刷到香香的才合格。沒有達到他的標準,打掃時間就是延長再延長。
其實他是 gay。看不出來吧,我也看不出來。當他說出口時,我按住內心不小的驚訝。當然,我並沒有問他是零還是一,我覺得這跟問對方平常跟女友做愛是什麼體位一樣沒禮貌。
那是我們去南部彈庫出任務的事。射擊完的彈殼與剩餘彈藥,要陳列出來清點,核對當初領出來的數量,確認無誤才能繳回。夏天,南部比北部更熱,陽光更刺。擺了整個早上的彈殼,雙手都是彈鏈上的油污、黃銅鐵屑、還有火藥擊發後產生的積碳。
我和盛班投了罐裝咖啡,癱坐在中山室的沙發上,吹著電扇。或許是難得只有我們兩人在,他跟我聊起了天,問我一些情侶相處的問題、吵架該怎麼處理之類的。憑我有限的智慧與經驗,當然講不出什麼值得參考的話,只是說了些「畢竟每個人和另一半相處都不一樣嘛」這種模稜兩可的答覆。
而他也和我想的一樣,並不是指望從我這裡得到什麼建議,只是以這個話題為開頭,跟我抱怨,抒發他最近和老婆吵架的心煩而已。
從他老婆的衛生習慣低落(每次都是他在打掃),到他老婆脾氣差不好溝通(難得休假還得花力氣吵架),大大小小的抱怨。就是在這時,他把那句話在嘴裡嚼了嚼,才向我吐露:「噢。我說那個,我老婆是男的啦。」
他並沒有要我別告訴任何人。但我明白,他認為我懂他的明白,才會將櫃門開了一道縫。
✹ ✹ ✹
大學以前,我身邊並沒有認識 gay(也可能有,只是我不知道而已)。當成年了、當大學生了、脫離國高中和家庭了,原本的深櫃也才願意展露自己的性向。而我在認識的過程裡,也知道了「雷達」這個說法。
有些人是有雷達的。跟他本身的性向無關,而是僅憑看一眼、聊幾句話,便能在心裡判別「噢,這個人是同志呢」。可我從來沒這方面的雷達。性向什麼的,相處時並不在意。
也因為如此,是有過幾次尷尬。例如跟女生親近之後才發現她是蕾絲邊,原來只是把我當作男閨蜜;或是男生找我喝酒,一直到他的手摸上我的大腿,我才意識到狀況不對。
小諭是我一個大學學弟,他是 gay。他曾跟我講過一個理論:
每個人的性向不是硬幣的兩面,而是一個光譜,其實每個人都是雙性戀。例如你是直男,但你可能只是 70% 的直男,其實你隱藏著 30% 的同志傾向。
「另一部份的性向是隱藏起來的,連你自己都不知道。但可能在特定的情況下會被觸發。
例如啊,假設你和一個很好的同性朋友一起去旅行、度假。他長得很好看,不是帥或漂亮,而是男女都會認同的好看!你們度過愉快的一天,回到飯店洗好了澡,兩人只穿內褲,躺在床上喝酒聊天。這時,氣氛很好,喝到微醺,他把手放到你的身上,湊過來親了你的臉頰。你真的會抗拒嗎?他彎下腰躺在你大腿上的時候,你會直接推開嗎?還是有可能被氣氛帶走,順勢就被激發出隱性的性向呢?」
小諭啊,你在講啥潲?你完全不了解直男是一種什麼樣的生物啊!
✹ ✹ ✹
要解釋直男,尤其是臭直男,那要談到另一個故事,是我同學當兵時發生的。
那是在成功嶺新訓,一大群男生離開學校離開家,來到這個狗屁不通的迷彩世界裡。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是此生第一次被關在只有男生的環境。不管在外面有沒有女朋友,進了營區,你想偷偷用手機看黃片打手槍都沒機會。
然而他們同梯之中,有一個 gay,而且是個好色的 gay。聽說他在軍中偷偷收錢幫其他人口交。
有沒有人去尋求這項服務、有沒有因此被掰彎,我不得而知。但若是隨便找幾個臭直男問:「你願意被 gay 口交嗎?」他們的回答不外乎這幾種:
「幹!不要!」
「給我錢我也不會讓死 gay 舔我老二。」
「要是有男的想脫我褲子,我先揍他一頓!」
所以,要怎麼讓臭直男願意被 gay 口呢?長得很好看的 gay?還是打扮成偽娘就 OK?
其實小諭勉強說對了一點,雖然方向全錯,但跟氛圍是有那麼點關係。出乎意料地簡單,需要氛圍,不過是那種「國中男生相約偷看A片一起打手槍」的氛圍。
只要把問題改成「你能忍住不被 gay 射出來嗎?」就好了。
在這時,事情的本質已經不再是「與 gay 的性行為」,而是「男子氣概」了。問題已經變成:你有沒有種?你能撐多久?你他媽要是真男人,應該在 gay 的面前不會硬吧?
厲害吧。不管是被 gay 口交、舉辦「九刀盃自由格鬥賽」、或是在奧運比賽擺出二檔的姿勢,只要氛圍到了、男子氣概到了,做出什麼事都有可能。
沒錯,包含上戰場殺人也是。
軍隊像個男子氣概的螺旋漩渦,隨著一圈一圈旋轉,越來越高漲。沒有跟上、拿不出足夠氣概的傢伙(例如我),就等著被離心力甩到邊緣。
✹ ✹ ✹
要論整個軍營裡最有男子氣概的地方,集合場、軍械庫、健身房,都只能排在後面。浴室才是最男性氣味張狂的地方。
營區的浴室,一般來說是隔間式的,隔間有門,但那不是標配。有些是沒有門的、或只有浴簾、或是浴簾根本破了,又或是明明有門但他們總是不關。淋浴時,水霧和熱氣蒸騰,熱水和泡沫加上男性的汗水與髒污,把整間浴室燻成一股男以言喻的味道。
這時你會看到,例如小鴻時不時經過洗手槽的鏡子前,把霧氣抹去,停留一下,暗自欣賞自己的胸肌和二頭肌;還有脩仔阿宗杰哥他們連洗澡也要串門子,光著屁股不關門,在不同隔間走來走去,一邊搓著泡泡一邊大呼小叫;或是等不及隔間裡的人洗完,彰老會直接在洗手槽脫光開始洗衣服洗澡,露出濃密的胸毛;從隔間洗完抓著臉盆出來的傢伙,可能只穿夾腳拖和一條內褲,三角的,鼓起的形狀一覽無遺。
人滿為患的浴室令我不舒服。太多的霧氣、太多的回音、太多的泡沫、太多的汗味、太多的體毛、太多的肌肉、太多的老二、太多的男性荷爾蒙,像是強姦你的視覺一樣,但他們不這麼想。
「都是男生,有什麼好介意的。」
「不想看就不要看嘛!誰叫你看別人老二的,變態啊?」
言下之意:你不能接受,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至於盛班,明明整天把老二掛在嘴上的,但他洗澡從不露屌。
會在浴室露屌的是阿文,他是連上另一個 gay──是一開口說話大家都看得出來的那種。
作為一個 gay,軍中這群臭直男給了阿文很多的「尊重空間」。例如他裸著身體在洗手台搓洗衣服時,旁邊的水龍頭是不會有人用的;或是互虧身材、開黃腔,言語性騷擾的問題突然就解決了;還有那些男人間的肢體接觸(搭肩、拍背、搔癢、扭打、捏肉、擊掌、碰拳),一面對阿文,他們突然就懂了身體界線,不只不碰觸,還保持一公尺安全距離。
當然,這種「尊重」僅限本人在場的時候。有次在室內保養槍枝,天熱,大伙脫了迷彩服,僅剩迷彩內衣。至於脫下的上衣,隨手扔,槍箱上東落一件西掛一件。
當時杰利正要打開槍箱,隨手抓起一件上衣,攤開一看胸口的名條,是阿文的。杰利觸電一樣馬上把手甩開,大喊一聲:「唉噁!阿嘟 [註] !」
衣服甩了出去,另一人也叫起來,紛紛縮手,那衣服帶病菌似的,丟在地上沒人敢碰。這種小學生似的行為還是讓他們笑了好一陣子,才捏起阿文的衣服放回槍箱上。
盛班都看在眼裡。
「幹!丟遠一點不要碰到我!」他這麼說。
✹ ✹ ✹
大約一年多後,盛班因吸毒被抓到而汰除。對於這個平時大呼小叫、有點瘋癲的士官,連上的大伙有那麼點驚訝,卻又不那麼意外。當我聽到消息時,正在外單位受訓。我想起那次與他在高雄的談話,說得其實不多,我只能試著拼湊。
他告訴我,他是台北人,家人也都在台北,然而他南遷,找了老婆,還在高雄買了房子。
他告訴我,放假回高雄家裡,就得做一堆家事、還被老婆嫌、動不動就吵架。
他告訴我,越來越不想回家,但那明明是他買的房子。他說話的聲音不粗了,但像混著沙,他考慮要離婚。
而我問,那回台北的家呢?他並沒有回答。
想起大學遇過一個劇場老師,鑽研聲音表演。他說,聲音是從身體長出來的。一個人用哪種嗓子講話、用什麼位置發聲共鳴,都是有原因的。
阿文一開口,直接把櫃門給開了。那聲音細軟、鼻音重,字句間是用黏的,還帶點嗲聲嗲氣。部隊那伙人聽這種聲音,像見了黃綠色的黏稠鼻涕一樣,避之唯恐不及。交朋友?別傻了,沒被霸凌就要謝天謝地。
而盛班呢?像被鋸子刮過一樣的聲帶,嗓門大到像改管車狂飆,在這喧囂的環境裡,他融入得還不錯。那是聲音的迷彩。
但在我聽來,那聲音卻是如鯁在喉,像吞了什麼不該吞的東西。當年我們去南部出任務時,夜半,我睡上鋪,時不時聽見他下鋪傳來咳嗽聲,是那把鋸子正來回切割。我總想像,他咳出來的不是痰,而是鐵鏽一般腥紅的碎屑。
註|阿嘟(Adju),源於台灣原住民排灣族語,原為對生理女性姊妹、好友間的親密互稱,經語意演變,目前也用以指稱性別氣質較陰柔的男同志。(回到上面)
【有一種性別認同叫迷彩】
有一種性別認同叫迷彩。他們陽氣過剩、精蟲衝腦,他們歧視男也歧視女、黃腔滿口橫飛。性平教育 20 年,在軍中只是一本簽到簿。
【東雨】
畫過圖、寫過詩、跳過舞、演過戲,但不喜歡被稱文青(現在也不年輕了)。怕苦、怕難、怕死,練體能像會減壽一樣,卻穿上虎斑迷彩,簽了四年海軍陸戰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