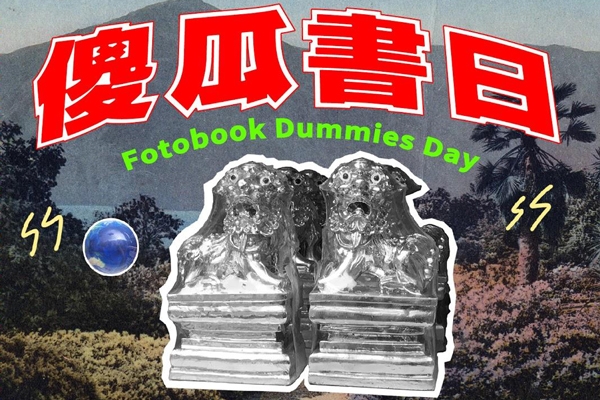【年末聊聊】潘怡帆 ⇄ 王湘靈:最近有在創作嗎?這種有點心煩的問句
𝒘𝒉𝒆𝒏_ 節氣大雪
𝒘𝒉𝒆𝒓𝒆_ 台北一處風光明媚
𝒘𝒆𝒂𝒕𝒉𝒆𝒓_陽光溫煦
𝒘𝒉𝒐_ 潘怡帆 ⇄ 王湘靈
在離開編輯工作之後,很久沒有採訪了,這次受 BIOS monthly 委託一起參與專題,不免有點緊張。不過編輯說這專題比起採訪,更像是聊天,希望帶有平等而親切的氣氛,並讓我任選聊天對象。於是,我一邊嘴上跟編輯抱怨著「好麻煩啊」一邊又像在挑禮物一樣興奮。BIOS monthly 給了我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讓我可以有憑有據地向想要親近的人提出邀請。
我想起湘靈。我和她一直保持著「大約知道彼此近況,卻一次也沒有約出來聊天」的狀態。但我時常想起她。
第一次看到湘靈的作品,是在 2019 年的年底,我和湘靈一起參加了 《VOP 攝影之聲》主辦的後藤由美藝術書工作坊,湘靈將《快要降落的時候》中的部份照片帶來當作書本的素材。照片中有點飄飄然、又有點悲傷的氣氛,讓我非常難忘。即使那些照片當時只是作為 moodboard 被率性地貼在牆上,卻仍有撼動人心的魔力。這是我這幾年少有的照片觀看經驗。那樣的照片對我來說,比起藝術創作,更像是魔法的延伸。
湘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音樂背景的她為什麼選擇以攝影創作?她又是如何定錨自己作為「一位創作者」?
打開
潘:這壺是熱紅酒,這壺是伯爵紅茶。先喝喝看。
湘靈:這是妳剛剛煮的嗎?
潘:我整個早上就在弄這個。因為我想到要聊創作,壓力就很大,可能也是一個覺得自己沒有在創作的罪惡感⋯⋯反正越靠近這個對談,我越是逃避——哎、我就花很久的時間,研究今天要買哪一種起司。(大笑)
湘靈:真的喔,我也是,很久沒有這種⋯⋯訪談?被訪問會覺得太被關注,好像一定要講點什麼。
潘:應該滿多人都覺得妳有點神祕。
湘靈:沒有沒有,我就是喜歡待在邊邊,我沒有喜歡在中間。
潘:嗯。滿好奇妳現在每一天大概長什麼樣子?
湘靈:早上和下午會看一些書、整理創作的事情或計劃等,晚上就很廢。現在生活比較規律,因為我最近開始練習跑步。
感覺到自己年紀不小了,體力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好⋯⋯然後我覺得,創作其實常處在一個高壓的狀態,所以找到一個紓壓的方式好像還滿重要的。最近幾個月開始跑步。不過我超不擅長長跑,以前跑個800公尺就不行了,但就想試試看。現在慢慢練習之後發現,身體真的比你想像中的有能耐多了。
我都是日落前去跑,所以五點前我就必須要完成當天的工作,也因為工作時間變少了,我就知道,喔、不行,我白天不能做一些很廢的事喔,不然事情會做不完。
潘:妳會做什麼很廢的事?
湘靈:噢,我晚上都在看廢片。一些 YouTube。或是什麼貓貓狗狗的影片。
潘:妳好不像會看 YouTube!
湘靈:我看超多的。像是好口唄、叉雞啊、豆漿⋯⋯我前陣子沉迷於看人家開箱跑鞋。(大笑)
潘:好看嗎??
湘靈:很好看、我本來才不相信穿什麼跑鞋,就能提高跑步的速度,想說屁啦那是商人的計謀吧。但 1111 的時候很便宜,我看到原價 4200 變成 2400,我就!哈哈哈。
潘:我 1111 的時候也做了類似的事,而且跟運動相關,就覺得這個消費是為了身體好,比較沒有罪惡感。
嗯?明明說要聊創作,結果是一個沒有靈性的開場。
湘靈:我覺得這樣很好啊!好像也不用一直聊創作,這樣隨性滿好的。

潘:我從小一直到大學,都算是害怕社交的人。就算是跟最好的朋友週末約出去玩,我當天早上都會寫小抄,寫說今天要聊的項目有哪一些,還會準備笑話,想說乾掉的時候要不要講笑話⋯⋯
湘靈:真的嗎?感覺不出來,真的感覺不出來!在我的印象中總覺得妳是很會表達自己想法的人,不太需要去迎合別人的喜好的那種。
潘:嗯,想起來滿好笑的。
湘靈:妳的 16 型人格是哪一個?
潘:我有點忘記,好像是什麼 INFJ?那妳是什麼?
湘靈:我是 INFP。IN 比較內傾,它的標籤是調停者,好像是比較擅長聽人講話的類型吧。
潘:妳覺得妳是嗎?
湘靈:我噢(笑)滿多人會來找我講話的,聊一些人生方向什麼的⋯⋯

潘:妳本來就是一個很打開自己的人嗎?不會害怕讓大家看到自己比較脆弱的部份,這種揭露⋯⋯?
湘靈:我好像是不知不覺變成這樣的。到紐約上課是很小的班級,課程裡教授會一直和我們探討、人生的際遇或處境。看到旁邊的人都這樣做的時候,好像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奇怪,自然而然就發生了。也有遇過比較特別的同學,因為不想面對自己,所以從學期初到畢業,拍攝的照片都在試圖隱藏些什麼,但教授一看就懂了,這好像又是反向的揭露⋯⋯
潘:會有這個好奇,是因為我從中學到大學,本來想做的都是文學創作,寫了很多東西。但後來我發現自己其實很怕被看見內心真實的想法。一方面很希望有人可以理解我,希望有一個讀懂這一切的人,但另一方面很害怕我寫的東西會讓別人不那麼喜歡我,怕他們會看到「原來我是一個這樣的人」,或也怕我寫的東西會去傷害誰。
後來就漸漸地,變得很想要逃避使用文字,轉往以影像為主。影像可以藏很多東西,可是久了,又覺得,我是不是一直在逃避?好像如果真的要創作,不能藏著不說?
妳把作品展出來,會擔心被身邊的人看嗎?
湘靈:好像不太會。如果擔心的話我應該就不會公開展示,可能只給自己看嗎?但這些我好像都還好,甚至好像沒有真的想過這個問題⋯⋯至於家人的話,他們會去看展覽,但畢竟他們並不在這個領域,可能也也沒辦法理解全部⋯⋯或是有時他們問我這件作品是什麼意思,我會講的比較模糊(笑)。
但仔細回想,我反而是希望作品做出來,身邊的人能夠讀懂,其他的我都沒有太在意。
潘:我發現妳感覺滿隨遇而安的,妳覺得妳是嗎?
湘靈:嗯,年紀再輕一點的時候我也滿憤世嫉俗的。後來漸漸發現很多事情計劃都趕不上變化,好像想這麼遠也沒用。不過講是這樣講,我平常也是會想很多。
自由
潘:妳現在有固定的工作嗎?
湘靈:目前就是一個禮拜有幾天教鋼琴,剩下的時間做創作。
潘:妳喜歡教鋼琴的工作嗎?
湘靈:還滿喜歡的,我覺得教鋼琴和創作這兩份工作可以分得比較開,用腦和執行的方式不太ㄧ樣。這樣對我來說好像比較適合。我其實滿喜歡跟小朋友互動的,很多時候天馬行空的對話也會令我哭笑不得。
潘:所以妳現在主要的生活就是鋼琴跟創作?
湘靈:對,目前來說是這樣。
潘:我現在跟妳很像。九月底離職後,我一個禮拜進公司兩個半天。
我會好奇妳的生活,是因為三年前到 BIOS monthly 做正職之前,當了兩年的 freelcancer,那時候覺得人活得自由自在,不用想太多。可是這一次離職,會覺得如果我在家不好好規劃時間,整個人好像會變得飄飄的。所以現在還滿喜歡看別人寫的一些時間規劃的方法。
妳剛剛說妳每天早上是在讀書和創作,那個「創作」會是什麼樣子?
湘靈:我想一下喔。嗯,應該說我會花很多時間在前置,會在筆記本上一直寫、一直寫,常常前面都會卡關,做一件作品會在前面卡非常久。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寫字。
潘:寫下來的東西,會是心裡頭一些很雜亂的想法嗎?
湘靈:剛開始都會寫一個很大的方向,有點像是畫一個很大的圓,不是很 precise 那種。所以會一直從比較大的範圍,開始慢慢往裡面、往裡面、往裡面,才會越來越多 detail。我不是那種,「今天有個展覽、我下個禮拜就可以給一個完整計劃」的人。
潘:妳通常卡關,是會卡在什麼樣的地方?
湘靈:卡在「要用什麼方式作呈現」吧。我覺得要用自己的語言去轉化一件事,是最不容易的。
潘:噢,好不一樣喔。對現在的我來說,最不容易的是,我對很多事情都變得沒有感覺了,沒有任何想要創作的題目。
我在倫敦唸攝影的時候,也是花了一些時間,才漸漸摸索出可以發展的題目。回想起來,那時候自己的狀況沒有非常理想,倒不是有什麼病痛啊,可是生活在一個遙遠的地方難免有點孤單,以及,唉⋯⋯碰到很多很賤很偽善的人,每天都要遭遇一大堆狗屁倒灶的事情,人就變得非常地憤世嫉俗。
走進英國的植物園,看到在溫室裡的熱帶植物,因為生長環境的需求相似,亞洲的竹子和南美洲原生植物被種植在一起。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熱帶植物,被搬來溫帶國家展示。看到這個畫面,我覺得很荒唐,也有點忿忿不平。
《Rash》是這樣來的。我一開始沒有很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的拍攝動機是這樣子。是之後受邀去 Lightbox 的講座分享作品,阿定(創辦人曹良賓)幫我的專題總結時,他說:「怡帆創作的起心動念,是來自憤怒。」我才想說,對耶,好像是。
但現在已經回來好幾年,沒有那麼氣了。也讓我一直無法完成這個東西。我覺得憤怒是一個很強烈的情緒,它驅使我創作。但我現在的生活過得很順,我就不知道我要幹嘛。
最近會在想,我會不會其實只是為了要成為創作者,或我很希望自己是藝術家,所以才開始做創作?
妳是怎麼開始的?妳本來不是學音樂嗎?那妳在學音樂的時候,會認定自己就是創作者嗎?
湘靈:不會。音樂比較是去展現妳學到的東西,我念的是音樂演奏,訓練上比較是詮釋各個不同年代作曲家們寫的音樂。所以不會覺得自己有創作,至少我自己在那時完全不會認為自己是創作者。
創作的初始喔⋯⋯如果真要追溯到源頭的話,大概是我十八、十九歲的時候吧,開始看一些廢片,什麼 G.I. Joe⋯⋯像是一群人把以前原本很天真的卡通,配一些很低級的對話。就是看那種東西的時候,覺得哇好 khiang 喔!好鬧!
妳知道,唸音樂班是很嚴格的,音樂體系裡也不會有太多時間接觸其他東西,但比較大了之後開始有比較多自己的時間,可以看這些廢片、聽音樂啊、或是一些較非主流的電影和小說,發現其實喜歡的不只有音樂,我對音樂以外的世界也很感興趣,有一陣子甚至認真想去學立裁,但是,如果那時候這樣跟我媽說「媽,我研究所想唸服裝設計」,我一定馬上會被罵死。知道家裡會反對,所以其實就一直就是放著。

潘:所以是到紐約唸書,才真正開始決定創作?
湘靈:我去紐約一開始還是唸音樂演奏啊。但可能跟環境有關係,剛搬到紐約時,多了很多獨處的時間,那時候會一直去思考自己的個性、自己是怎樣的人等等。紐約的藝術文化很活躍,當時因為還是學生,所以可以用很便宜的票價去看展覽或聽音樂會。好像到某一個時期,就突然很明確的知道自己真的很想要做這件事。
潘:那後來為什麼選讀攝影?
湘靈:也想過要不要唸室內設計,但仔細看身旁在唸室內設計的朋友,他們學的東西裡,我可能只對其中一、兩個領域感到興趣。也曾經考慮過還是要繼續念博士之類的⋯⋯但我一直都有在拍照,一直都很喜歡。回想起來、為什麼唸攝影喔?⋯⋯其實好像很單純,就真的非常喜歡拍照吧。
喜歡的事很多,但在那些選項之中,好像只有拍照是一件很純粹、非做不可的事。
潘:我記得妳三年前傳訊息給我的時候,提到自己在藝術創作跟生存之間,有一些搖擺跟掙扎。但妳現在還是繼續在創作,妳應該是真的很喜歡藝術?還是說喜歡產出東西?
湘靈:我覺得應該是前者。因為如果是喜歡產出,也可以從音樂裡產出,像是累積到多少曲目等等,但比起音樂,藝術有更多面向。
潘:妳覺得攝影是一個相對音樂更自由的表現方式?
湘靈:對。如果真的要比較的話,古典音樂真的非常地嚴謹。但兩者的表現方式不太一樣,音樂的詮釋,有點類似工匠用相同的工具,長時間琢磨同一件作品;但以影像來呈現,就可以是比較多樣的,所以對我來說自由性與開放性是比較高的。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非常喜歡古典音樂。
潘:嗯,那後來真正以攝影作為創作手法、直到現在,妳都覺得自由嗎?還是有所限制?
湘靈:一開始是什麼都不懂,真的想拍什麼就拍什麼,亂拍一通。完全依靠直覺創作。當然開始做展覽後就會比較謹慎,想要認真討論一件事情時,就會希望自己提出的觀點不是天馬行空的。至於會不會有所限制,我覺得每一種媒材都有它受限的地方,但現在我會希望自己可以想辦法去克服這些,而不是遇到問題就想說啊算了——突然覺得自己很樂觀 。(笑)
潘:我前陣子才回想起,真的非常非常久以前,小六的時候參加了一個在美國的 Summur camp,因為要跟美國小孩玩,可是那時候我英文又有點爛,就不知道要跟他們講什麼,我就每天一直看著天空發呆。
每天看著天空就會覺得:「哇,今天的天空好美、這個雲好美,我一定要把它拍下來。」然後我就真的每天都在拍天空,後來回台灣照片洗出來,每張天空都長差不多。(笑)
湘靈:好可愛喔、好有畫面。感覺妳小時候就是個小小藝術家。我小時候很屁,小六時都在幻想外星人從飛碟走出來時要怎麼和他溝通⋯⋯想起來還真好笑。
潘:很羨慕那個時候的自己,因為現在很難再有這樣的時刻了。
像前陣子我跟我先生去冰島玩,會想要拍很多東西,可是同時心裡就又會覺得「啊冰島就已經很多人拍好了,我拍也不會比較好看」,被這樣的心情不斷地輾壓,然後心裡又會冒出一股「不行,我一定要拍出跟別人完全不一樣的視角」⋯⋯
就是有太多這種雜念,我也覺得很煩。我明明可以在當下,為自己留念就好了。
湘靈:嗯,妳想好多喔!
潘:妳不會嗎?不會有那種想要戰勝別人的心情,或是想要拍出自己視角的東西?
湘靈:不會想戰勝別人,但會想要拍到很特別的東西。可是常常 36 張照片裡,只有一張可以用。這種狀況是很常發生的。
潘:妳的照片,我好像拍不出來。妳的照片好像是一個很需要安靜、有一點遙遠⋯⋯我拍不出這樣的氛圍。就算我真的拍出了一樣的畫面,很可能我也不會從毛片中把它挑出來。這樣很安靜,甚至有點空的畫面,也許會被我覺得「這是一個沒有完成的照片」就被我收在硬碟裡。
湘靈:妳覺得拍不出我的照片,我也拍不出妳的照片啊,因為那個就是妳啊。
其實我也都沒有「做完了」的感覺。可是當有一個展,或是有明確 deadline 的時候,到了那個點,可能就要階段性地完成它。
潘:所以如果今天國美館的展覽跟妳說展要推遲一年,那妳心中離這個作品的 deadline 就會跟著再往後,妳會想再把它做得更好?
湘靈:對,但有時候不一定會更好。有時候搞不好就一直拖。
啊最近有在創作嗎?
潘:妳去年有去駐村對不對?
湘靈:嗯,我去年在柏林的貝塔寧藝術中心待了半年。
潘:妳是喜歡去一個遙遠的地方創作的嗎?
湘靈: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可能兩三年會想要暫時離開原本的環境,也是轉換和整理一下心境吧。但不會想要一直不間斷的駐村。
潘:妳在紐約唸書的時候,待了比較長的時間,妳喜歡嗎?
湘靈:在川普當選總統前算是滿喜歡的(笑),不過我喜歡的是這個城市而非國家。歐美文化相對來說較個人主義,人跟人之間的距離好像不用這麼近。那個城市的氛圍就是,每個人都是一個很獨特的存在。
.jpg)
潘:好奇《質變》是妳在紐約做的作品嘛,妳有說過當時妳刻意讓自己處在比較孤獨的狀態?
湘靈:嗯,該去的 party 還是有去啦。但當時念攝影只有一年的時間,後期把所有心力都集中在做這個 project,為了讓自己維持在專心的狀態,每天真的只做一件事情:做作品。
完全沒有社交到——有天晚上,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紐約朋友上傳的年夜飯照片,才驚覺今天是除夕,大家都在中國城一起吃年夜飯,這是每年的固定行程——突然覺得自己彷彿與世隔絕⋯⋯現在想起來也是有點不可思議,不知道當時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潘:妳是享受在國外的感覺嗎?
湘靈:每個地方都有一些我滿喜歡的點吧。比如說在歐洲,大家可以生活地比較隨性,到哪都可以席地而坐,對物質的需求不會那麼高等等,這些是我覺得待在國外比較舒服的地方。但很多事都是一體兩面的,好的地方同時可能也會有其他的問題。現在會覺得心態比較重要,否則去到哪裡都一樣。
潘:妳是不是常被講過很爽?
湘靈:有時被問說最近在幹嘛,回說,喔在想新的作品,可能也會有人說:「就這樣喔,妳也太爽了吧!」我心裡想,我也只是懶得解釋那麼多好嗎。
潘:滿無禮的。
湘靈:對啊,我就想說:「如果就這麼爽就好啦,我也想要那麼爽!」
.jpg)
潘:最初從國外讀書回來,會很理所當然地覺得要繼續創作,但同時也要接案維生,可是我得失心太重,很常放太多心思在接案上,也很難專心創作。所以 BIOS monthly 找我去做藝術指導,我就想這樣很好,可以做離拍照沒有太遠的事,下班之後也可以繼續創作。
後來三年過去,我完全沒有再碰創作的東西,本來一直想像下班後或是週末可以做這些事,但就真的提不起勁。
現在離職,也是一個轉捩點吧。覺得自己可能沒有要繼續在藝文產業,或也沒有要繼續創作。我可能會想要去一個比較容易賺錢的地方。
湘靈:可是⋯⋯真的喔?那妳還會想要把那個書做完嗎?(編按:2019 年湘靈和潘一起參與後藤由美的藝術書工作坊時,創作的藝術書)因為說真的,我好喜歡那本書,到現在想起來還是印象深刻,還是妳覺得已經過了那個想做的時期?
潘:我一直到最近才發現,我自己是一個很沒有行動力的人。我其實很想要把這個東西做完,可是我有點不知道要怎麼把它完成。所以看到妳可以完成很大的展覽,就覺得哇好厲害。《快降落的時候》妳有寫一篇感謝的貼文,謝謝很多人幫忙,我就想說,要跟那麼多人溝通、要做那麼多事情,我做得到嗎?不知道⋯⋯
湘靈:我其實臉皮很薄,自己能完成的事就不會想麻煩別人。做一檔展覽,有時在技術上需要各方面的支援,合作的對象就會越來越多了,說真的,沒有這些專業人士,我一個人也不可能完成⋯⋯
潘:那妳現在為什麼會往複合媒材轉去,複合媒材又需要更多支援吧?為什麼會想把事情變得複雜?
湘靈:可能會覺得,現在只用攝影,好像有一種話還說不夠的感覺。
潘:那妳有覺得最近的幾檔展覽,有把話說完了嗎?
湘靈:沒有啊,每一檔都沒有。我多多少少還是會在意。這種感覺和詮釋音樂很像,它就是永無止境。你永遠都會覺得可以再更好,哪邊還可以再修正。
潘:我感覺妳的創作節奏,不是那麼頻繁,也會常常想妳可能要花很多時間感受自己或發功之類的⋯⋯
湘靈:嗯妳在信裡有說,好久不見的朋友會問妳「現在有新作品嗎?」這我很有感,我被問得更直接。曾經一個編輯第一次見面就問我:「欸妳現在,還有在創作嗎?」我還記得當時我回:「有,只是做得比較慢。」
潘:真的很常被問這個問題!前陣子我去草率季,隨便亂逛,有一個攤位進了很多攝影書,賣的人看我在那邊翻非常久,他就問我,妳是創作者嗎?然後我想說:我是嗎?我有點回答不出來,就說:「我是坐辦公室的。」他就一副「我懂啦、沒關係啦、大家都這樣啊」最後我要離開的時候,他說:「還是要記得創作喔,這樣人會活得比較穩一點。」
然後我想說,我懂你的意思,可是——你管我!(笑)
湘靈:這個問題其實很敏感,我不會這樣子問別人。因為有些人可能被迫暫時放下創作
先去做別的事,我自己也曾有過這種經驗。我只會問「最近在幹嘛?」如果想講,他會自己講。
潘:有時候如果被藝術圈的人問這個問題,心裡又會有一點不服氣地想說,很多接案的工作,我也是用創作的方式來執行的啊!可是即使有這樣的不服氣,我其實好像也沒有說出口的勇氣。因為我知道,那在他們眼裡不是創作,我自己其實也有一點懷疑。
湘靈:我覺得,妳覺得是就是耶。妳覺得這是商業案就是商業案,但妳拍完,覺得這是妳的創作,那就是。完全看妳怎麼定義。我自己覺得,要用創作的角度完成商業案很不容易,除非有些建議能給妳實質上的幫助,不然其實別人怎麼看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潘:我後來也是抱著這樣的想法。
湘靈:但現在如果被問到「最近有在創作嗎?」這種問題,我好像不會那麼尷尬了。現在好像比較接受自己原本的樣子,你現在是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然後你現在有創作就有創作、沒有創作就沒有創作。人每個時期都會有不同的變化和優先順序,有時候你把 A 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但可能過了幾年 B 又比 A 重要。對,所以我覺得不用想太多。
潘:那現在創作對妳來說,還是重要的嗎?
湘靈:現階段創作當然是重要的事。我很認真看待每一次的創作和過程,也希望可以一直持續下去,但現在不會擬定太久遠的計劃,比如說十年後ㄧ定要怎麼樣。世界一直在變,現在可以創作,可以在當下很努力的去把作品做好,我覺得很開心也很感激。這樣就好。

【年末聊聊】 take a seat, and talk a bit
歲末年初,結束與開始的時刻,按下暫停,回頭與往前探探吧。在溜進喜悅與不安交織的生活伏流之前,展開一場深談、一次散步、一通難眠時深刻的電話——找一個人聽聽自己的疑惑,聊聊自己身在何方?
這次我們拉了一把椅子給自己,編輯部的成員坐上去,邀請一名喜愛或充滿好奇的對象與自己對話,也許親密、也許閒散、也可能正經八百⋯⋯但保證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