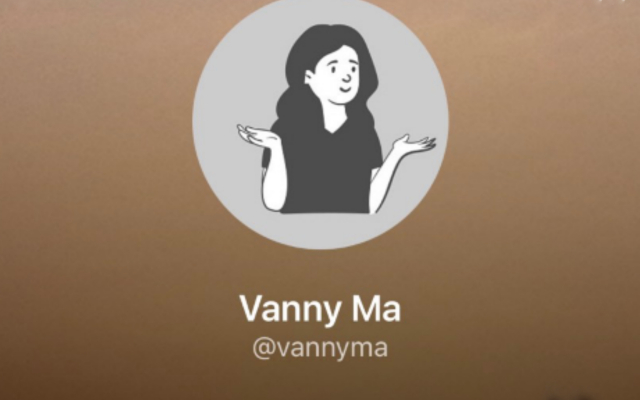主持人,是讓別人留下來的人──專訪馬世芳
意外的是,就連聚集了長期收聽馬世芳《耳朵借我》廣播、自發上傳分享節目錄音檔的忠實聽眾的臉書社團,也一直到今年一月才出現第一篇有關他主持公視新一季《音樂萬萬歲》第四號作品的貼文。那位網友絕望地問:有人知道家裡沒有電視的話要怎麼收看節目嗎?馬世芳本人也在那個社團裡,難得浮出水面:「恪於音樂版權,目前暫時只能電視收看喔。」恬恬淡淡。其實訪問那天,他面對這個問題時更激昂一些:「我個人當然非常希望《音樂萬萬歲 4》可以直接上 YouTube 啊。拍得這麼好、花這麼多錢、搞得這麼累,why not?但不行,版權非常麻煩,重製權的取得是一件極其辛苦的事⋯⋯幸好至少我們十二月下旬開始會有重播了。但好像也只能重播一次。」

閱聽者終究被這個時代寵壞了。線上串流讓人們從只能在固定時間收看節目的限制中解放,純聲音無影像的 Podcast 也逆勢回歸,因為沒有畫面的它甚至把我們的雙眼也解放了。有時候不是人們不願意守在電視機收音機(或手機)旁等待,而是連這麼做的時間也被切碎到生活的其他部份。網友這樣問,想必是真心愛馬世芳的節目,只是連這樣的觀眾也不免想知道除了傳統媒體外有沒有更方便的管道可以走。
拉遠一點看整個音樂產業,不只傳媒,唱片工業也不再掌握聲量大權。這樣的背景下,音樂節目如何有機地經營,獲得維持運作所需的轉換率?他先是笑說前年他和陶傳正主持的《閃亮的年代 Yesterday Once More》入圍金鐘,但因為比較少在做音樂節目了,所以被列進綜藝節目獎裡,「和胡瓜、許效舜、黃子佼同一個項目欸⋯⋯這不好意思啦⋯⋯人家在這領域耕耘那麼久。」然後反問我:也對,現在這個時代到底怎麼去理解「明星」?「比方說你的世代,從你童年以來,周杰倫之後,還有誰是真正的大明星?羅志祥?」
「我可能會說陳綺貞?」
「OK,maybe,但陳綺貞就不會是你們全班同學都聽的,對吧?而且,這些人其實也都是二十世紀的音樂人了。已經二十年,沒有那種所有世代所有人都在聽的歌手。」
他說,當然不是因為現在的歌手唱得不好。他那個世代的聽眾是報紙廣播電視餵大的,唱片行東西多,大家要挑聽過的名字買,而新名字從媒體來,於是他們甘願守著收音機聽全國首播。但現在,頑童在小巨蛋連辦三場演唱會、茄子蛋的 MV 破億流量,他們可完全沒有買電視廣告。「以我做廣播的經驗來看,我很清楚,現在打開收音機的聽眾不是為了想要聽沒聽過的新歌,而是想聽你能給我什麼 KKBOX 或 Spotify 沒有的東西。」
「如果主持人是做一個人肉播歌機,我何必呢?」
不能只是翻譯
他的話,讓人不禁想起台灣還把西洋歌曲喚作熱門音樂的時代。作家熊一蘋在《我們的搖滾樂》書裡點名過台灣最早做起西洋歌曲廣播節目的主持人亞瑟,一開始也只是請赴美留學的朋友寄唱片回來、再放到節目上播出。那時的音樂節目主持人更像是未知事物的引介者、翻譯者。比起關於歌曲的軟知識量,歌曲資料庫的硬庫存量(也就是架上唱片和卡帶擁有量)也很重要。那是馬世芳言下之意所謂「聽眾聽廣播仍是為了想要聽新歌」的時代。
有趣的是,當年亞瑟節目的繼任主持人陶曉清,就是馬世芳的母親。沒問他小時候是否曾在家中看到聽眾寫的明信片──據說當年廣播電台之所以請聽眾改寄明信片,是因為寄來點歌的信太多、多到要用明信片來省下主持人拆信封的時間。那是他母親當主持人的時代。如今,由於網路,人與人之間坐擁的歌曲資料庫差異越來越小,你聽得到的他大概也找得到。節目、主持人作為新歌引介者的功能也就削弱了。
這是馬世芳身為主持人所處的時代。

入圍金鐘的《閃亮的年代 Yesterday Once More》,或許是音樂節目應對這個環境演變的一種轉型方式。馬世芳很清楚,《閃》是一個服務年長觀眾的節目:幾乎都唱 1950、1960 年代的西洋老歌,他出生之前的音樂。歌曲不是新的,觀眾未必要從節目中認識歌手或曲子,而是回味自己記憶中的聲音。
《耳朵借我》節目則「更任性一點」。馬世芳請來他自己想請的音樂人,不少是剛出頭的年輕歌手或樂團。他們在廣播裡聊更多「心事」,偶爾也帶著樂手樂器到空中做獨家的現場演唱。名字或許是聽眾早就知道的名字,但是向下挖掘縱深,主角從歌曲轉到人物,這又是另一種應對時代的路數。
馬世芳的廣播節目從沒做過收聽調查,他不知道是誰,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聽;但到了公視,有了收視率,他知道電視機前拿著遙控器的人年齡下限落在三十五歲,也抓出觀眾是對音樂幕後較不熟悉的族群。多不熟悉?他說一百個觀眾裡,知道分軌錄音是怎麼回事的大概 0.1 個。
「這不是外不外圍的問題,《音樂萬萬歲 4》這類節目的核心不是要告訴你音樂製作是怎麼回事,也不是要告訴你慣用編曲是什麼意思。而是你打開看到漂亮的舞台、覺得哇這歌好好聽、這收音收得真不賴。」
光弦樂就有十一把,管樂組、弦樂組、吉他、貝斯、合聲加起來二十一個樂手,外加 4K 錄製規格,攝影棚裡午晚兩餐加起來一百多個便當的團隊。這是《音樂萬萬歲 4》應對這個時代所提出的可能:他們要保證觀眾打開這個節目來看的時候、永遠都是好聽的。

《音樂萬萬歲4》錄影現場。
從上萬子彈裡挑選一顆
聽起來單純到有點老生常談的一句話,背後有千絲萬縷。馬世芳說,台灣音樂節目一直以來最被詬病的事情就是音質──有線電視的最後一哩路建設不足,大頒獎典禮轉播時大家常說聲音爛;其實看 YouTube 直播聲音都很好,是到了第四台才爛掉的。
「公視這個節目,真正厲害的地方是你看不到的地方。收音。」他繼續說,「我們找這麼多不同風格的音樂人來唱各種不同風格的歌,後期一定要做到聲音是好的。但這個事情大家看不到,是技術問題。那都是功夫。」
他聽節目製作人張硯田聊去 NHK 參觀的事,看別人的舞台怎麼弄、棚怎麼弄,回來只有一個結論:我們要很努力。「人家做了五十年,那個規格、經濟規模、技術高度,我們想都不用想。但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樣就放棄吧?」

有限的範圍裡,有些事還是能做。經費沒有外國充沛,但可以在細節上做調整,例如打光,色溫怎麼佈置,sense 一對,就有質感。「《音樂萬萬歲 4》我覺得有做到,它視覺上不再是以前我印象中的台灣電視節目那樣大紅大綠、彩度很高,一種美國酒吧或兒童樂園的感覺。這也是功夫。」
雖然他一再提到,這是在經費不足的狀況下以技術作出的最大努力,但他也說,放眼台灣電視圈,能花得起這樣的工夫和功夫的,也只有公視了。
「我後來發現,有時候他們 take 1 跟 take 2 的打光邏輯完全不一樣,顯然導播也在嘗試。導播一天到晚在想各種怪點子,想這個節目還可以怎麼樣、不要那麼⋯⋯那麼理所當然。歌手有時候可以坐在前面、有時候可以站到後面;主持人進場出場到底要怎麼設計⋯⋯在公視攝影現場隨時可以試試看這些,現在的商業電視台大概都沒有這種餘裕。」
人力規模上,這是和做廣播主持完全不同的等級了。《耳朵借我》只有他加上一個手上還有其他節目的企劃同事;2015年和中國合作的網路節目《聽說》,團隊都是台灣人,也只有十人左右。現在身在一個五十人的團隊裡,「這完全是一件勞民傷財的事。」
主持人在這樣的規模裡,角色的重量自然被稀釋了。在廣播節目裡,馬世芳播歌跟談話的比例各半,但在《音樂萬萬歲 4》,訪談時,一個段落最多就是三分鐘。他知道他對節目內容的貢獻,頂多就到某個比例。前期他會跟製作人、企劃一起討論主題、歌手人選、歌單,聊完之後他就放手不管。接下來就等錄影通告,錄影前一個禮拜他會收到腳本;到了現場,企劃再和他對一下今天有哪位歌手、會講到什麼。「我要做的,就只有把這些東西裝備在我身上而已。」
他說得謙沖,其實誰都知道上場時間越短、主持反而越困難。縱然軟知識庫彈藥充足,要從上萬顆子彈之中選擇一顆來發射,套他的話說,這當然也是功夫。
後來,馬世芳為這樣的大製作摸索出的主持方式是「情境化」:優客李林的〈認錯〉這首歌,是當年李驥和情人吵架分手,結果自己很後悔,想要挽回,沒想到跑回去找這個前女友的時候發現,啊,她坐在別人的車裡。他悔不當初,寫出這首歌來,但一直沒有歌名。好不容易出唱片,大家看這個歌每一行歌詞都在認錯,所以就給它〈認錯〉這個標題。
「這就是個不錯的情境、不錯的故事,我就把它講出來就好。我不用再去講當年它排行榜第幾名、賣了多少張、點將唱片是怎樣的公司。這些囉嗦的部份就免了。」
不是大量地給予,而是有效地省略。這是主持人馬世芳如今所選擇的主持策略。

留下別人的人
說起《音樂萬萬歲 4》安排的歌手,馬世芳很深情:「一方面,我們節目的費用沒辦法每一集都請來大明星,這是一個點;但另一方面,台灣有很多歌手,他們一身本領,但在現在的圈子不太有機會施展,跑去拍偶像劇啊,去找兼差啊,心裡面是有點憋屈的。」
校園民歌時代的口號「唱自己的歌」過了四十年,想不到這句話的意思從文化意識上變成字面上,有歌手真的沒機會唱自己的歌。「你想,明明一身本領,但也沒有機會出專輯、沒有機會做專場。他們來到公視這個棚唱唱歌,很珍惜這樣的表現機會,就使出渾身解數、唱啊⋯⋯二十幾歲三十出頭,這個世代滿多這樣的例子,真的很能唱,工作態度也非常好,這個環境機會沒那麼多,剛好我們有一個這樣的空間讓他們來唱,就來吧!他們也都很好,出什麼題都願意挑戰看看。」
說完,他又面面俱到地補述:那我們當然能力所及,也會盡量爭取大咖啦⋯⋯齊豫姊姊才剛來過,唱我們的過年特別節目⋯⋯女神降臨當然就是好好對待⋯⋯

《音樂萬萬歲4》主持人馬世芳與歌手齊豫。
有大歌手來無疑很好,但聽他講來到節目上的小歌手也真是動人:「我們的固定來賓之一是薛詒丹,阿丹有一副金嗓,人又 nice,什麼歌都可以唱⋯⋯但她真正的本命是爵士樂,對不對?所以有一集她帶了一個做 Gypsy jazz 的樂團朋友來,那就是她的本色──你能想像嗎,〈失戀陣線聯盟〉和〈對你愛不完〉改成 Gypsy jazz!」
「現場我們就想,有沒有可能用這個編制來做獨立搖滾的歌?比方說,〈帥到分手〉有沒有辦法變成 Gypsy jazz?後來我們選了〈大風吹〉,他們當場就接這個球,馬上做出來,阿丹用她的菸嗓唱『哭啊──喊啊──』到『交點朋友吧』之後丟給樂手,樂手把那個節拍加一倍,開始 solo⋯⋯」
YELLOW 和呂士軒來,自己做 beat 的嘻哈人第一次和帶管樂的 full band 一起演出;大家以為 Karencici 只唱 hip-hop、R&B,節目找她來唱西洋經典老歌,完全可以;馬世芳也想找張國璽來唱懷念金曲之類唱將型的歌單,「我們看國璽就是脫拉庫的那個鳥樣嘛,但他其實超會唱的,我十多年前就知道他超厲害。我認為這些都是可以開發的。」
在圈子日久,一個歌手不同樣子的可能,馬世芳看到了。
畢竟知道觀眾最年輕也是三十五歲起跳(「當然我們也沒有很甘願,也希望多爭取一些年輕的觀眾啦。」他強調),節目也必須為此定錨。比方以嘻哈歌手為主角的集數,不能讓不熟悉曲風的觀眾馬上轉台,於是主題就訂為「唱首嘻哈給爸媽聽」;馬世芳說,一旦你給這些歌手好的音樂支援,他們所展現出來的能量,是連長輩都會被說服的。
歌手也樂,很多人從來沒有想像過在攝影棚裡面可以跟有完整弦樂管樂的編制做現場演出,「知道的人就會發現,哇,合聲中間站的是林美璊老師,旁邊彈鋼琴的是屠穎老師。這是很豪華的待遇。」
而剩下的,是他做了半輩子的事了──「一直以來做廣播,廣播是有過路客的。有人轉來轉去,咦,這個歌沒聽過有點意思、這個人在講什麼好像有點有趣,他就留下來。我必須要有這樣的自覺,要讓陌生人不小心轉到這台、聽了五秒鐘,就停下來不再轉了。」
「我要對這些四十五歲以上的觀眾說:『你先不要轉台喔,我們今天主題是給爸媽聽的嘻哈,他們都很厲害,我們樂團很強⋯⋯嘻哈不是你以為的嗑藥啦、亂七八糟的樣子。』」
然後,當他們聽呂士軒的故事,聽國蛋唱〈嘻哈囝〉,他們會被感動。因為那是歌手從生命裡生出來的東西。馬世芳說,身為主持人,他該做的就是想辦法讓人們進入這些。
原來,主持人是那個說服別人留下來的人。

假如有天不主持
錄這檔節目,他通常中午進場。前一天公視團隊先搭台,接著音響要試聲音,第一組錄音人馬早上十點先排練,馬世芳到的時候剛好排得差不多。然後吃便當、化妝、準備錄影,要錄到晚上十一二點,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他們往往連續錄兩天,因為棚已經搭了,只錄一天浪費。
這樣兩天下來,大概只錄兩到三集節目,實際在電視上也就兩個多小時。「那是非常非常⋯⋯縝密而費工的、耗費心力的一個事情。光是換景、調燈什麼都要考慮,這都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
馬世芳說,他心中最難的演出場合是頒獎典禮,第二難就是現場節目,攝影棚裡通常沒有觀眾給演出者即時回饋,幾十個工作人員都專注在自己的職務上,歌手的能量會因這樣的狀態而內縮。「你一個人站在台上,感覺到全部的成敗都看你了,唱完了也沒人幫你鼓掌,一片死寂。助理導播和導播連線,大概會有十秒鐘的空白,是導播在確認。百分之九十的狀況是導播說:好這個很好,我們再來一次⋯⋯有時候兩 take 就 OK,有時候要唱第三次。一直到導播說好,所有工作人員才會一起鼓掌。」
這樣一輪下來,等到訪問的時候,大家都很輕鬆了啦。他邊說邊笑,這次的笑是看多風浪的那種。
訪問時他最怕的反而不是不善言辭、口拙的受訪者,而是已經習慣面對媒體的對象。這樣的人有一整套應對模式,按一個鈕,接下來十五分鐘就講一套,演講般什麼時候用什麼道具、什麼時候有笑話、什麼時候觀眾會有什麼反應,都已預期。
「我都把這種叫做自動導航模式。當對方進入這個模式的時候,我就會問一個必須要想一下的問題。這種問題通常很簡單,比方問他做這張新專輯學到什麼,他總不能說沒有吧?這種時候他們就非得從那個模式跳出來了。」

主持有經驗,但他說自己在電視圈真的還是菜鳥,到現在還不太好意思看自己上鏡頭的樣子。慢慢才知道:眼睛往上看眼神會比較亮,對著攝影機心裡默念不要駝背不要駝背,肩膀放鬆肩膀放鬆。發現自己在台上連要用兩隻手拿麥克風、還是用另一隻手比手勢,都要想個半秒。「我以前看小燕姐,後來看小玲和黃子佼主持,他們的身體都很鬆很自然。再看我自己,連走幾步路都常常不知道手腳怎麼擺。」
很詫異,但又頗為合理的,馬世芳說他在主持上的偶像是張小燕和黃子佼。長大後的他回頭看 YouTube 上 1983 年張小燕主持《綜藝一百》歌曲暢銷榜頒獎的片段,整組團隊拉到高雄勞工育樂中心現場轉播,公布前十名的時候也會讓鏡頭帶到坐在觀眾席的詞曲作者和製作人,講出他們的名字,「我想說哇,他們那個年代就已經在做這種事情了。他們是在榮耀音樂的幕前跟幕後工作者啊。」
「大部份觀眾其實不需要、不想要知道那麼多,但張小燕會在娛樂之中不著痕跡的、把很多內圍的資訊一起告訴你,我很佩服她這一點。」
對黃子佼的敬佩,也是因為看見他身上那份榮耀他人的心。「金音獎他主持了好幾屆,他真的很認真。黃子佼從來不會讓你覺得他在炫耀,他是要成就別人、讓所有人都覺得自己被尊重,而且他又很有哏,這個最難。知識背景掌握到位,搞笑又不會弄得當事人很尷尬,那個拿捏好厲害,我做不到。」
他曾和母親一起上張小燕的節目,為了宣傳母親剛出的書。那天張小燕從早到晚要錄五六集節目,他卻看見她手上那本書裡夾了幾十個便箋,然而整個訪問過程沒翻開書來看、全都記在腦海裡。「不管你是不是名人、是大眾還是小眾,她都一視同仁,讓你感覺被照顧、被在乎,這個非常非常 inspiring。」
回到最一開始的問題。媒體環境改變,大眾習慣也變了,他其實也想過自己有天不再做節目的樣子。如果沒有廣播、沒有電視節目了,自己有沒有辦法變成自媒體?有沒有可能不靠行,做一個網路原生的流行音樂節目?三年多前他研究的結果是暫時不行,台灣目前的法規條件尚無法處理以個人為單位的自媒體音樂版權問題。但他想,不久的未來應該會有辦法的,連 YouTube 都可以弄出一套 Content ID,台灣的版權集管單位沒道理做不到。
如果有天這問題解決了,他會做什麼?「要是有辦法克服的話,很多可能性啊!我可以做那種一集十分鐘、十五分鐘的節目,不定期更新,放我自己喜歡的很冷僻的音樂,which is fine;或者找來賓聊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不用去顧慮尺度的,我都可以做。」
其實就算不靠行,他談起的這些事也終歸回到一位主持人。本想追問下去,問他有沒有什麼除了主持之外想做的事?想了想還是收了口。因為,其實我自己也不能想像馬世芳不做主持的樣子。

公視《音樂萬萬歲 第 4 號作品》
公 視 2019/11/24 起 每週日 21:00 播出
公視3台 2019/12/21 起 每週六 20:00 播出
當周節目預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