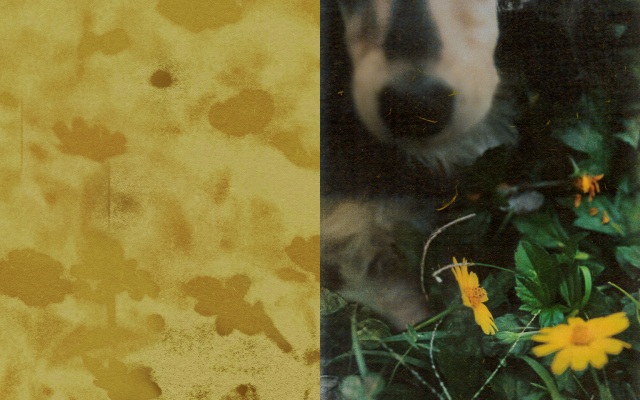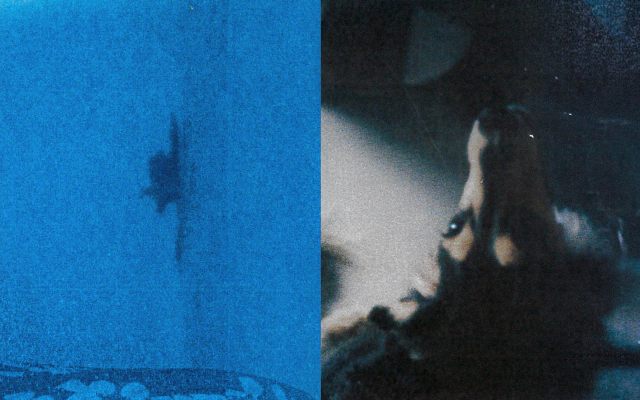Le Bonheur|晴雨交錯的安錫
早晨的安錫下著綿綿細雨,整個城市跟昨天截然不同,在一夜好眠之後被冷空氣狠狠地刺入鼻腔中驚醒了,昨夜難得的倒頭就睡有一種久違的幸福感,在轉程飛行的來去之中,托運的心勉強找到一處可以窩藏疲憊的地方。
入夜後的雨聲窸窣地打散了方才的離別,入夢後的點滴彷彿數十小時前的稀鬆平常,在吸入冷空氣而警醒坐起的那一剎那又被拉回現實,很諷刺地想起李後主詞中的《浪淘沙》,其中幾句點滴勾勒了這種夢醒時分的難以適應——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然而我大抵沒有那種國滅心亡的那種哀楚,也沒有他那樣走入極致的憑欄遠望,畢竟回過神後我處在一個太過美麗而不真實的小鎮,身旁四處是碧眼金髮的外國孩童,他們在青年旅社的餐廳中過度成熟地閒談著,我們慌慌張張地回到現實,趕緊把手上的托盤裝得滿滿、然後隨意得找了個位子,看著果醬上頭印的許多單字一面回想過去一年的法文課程才猛然驚覺——日子的確走得很快,快到我們都還無法自由的運用並記憶這些單字,我們就必須隨時隨地地辨認他們。

眼下不斷下降的溫度與遽增的溼度讓我們走起路來不時得閃避著水花,以一種荒唐浪漫的姿態逡巡著這座古城,我們在山間蜿蜒著走向安錫的城堡(Château d'Annecy)想要一眺雨中的山嵐,沒想到城堡正在整修,我們只得悻悻然地從高小城的高點順勢而下走到了底端進入舊城(但必須要公道地說,悻悻然的是我們,對於城堡本身而言,這卻應該是幸福的時刻,在針對文化遺產的保存上,歐洲大多數國家的謹慎和大方是值得我們借鏡的),而這樣的雨遣散了昨日滿溢的遊人,取而代之的是屬於當地每週兩三次的早市,攤販們在雨棚下頭叫賣,從醃漬食品到風乾的臘腸,從生雞肉到烤雞腿,色彩鮮豔的水果蔬菜也是隨處可見,看著大家仔細慎選的表情,對於生命的專注無意間流露出來,快門只能夠讓我們試圖去抓住那些瞬間,卻怎麼樣也沒辦法讓我們把四周的冷空氣和混雜的各種食物香味給傳達出來——的確,每每在一個極具氛圍的時空之中最難以圓滿的就是整個空間中除了攝像之外的諸多元素,關於氣味,關於濕度,關於指尖冰冷麻木的感受——數位的攝像已經簡省了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諸多想像,文字的功能也因此被大幅削弱,只是我的確在這條早市中聞到了一種有著歷史感的懷錶中發出的滴答聲、一種沉穩而繼續行進的味道,那是從舊城中諸多年輕攤販中此起彼落的叫賣聲中傾洩而出的,沒有章法卻有著類似的節奏,彷彿他們會一直在這兒,和城市一同老去,接著再有一批年輕的攤販,一直一直叫賣下去。

從早市的尾端走出,我們在城市中漫無目的地閒晃著,矗立在湖邊的是當地的遊客中心及圖書館,圖書館的外觀無甚特出之處,但在內裡卻有著一份難以言喻的別緻感受,穿梭高低的空間勾勒出了屬於每一層讀者不同的專屬視野,適當的光線搭配著不那麼整齊畫一的書道擺設,這個圖書館遠較一般制式的圖書館來得更有潛力——某一種趨人閱讀的潛力——而在頂樓的兒童圖書室中則全然沒有圖書館所一貫擁有的靜默,取而代之的是親子間隨著圖畫書中劇情起伏而產生的對話,整座圖書館就在不同的角落以不同的面貌陪伴著不一樣的讀者,大相逕庭的風格卻營造了一種獨特的完整性。

我也樂得在這樣的空間中抵擋著外頭驟變的風雨滂沱,我們坐在一樓靠近外頭的落地窗旁,隨手拾起一本攝影集,沒想到就這樣一頁接著一頁翻了下去,這是 Jane Evelyn Atwood 的攝影作品,其中多是一些社會邊緣或者是邊緣社會的攝像,大戰過後的受難者的臉龐在其中不時浮現,對比四周安詳寧靜的空間顯得有些嘈雜,彷彿都還可以聽見裡頭曾經響徹的警報聲、尖叫聲,小孩失去了手臂卻同時掛著一抹深不可測的微笑,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解讀箇中的情緒,只能無法克制地睜大了雙眼,不知所措地靜靜看完了這一本攝影集,怔然地回到現實後才發現時間並沒有走得太遠,我闔上這本攝影集,試圖假裝它在我的心底什麼也沒有留下,就像那一抹笑容中試圖遺忘的情緒。
現實之中的那場雨也走得毫無痕跡,我們在舊城區裏頭挨家挨戶地尋找著與眼下記憶最符合的景致,嘗試透過明信片來捎一份訊息給遠方的友人,安錫本身集中的景點配置讓明信片透過不同的攝影師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層次感,即使是類似的角度、相去不遠的景點,然而每個光影流瀉的瞬間都體現出這座小城的不同風情,每碰見一張值得玩味的明信片就像是在古城巷弄裡頭偶然碰到的驚喜轉角一般——一個你怎麼也想不到的無名石板坡,在驚喜中出現、於驚喜中結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一條小巷中的骨董店,裡頭的老奶奶不僅僅賣著骨董,也賣著古老的明信片,五六十年前已經泛黃的明信片,偶爾在背面會看見褪去的字跡及郵戳,紙面的邊緣顯得參差而泛潮,時間的痕跡很輕易地在這些二手明信片中被保存下來,而我僅僅花了折合台幣約六十元,就把這城市過去的模樣給擁有了,這的確是一種怪異的感受。

關於這座古城,這片青翠的綠地湖山,除了有著無比的驚喜之外,在湖泊的四周隨意找個出租船享受被湖光山色擁抱是各個旅遊書上都會提及的「經典行程」,趁著雨歇的午後我們也決定踩入這面粼粼明鏡之中,在一整片的青翠之中,我們決定去踩船,或許是因為大風之中碎浪不斷,船身搖晃的緊,我們被吹拂得有些醉意,腳下的踏板不停地踩動著帶我們駛離岸邊,這種腳踏遊船總是可以讓我們更貼近水面,但同時也因此產生了某種意外橫生的畏懼——貪生怕死之徒如我,在每個快門拍攝的瞬間都有所驚懼——憂心著這看似夢幻的水波會有著不期而遇的大浪拍散了遊興,在湖泊中央所感受到的渺小無助讓每個微波輕浪都顯得巨大無比,我們花了些時間吃力地踩回離岸頭較近的地方,終於可以悠閒地休息,把腳輕踩進湖水之中,感受那冰冷沁涼的湖水;此時四處的景致終於也逐漸清晰了起來——岸頭四處的愛之橋(Pont des Amours)上遊人如織,橋頭的人們排隊等著在上頭浪漫一吻,期許永恆愛情的傳說能夠印證其身,而後頭的威斯運河就顯得比較溫蘊內斂,即使她身處在旅遊焦點之中,卻因為河畔交織的樹頭遮蔽了太過刺眼的陽光,提供了一處漫步傾訴的空間。

然而悠閒的日光眨眼即逝,雨滴不爭氣地灑落,我們狼狽地將船踩回雨中的碼頭邊歸還,在滂沱之前瑟縮上岸,整個城市被暮色給浸得濕透,山嵐渲染整座城市的華彩,路旁的攤販與遊人也默契絕佳地逐漸匿跡,安錫的這個夜晚寂靜地只剩下雨滴的聲響,我在青年旅館的交誼廳中書寫著,嘗試用筆桿子去勾勒這個城市忽焉晴明忽焉驟雨的善變、去勾勒著晨光雨露和運河交錯的紋理,然後貼上郵票,在明日的離別之前寄予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