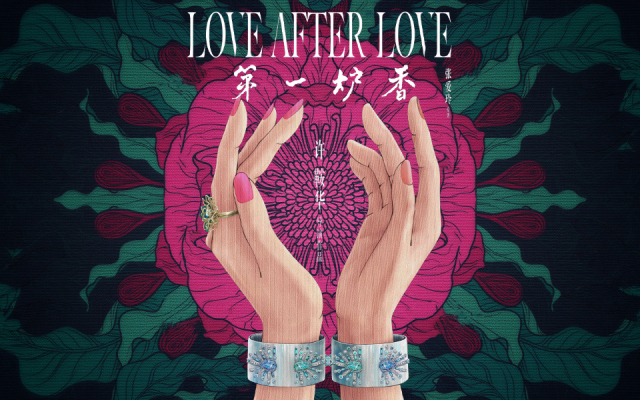《十年》的十年之後:當香港從「不想見到的將來」變成「已然成真的未來」
「我想澄清一下,不是因為我做主席想出風頭,所以來頒這個獎。事實上就是找不到頒獎嘉賓啊,大家都懂吧?也沒必要為難大家嘛,要誰上來頒都不好,對不對?一打開萬一是『那部電影』,我怕你十十十十到極都講不出來。」
2016 年 4 月 3 日,第 35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上台頒發當年的最佳電影,本應是大會的最高榮譽,最佳電影卻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那一晚,沒有人想從自己的口中說出《十年》。
警鐘
《十年》集結 5 位導演,以劇情風格各異的 5 段虛構短片,試圖想像:如果香港社會再不做點什麼改變,10 年後的香港是什麼樣子?
那時的人們還說廣東話嗎?或甚至,人們還能自由說話嗎?2003 年七一遊行全城傾力擋下形同日後《國安法》的《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十年以後是禁忌、笑話還是避無可避的日常?我輩的無所作為,會不會逼得下一代要用更激烈的手段爭取自由?
監製蔡廉明回憶,2013 年底與導演伍嘉良(〈本地蛋〉)開始發想《十年》,是有感於當時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控制逐漸加深,因此希望以電影作為對社會大眾的警鐘。然而籌備期間遇上 2014 年 9 月的雨傘運動,幾位導演不得不修改劇本,以回應社運後的社會氣氛。

伍嘉良〈本地蛋〉劇照。
片中想像的未來,都正中那曾被允諾「馬照跑,舞照跳,50 年不變」的城市,最深層難言又無法逃開的集體焦慮。這部電影並不試圖清創或療傷,而是呼喚人們:再坐視不管,電影裡的虛構情節,就會是我們都要承受的未來。
也因此,《十年》2015 年底在香港上映時掀起滿城風雨。有評論認為以 50 萬元港幣的低限製作條件下,《十年》展現出高度的勇氣與創意,然而也有人認為它技術層面粗糙,只是因為正好呼應雨傘運動後的社會氛圍,才受到矚目與讚賞。
隔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更引發公眾譁然:《十年》沒有入圍任何演員或技術獎項,卻一舉打進最佳電影的最後五強。它只入圍這一個獎項,而且還真的得獎了。
到底憑什麼?所有人都在問。只要議題夠敏感正確,再粗製濫造都可以拿獎嗎?不少評論為當年入圍最多的《踏血尋梅》抱不平,回過頭對《十年》的獲獎大表不滿。
那是 2016 年。而後來發生了什麼,大家都知道了。
10 年
今年就是那一年——《十年》想像的那一年。
十年過去,香港這座抗議之城從雨傘運動後的低潮,到 2019 年迎來席捲全港、規模前所未見的反修例運動,之後又因為疫情與驟然落地的香港《國安法》而被噤聲。而《十年》的預告片,經過這段跌宕後也有了變化。預告內容絕大部份與 2015 年的版本完全相同,除了一句話:當年的「五個香港故事,一個不想見到的將來」,在 2025 年的重映版本則是,「五個香港故事,一個已然成真的未來」。
今年 10 月台北的《十年》放映座談,有觀眾向影人致歉,「那時我只覺得《十年》是個荒誕的科幻電影,現在覺得它寫實得像《鏗鏘集》[註]一樣。十年過去給這套電影帶來的力量和意義,我想起自己以前質疑《十年》憑什麼拿最佳電影,只是因為它的政治隱喻嗎?現在我的想法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這部在當年希望力挽狂瀾的電影,大概沒有參與的導演會想在今日被人們評價,你拍得最準確。
.jpg)
郭臻〈浮瓜〉劇照。

周冠威〈自焚者〉劇照。
那樣的準確預言是:〈浮瓜〉將背景設定在 2020 年五一勞動節活動上的一場槍擊案,背後正是為操控輿論、加速國安惡法推動所籌劃,映照現實中的香港《國安法》,也是在同一年正式生效。〈自焚者〉裡,街道上瀰漫的煙霧與被壓制在地的抗爭者,則讓人有種在看 2019 年抗爭紀錄片的錯覺——彼時想像得見或甚至難以想像的,都一一成為現實。
就連電影結尾看到演職人員名單一頁一頁捲動,也會讓人突然感到恍惚:已經有好幾年,曾經努力挑戰體制的香港電影人在這裡幾乎都不見人名,而是一連串的代號、化名、「愛電影的香港人」、沒有姓氏的英文名字、匿名、匿名、匿名。直至結尾。
「你神經病啊?我們說的生命,是你的生命啊!」
「那我呢?我是消亡中的,還是活生生的?」
《十年》在 2015 年上映當時,許多人對黃飛鵬〈冬蟬〉的章節感到困惑。片中一對男女將被拆毀的房子裡的各種物件一一做成標本封存,直到有一天男主角提出要求,請對方將自己這副肉身,也做成標本。
「我以前覺得這片是整部《十年》當中最差的。」〈自焚者〉的導演周冠威承認,自己當年只覺得那片的對白詩意,但現在才發覺那份詩意,是恐怖。「〈冬蟬〉的角色好 professional、很講原則,對過去充滿感情,但好絕望,最後將自己冰封,變成標本。這就是現在 2025 年好多香港人在香港做的事。現在的香港,好靜。」
靜,是無法動彈。每天能上街買、流傳在市民熱話間的香港《蘋果日報》沒有了,人們將 2021 年 6 月 24 日的最後一期頭版《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裱框收藏,像是標本一樣,試圖記得曾經還有這樣一個香港。販售過《十年》DVD 的書店和影碟舖,如今不能賣《十年》之外,好多書和 DVD 也得收起來,否則就是這間店要收起來。

黃飛鵬〈冬蟬〉劇照。
紅線不語
當整座城市都被迫安靜下來,當年參與《十年》的 5 位導演,卻依然嘗試在有限的空間裡挪動手腳,艱難地前進。
〈浮瓜〉的郭臻以《夜更》在第 57 屆金馬獎拿下最佳劇情短片,〈方言〉的歐文傑共同執導的《樹大招風》,則在 2017 年斬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當年作為《十年》監製之一的伍嘉良,近年來與執導過《少年》和《窄路微塵》的林森在英國籌辦香港電影節,而〈自焚者〉的周冠威,除了以《幻愛》接連在香港和台灣獲獎之外,2021 年的紀錄片《時代革命》更是如今討論反修例運動不能不提的重要作品——
然而再靈活的動能,也抵擋不了香港漸趨抽象的電影審查,與令人摸不著頭緒的紅線。
2021 年,因應香港《國安法》生效,被認定「不利於國家安全」的電影,有些被列為 18 歲以下不得觀賞的「第三級電影」,如《理大圍城》,有些被要求修改情節,否則難以獲得公映許可,如多部原先預計在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短片競賽之一「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放映的短片。
直接關於反修例運動的電影,不能放。角色名字太像那場運動裡被公眾認為死因有可疑的學生,不能放。英文字幕有幾個煽動言詞,不能放。更多的不能放,連理由都無從想像。
這些無法與香港觀眾見面的香港電影裡,有些因為拒絕修改而不獲准映,有些放棄或拒絕將作品送去做檢查,也有些導演,儘管配合要求刪去畫面,卻以持續數分鐘的黑畫面取而代之,彷彿在說——如果你知道這裡少了什麼,你記得。

歐文傑〈方言〉劇照。
不只香港電影,其他地方的電影也沒能倖免。中國導演李睿珺關注西北農村生活的《隱入塵煙》,先是在中國上映至票房破億後突然被撤檔、串流全面下架,原定在香港科技大學進行的放映,隨即因為電檢未獲批出准映證而取消放映。2021 年至今,也已經有至少 7 部台灣電影,因為電檢而取消在港放映。包含同志紀錄片《同愛一家》、關注移工權益的《逃跑的人》、以白色恐怖想像威權未來的《赤島》,也有黃信堯導演早期的短片《唬爛三小》。而最近一部,則是潘客印導演的新作《我家的事》,取消原因不明,只能揣想。
而儘管香港目前尚未引入如中國須在開拍前事前審查劇本的制度,但那並不代表那方地界仍然自由。周冠威今年的新作《自殺通告》,場景設定在一所架空的菁英私立中學,然而前期勘景時,全香港沒有一所學校願意出借場地,最後只能轉往台灣拍攝。
按香港電檢規範,電影拍攝完畢後還需送檢,14 日內必須做成結果,若涉及國安可再多 28 天——然而《自殺通告》從 8 月 4 日送檢後至今已兩個多月,仍無法確定是否能在香港上映。
「也好,或許證明這套電影根本不涉國家安全,所以找了兩個月,都找不到任何禁映的理由?」在一則社群貼文上,周冠威這麼說。
《十年》10 年,當年的想像從細如幻聽的遠雷,成了今日此城不止的暴雨,落在當年參與其中的人身上,落在電影院裡,也落在街頭。
其實那年金像獎頒獎典禮,頒出最佳電影之前,爾冬陞還說了另一個故事:「典禮前六個月,我們就已經開始寫今晚節目的第一稿,三個月前就開始找嘉賓⋯⋯這個創作班底裡有個年輕編劇,偷偷問過我:主席啊,我們今年的稿,能放『十年』這兩個字嗎?」
「我跟他說,年輕人,羅斯福總統曾說過一句話:我們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註|《鏗鏘集》為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老牌新聞紀錄片節目,1978 年開播以來每週一集,關注香港政治、社會、經濟、民生議題,亦有中國與國際政治題材。2020 年因製播反修例運動期間元朗 721 事件週年追蹤節目《721 誰主真相》,導致編導蔡玉玲遭警方拘捕,事件震動新聞界。2021 年起要求新集數須經審查方能製播,並且僅能涉及民生議題,不得製作涉及政治敏感事件的選題,此外,過往舊集數有大量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