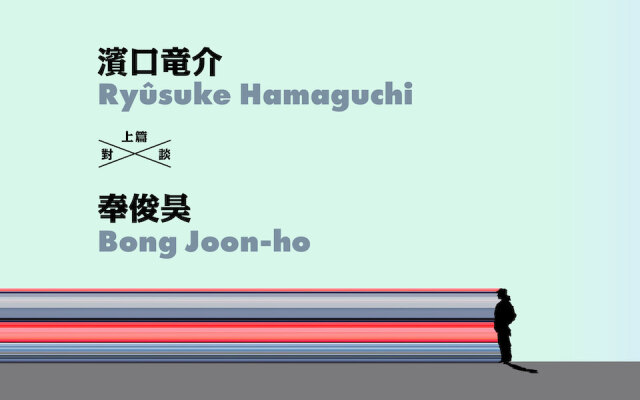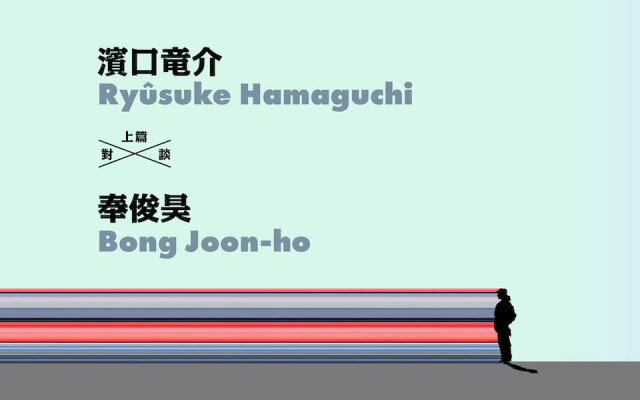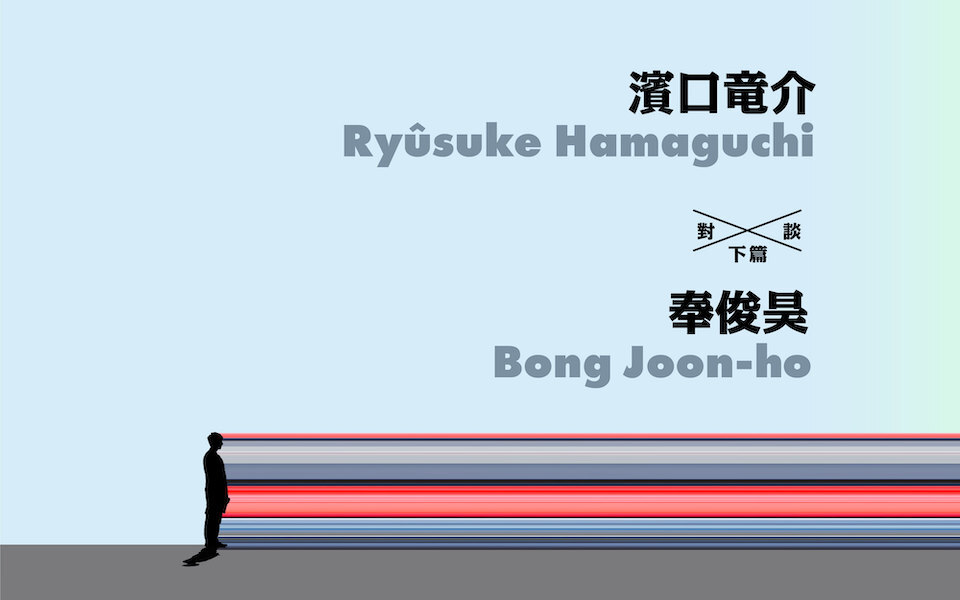
【奉俊昊 ╳ 濱口竜介】下篇:不是擅長當導演,而是理解了時間
續上篇,當代最受矚目的兩位亞洲導演:奉俊昊與濱口竜介對談,從電影實務、設定來到身為導演的焦慮與不安。2021 年釜山電影節講座中,奉俊昊接待濱口,以充滿細節的審視眼光與電影愛來發問,來回之間,對觀眾來說也像有趣的創作解碼。
BIOS monthly 與東昊影業合作,將此對談內容分為上下兩篇刊出,為求閱讀流暢,文字有所順調整並微幅編修,並非逐字翻譯。
奉俊昊(以下簡稱「奉」):《偶然與想像》第二篇的教授小說家,真的長得很像生病的申河均(觀眾笑)!那位是日本的資深演員是吧?
濱口竜介(以下簡稱「濱口):是的,那是資深演員澀川清彥,他通常接演幫派角色。我已經認識他十四、十五年了,我就是單純喜歡他這個人。這次我請他演出一個和過去差異很大的角色。我一直覺得他的眼睛很漂亮,我希望可以在電影裡捕捉到那種美。
奉:是的,我也這樣覺得。他好像戴著面具,有種不信任他人的感覺,有點像壞人,但當你近看,會發現他的眼睛裡有光,看起來深邃又脆弱,彷彿過去有什麼創傷,因而成為敏感、易傷的人,很複雜呢。《偶然與想像》第二篇有強大的張力,由你導演、澀川演出的那些動作,像是開門、關門,撼動了整間辦公室。兩位演員能維持那樣的張力很厲害,你把細節都拍出來了。
其中讓人最難忘的一段,是女主角揭露她從一開始就在錄音,教授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我演不出來(笑),但他起身的動作有種節奏、韻律,演員運用他的身體,抵達了藝術。這讓我驚訝,也讓女主角進入驚嚇的狀態,一切都很自然。可否談談這一場戲?你是透過排演找到這個表演的嗎?還是是在許多 take 中選擇的?

圖《偶然與想像》第二段〈敞開的大門〉,左為兩位導演在討論的演員澀川清彥。
濱口:那個二十分鐘的片段拍了大概三天,我記得我們不斷不斷地拍攝同樣片段,但前兩天拍出來的東西感覺有點僵硬。到了第三天,我才感覺兩位演員碰觸到那個場景情感的核心。有關導戲,我只導大方向,不涉及細節,是兩位演員理解了自己角色的狀態。
當演員們在對的角色狀態中演出,導演並不需要多說什麼。奉俊昊導演提到演員突然跳起來的動作,那並不是來自「我的導演」,而是演員本身。當女主角看到對方的演出,她也泛淚了,代表這是她在當下所感覺到的。
看著他們,我也感到十分驚訝。這樣的場景,需要耐心才能抵達,有時看著自己拍下的畫面,我都對自己感到驚訝。我所做的,就是把這些場景縫合在一起。
奉:聽起來真是太棒了。為了要觸及那樣的場景,導演必須要等待。但日本的製作公司通常都把拍攝控制得很緊湊,期程也比韓國短,速度和壓力都更大。即使如此,濱口導演還是完成了如此真實的表演,我想是因為他擁有自己的獨門秘訣。
我很好奇,從《在車上》《偶然與想像》甚至到《睡著也好醒來也罷》、《歡樂時光》,最難達到你心中想像的畫面,是哪個時刻?那種等了又等,等到演員都累了卻還沒拍到,可能隔天因為拍攝行程又要前往大阪之類的,一定有這樣的例子吧?
濱口:《歡樂時光》的製作期兩年,實際拍攝時間大約八個月。那時我沒什麼錢,但我覺得電影資金還算是充裕,想要重拍是沒問題的,我並沒有感覺到你說的那種壓力。在那之後的《睡著》是我第一部商業片,我是在那時候才感覺到拍攝期程的緊迫,但幸好兩位演員唐田英里佳和東出昌大,都給出我想要的表演。
拍攝結束後來看,我對結果很滿意,但我想這大概是出於運氣。我也察覺,當初如果我運氣不好,我就會處在一個很難把事情做對的狀態,甚至可說是,如果不是我運氣好,就無法讓一切運轉。那次拍攝全然取決於運氣,並非取決於我的能力。
在那之後,《偶然與想像》則像是回到獨立電影的路上,走回之前的拍攝模式,花足夠多的時間。如果少了時間,會讓我覺得好像回到商業片的拍攝狀態,而那對我而言並無法保證一部好電影的誕生。
《歡樂時光》至今,我覺得我已經能拍到我想要的東西,但那並不代表我有多擅長當導演,而是我理解了時間之必要,並在拍攝前確認我會有足夠多的時間。我需要時間,如果屏除了這個因素,那就無法擔保影片的品質。寬裕時間所形塑的拍攝環境或說心法,成為我拍攝的核心。
奉:你說無法想像不幸運時拍攝會變成怎樣,但其實幸運是你創造的,運氣也取決於導演為拍攝所做的準備。拍攝時間不會是唯一的因素,準備時間也得算在內;排演、拍攝前的規劃、與演員溝通⋯⋯我感覺你花了很多力氣在這部份。
《在車上》拍攝了《凡尼亞舅舅》這部戲的準備過程,像你在電影裡表達的,一開始角色不帶情感的讀劇,每個步驟都被美麗地拍了下來。在公園的那場戲,戲劇時刻終於到來。你準備拍攝的方式,或許和角色們準備《凡尼亞舅舅》有共通之處?
我想說得更具體一些,《在車上》厲害的韓國演員今天也到了現場,角色們一起用餐的那場戲裡,那個張力消失的瞬間,女司機被問到說食物好吃嗎?那是角色們第一次敞開心胸,氣氛很好。這些韓國演員你是如何選角、如何和他們合作的?過程和《凡尼亞舅舅》的準備過程有重疊的地方嗎?
濱口:你說的那場戲也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場,那是整部電影裡唯一讓人感覺溫暖,舒適的場景。至於準備過程,韓國演員對我來說和日本演員沒什麼不同,除了要透過翻譯溝通之外。你在電影裡看到的,就是我準備電影的方式;一遍又一遍閱讀劇本,手語的部份也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排練來讓演員們習慣。
說起來有點羞恥,我和奉俊昊導演一樣也有種矛盾的慾望,有時候會希望屏除一切多餘的東西,有時候又希望如實捕捉鮮活的感受,兩種衝突感在我身上共存。我不是演員,不知道實際演戲過程中,發生在他們內在的是什麼,但大量的讀劇讓我得以推測他們會有怎樣的行動,也能讓演員更自然反應出他們下一個動作。
一起讀劇後,實際拍攝前我會和演員們說,請他們根據當下所感受到的演出,感覺到什麼,就自在地演出來。當他們開始說起台詞,其他演員給予回應,有時演員們會給出連他們自己都驚訝的演出。然後了解,「啊,這句台詞原來是這個意思」,或「啊,原來對方會給出這樣的反應是很自然的」。
像我剛才說的,我通常會在不同角度重複拍攝,這對演員來說也有滿大的壓力。但西島秀俊先生在看到朴有琳(Park Yurim)的手語表演時和我說,不管看幾次,都感覺能和她的手語表演共振。演員所傳達的都可以被感知到,我想這也是餐桌那場戲會讓人如此愉快的原因。
奉:手語那段,我相信懂手語的人是可以理解意涵的,但像我這種不會手語的觀眾,會傾向看著比手語的人的眼睛。朴有琳的眼神非常細緻,很有吸引力。
《凡》的台詞大量出現在電影裡,角色們排練、表演這齣戲。但還有另外一齣戲中戲,是太太家福音從一開始就講述的故事,故事有點讓人毛骨悚然,但有趣到幾乎可以自己獨立拍成一部電影。把兩個故事放進電影裡不會很困難嗎?你曾擔心過他們會彼此干擾嗎?這兩個故事之中,有你比較希望觀眾關注的嗎?你想用這兩個故事帶來怎樣的感受?很好奇你在寫劇本時的想法。
濱口:像你說的,放入兩個故事並不容易,我希望能讓他們共鳴,為此做了不少安排,這也是電影最終長達三小時的原因。
村上春樹的原始作品對此有直接的影響,我不確定韓文書名,但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裡,也有兩個接連的故事彼此影響,共振。其中一個故事的世界觀,幾乎可以為另一個故事說明。如果有兩個故事存在,我希望一個故事能夠讓另一個故事成立。
《在車上》裡,真實世界是主線,劇中劇則是次要的劇情線,但在拍攝過程中,劇中劇的故事可能會越來越巨大,甚至超越主線,兩者界線變得混淆。最終,劇中劇即便是虛構,也感覺很真實。我想創造那樣的感覺。
奉:小小的劇透警告,電影裡,角色們在多年後再次回到一開始說的那個故事,聽了「結局」,當然我們不知道年輕演員說的結局是不是真的,但總之結局揭露時車子正在穿越隧道,穿越夜間的城市⋯⋯那幕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我閱讀過原著小說,故事非常短,特別是有女司機的那篇〈Drive My Car〉非常簡潔。在我看來,《在車上》更像是你的原創作品,不只是片長的緣故。這部電影可以拿下坎城最佳劇本,是實至名歸的。
順帶一提,演員宋康昊前幾天還傳訊息給我,想請我在見到你時打聲招呼。宋康昊是《在車上》拿下坎城的那屆評審之一,他很喜歡這部電影,想在閉幕時和你打招呼,結果因為疫情管制錯過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說這些!
有件很小的事,原作中的車子是黃色的,為什麼電影改用紅車?你對紅色有什麼迷戀嗎?
濱口:哈哈哈哈,或許吧。看過電影的人應該知道,拍攝移動中的車子時,會一面看到日本的地景。拍之前我在想,如果在山林這種綠色背景裡拍攝黃色的車子,顏色上的對比不夠吸引我,我就想說,如果不是黃色,那要選哪個顏色呢?懷抱著這樣的疑問,想說去看看車子。結果負責車輛的人開著紅色車子過來接我,我就把這件事視為一個徵兆,選了紅車。
奉:你試鏡了工作人員的車子?
濱口:對⋯⋯我遠遠看著那輛漂亮的車開來,想說,這是什麼?原來是工作人員的車。我立刻想說,這輛車可以,就立刻和製作人及工作人員講定了。
奉:那個工作人員在這部電影中留下了很大的印記呢(笑)。其實《寄生上流》也是,在富人客廳發生混戰時使用的義大利民謠,不是來自劇本,是道具組本來就在房子裡準備了唱盤機和三十幾張黑膠,我就想說,為何不從裡面挑一張?於是從一張義大利鄉村民謠選集裡,挑了首很像以前我父親聽的歌。
在義大利上映時,聽說觀眾們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可能有點像是在首爾看一部義大利電影,片中然出現了南振或羅勛兒的歌曲(笑)。那位義大利歌手很有名,我後來在威尼斯有見到他。但即使如此,這也是從道具組挑選的物品中延伸而來,製作電影真的是一個共同創作的過程,會留下你意想不到的印記,也讓合作變得有趣的經驗,那輛紅色車子也是一樣吧。
電影就叫做《在車上》,車子也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電影的性格。女司機開著車,和車子合為一體,滿足男主角對於駕駛的困難需求⋯⋯回頭想,我不記得你有用場景來建立「她很會開車」這件事?像是超有技巧地躲避從對向飛奔而來的大卡車,或單手停進超窄停車位之類的。但在她出場十分鐘後,我們全都相信了她,她的表情、肢體等等都很有說服力。你是如何做到的?
濱口:這個嘛⋯⋯我看到三浦透子的臉時,就覺得她應該是個很會開車的人。
.jpeg)
《在車上》劇照。
奉:所以實際上她本來就是駕駛老手囉?
濱口:我第一次見到三浦透子是在拍攝《偶然與想像》時,當我們開始製作時,她並沒有駕照,我只好請她去上駕駛課,取得駕照。現在她開得很好,也很常開車。但對我來說,拍攝她的臉部表情時,我很確定觀眾也會相信她是個好駕駛。
奉:確實是,她看起來很像可以單手開車環日本一周的樣子(笑)
觀眾提問
觀眾一:看了所有濱口導演的電影,在您的短片《海浪之音》裡看到神戶,《睡著》的背景在東北海嘯發生的地方,《在車上》則有廣島、北海道發生了土石流⋯⋯您的電影裡經常會出現災難性的空間,你希望這個空間在電影中起到什麼作用?
濱口:你聽到可能會不相信,《海浪之音》在東日本大地震發生的地方拍攝,那是我從一開始就有意選定的場所,除此之外,後面幾個場景都是偶然的。
《歡樂時光》會在神戶拍攝,是因為拍攝的合作方在神戶。曾經有考慮過另一個靠近京都的地方,但後來因為合作方就選定了神戶。《在車上》在廣島拍攝也是偶然,其實我本來打算在釜山拍攝,把釜山電影中心(Busan Cinema Center)設定為戲劇中心,以發生在此的戲劇節來展開這部電影,這是原本電影設定的開場。後來這個構想因為 Covid-19 變得不可行,我們就改在廣島拍攝。
奉:觀眾特別詢問到災難這點,有看過《睡著》的觀眾應該都會對那個畫面印象深刻:去看戲,看到一半卻突然地震,人們排隊摸黑而出,周遭傳來收音機和直升機的聲音,昏暗的燈光下大家在城市裡聚集⋯⋯有點悲傷,恐怖,災難如此突然地降臨我們的日常生活。這部電影的想法應該和災難有關吧?地震、海嘯等等似乎是這個故事的核心。
濱口:我聽起來很像在找藉口,但很抱歉,想到這樣做的人是這部電影的共同編劇田中幸子。兩人重逢時,發生了地震——田中有了這樣的構想,我覺得沒有比這更好的想法了。對我個人而言,我覺得我是被引導來拍攝這部電影,在拍攝這部電影之前,我有了「日常生活就已是災難」的想法,我想跟隨我的直覺把它拍下來。
觀眾二:濱口竜介導演剛剛說,自己的弱點就是一邊對話一邊寫劇本,但在觀眾眼裡看來,會覺得那是您獨特的優點。那麼,奉俊昊導演認為自己在導演上的弱點是什麼呢?是否曾經有某個不經意的失誤,後來得到很好的回饋呢?
奉:我基本上是非常焦慮的人,製作電影的每一步都在表現我的焦慮⋯⋯看看濱口導演,如果說我是焦慮之導演,那麼濱口導演就是穩定之導演。他做電影的方式、拍出來的電影,連同他的信念和哲學都安穩如磐石。
但我在每時每刻都很緊張,這種「我要逃去哪裡」或「怎麼逃跑」的念頭一直冒出來,我總是在尋找出口。觀眾會把導演手法解讀為好的,有趣的,或奇怪、獨特、很有創意,我很感激大家豐沛的詮釋。從我的觀點,既然我的表達來自我的焦慮,這件事本身就是我的弱點。即使我有想要做到或達到的效果,我也不會停止懷疑自己。我會自問,這個故事對大家來說是必要的嗎?即使我如此急迫地想說這個故事,人們會不會還是不感興趣?
我心中充滿了類似的焦慮,這是我的弱點,但既然我並不真的相信自己,這也可能成為我的強項。
我想每個導演都一樣,會感覺到電影離手的時刻。我指的不是完成後在電影院上映,而是當我把自己投入在電影裡到一個階段,我感覺到自己僅僅是這部電影的一部份,電影已經大於我,我只是佔有了導演這個虛名,來完成它。遇到這樣的時刻,我只能接受,我必須跟隨。直到那個電影離開我的時刻,我的焦慮才會減輕一些。濱口導演呢?
濱口:(大笑)我要先謝謝這位觀眾的問題,這也是我很想問奉俊昊導演的。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和奉俊昊導演一樣焦慮,對所有事情都緊張得要死。
我試著把自己穩定下來,為此做了很多事;無論是預留很多時間,或和演員不斷排演,都是減輕我焦慮的方式。這樣看來,我也是個焦慮大集合。
奉:說謊吧你!
濱口:是真的(笑)。
我感覺我們大概沒時間了,最後就講些想講的。在這個講座裡我們看似輕鬆隨意地交流,但我有種感覺,很像在被奉俊昊導演導戲。基本上您給予我認同,說我還可以做得更好。我感覺您從我身上提取了一些東西,在您的指導下,我甚至會覺得自己好像可以表演得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