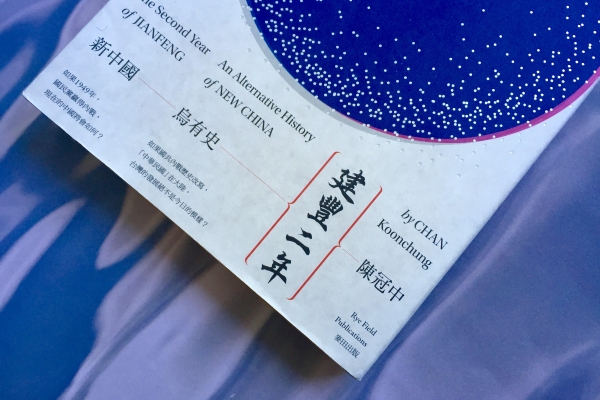《怪胎之愛》:我愛你的醜惡與美麗
她是天生禿頭、駝背、侏儒、白化症女子,最平凡的小孩,在她的兄弟姐妹之中。她有一個四肢長鰭的哥哥在水箱裡表演各種特技、連體嬰雙胞胎姊姊演奏四手聯彈,只有她無法吸引馬戲團的觀眾,於是負責各種跑腿雜役。偏偏有一個會念力的弟弟做事比自己更聽話、更有效率,笨拙無用的她,奧麗琵雅,因此得以旁觀家族的興衰,說出了《怪胎之愛》的故事。
「讓孩子光是做自己就能討生活,還有什麼比這更棒的禮物?」
經營馬戲團的夫妻在受孕過程裡執行種種化學實驗,誕下各式畸形的兒女,成為舞台上最受歡迎的班底。對於嬰孩,他們有驕傲與慈愛,同時卻也獨斷決定了這些骨肉的表演宿命。孩子的怪是父母的禮物,最終成為武器與負擔:四個怪胎為了保護、鞏固自己的地位,被迫盡情展現天性,為做自己而做自己。家庭的快樂祥和只短暫地出現在小說的前十頁,緊接而至的,是四百多頁的愛憎妒忌、爭權奪利、弱肉強食。懷抱著馬戲夢的父母,在世故於生存規則的小孩面前,顯得天真愚蠢。因此,當奧麗琵雅以童真的語氣輕輕帶過哥哥用枕頭悶死妹妹的情節,我們早就已先預見了後續奪權的腥風血雨。
「『假如爸爸發現火。』亞圖洛隨自己舉重的節奏嘆氣,『他會以為火是用來塞進嘴裡娛樂觀眾的⋯⋯假如爸爸發明輪子⋯⋯他會平放⋯⋯在上面放旋轉木馬⋯⋯以為頂多就這麼用⋯⋯假如他發現美洲⋯⋯他會回家忘了這件事⋯⋯因為那裡沒有熱狗攤。』」
家人之間卻又是互相在乎、高度凝聚的。他們自豪且認同這個家,拒斥任何人剝奪壓抑手足的怪。也正因為如此,家與馬戲團成為唯一的去處。當他們渴望出逃,才發現自己根本無處可逃,只能留在家人身邊,互相愛惜、互相利用。那種對待親愛之人的殘酷與黑暗,令人聯想到張愛玲小說中,那些步入無光的所在的女性,反覆掙扎卻注定失敗。書名《怪胎之愛》,講的不只是怪胎之間的愛,更是怪胎式的愛。生理上的畸形之外,四個孩子漸漸長出畸形的情感,在繽紛的馬戲篷後,慢慢消耗吞噬彼此。
小說的前半部到後半部有強烈轉折。家庭權力的重心更移之外,更驚人的其實是大眾價值觀的扭轉:在故事前半開槍攻擊怪胎一家的犯人,在十年後加入馬戲團信徒的行列;過去對怪胎感到噁心的人,開始追求怪、渴望怪,狂熱改造自己的身體。人們一方面安於世俗價值,一方面為其所困,遂產生對怪的盲目嚮往。
然而,當所有人變得一樣怪,怪胎其實也淪為平庸。真實而諷刺的是,不論是後期的信徒,或者前期怪胎家族的核心成員,都不曾真正看見怪胎的獨特性,只是著重於「怪」的事實:如何怪不是重點,重點是怪不怪、多麽怪、能不能表演、賺不賺錢。沒有人在乎小兒子為何能使用念力,他的父母思索的是念力帶來的利益。最後我們發現,早在那對夫婦決定施行這項基因的實驗,就已經注定了未來的失敗與毀滅。
唯一看見差異的,是那個最平凡的怪胎,小說的敘事者奧麗琵雅。過早被排除在鬥爭之外,她得以看見了自己之外的他人,愛他們的怪、愛他們的醜惡與美麗。她成為家庭裡的保護者,不像他的手足,她不曾為了自己,傷害任何人,也從而倖免於任何傷害。
只有一次例外。那次,她是為了保護一個人。於是,看見傷害的同時,我們也終於在敘事者身上,看見溫柔與堅強,就像那顆柔軟、卻始終拱起的駝背。駝背原來是預言:她須得背負整個家族的重量走下去。她在最後證明,怪胎也是人,每個怪胎都是有用的。每個怪胎都有活著的意義——或者該說,每個人都有活著的意義。
|BIOS 評鑑|
創作鮮明 ✭✭✭✭
內容精實 ✭✭✭✭
發人省思 ✭✭✭
《怪胎之愛》

作者:凱薩琳・鄧恩
譯者:陳靜妍
出版者:南方家園
出版日期: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