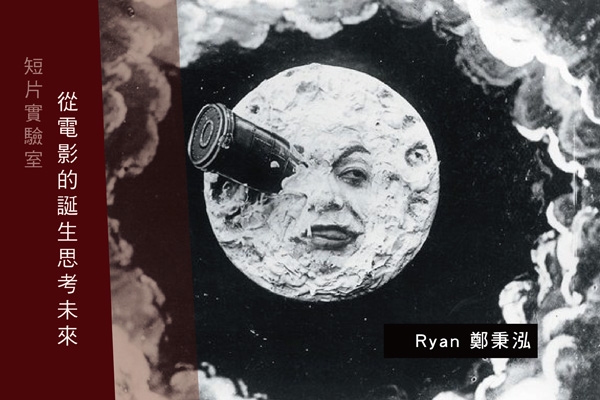短片實驗室|故事不是最關鍵:如何和全世界要資金拍電影?
面對台灣本地窄小的市場量體,影視製作的上中下游資源皆相當稀缺,除了搶食有限的補助獎勵之外,跨國交流合作是一條必須鑽研學習之路。
馬來西亞籍導演廖克發與義大利籍製片陳璽文(Stefano CENTINI),兩人在 2015 年台北電影節「國際提案一對一提案工作坊」後結為盟友,從紀錄片《不即不離》開始合作,接著發展同一議題延伸而出的劇情片《波羅蜜的愛》。發行商佳映娛樂的負責人劉嘉明(人稱 James),從耕耘國際銷售到創立專職製作的想映電影,愈趨積極參與國際合製計劃,而本次講座舉辦的幾日前,長片輔導金甫公佈獲選名單,三位主講人恰巧共列其中,趁此機會,他們將與學員分享自身企劃案的籌備過程,為新進影人帶來更寬闊的國際視野。
首先請兩位製片介紹手上正在進行的片子,經歷過哪些創投會和工作坊?
劉嘉明:《醬狗》是來自一位台灣出生、南非長大、回到台灣唸高中和台灣藝術大學、之後又跑到韓國念首爾中央大學、現在正在唸博士班的年輕導演張智瑋,他先做了一部短片,寫韓國華僑的處境;另外一個是前幾天見報、克發也有一起合作的《十年台灣》這個案子,其實就是五部短片的集合創作。
我今天來的路上在想能夠跟大家分享什麼,如果大家將來是拍片的人,有什麼可以影響、提醒你們?首先就是對財務要有責任感,我在台灣經常遇見要把力量都砸在一件事情上的做法,我真的並不鼓勵,因為要非常好的運氣才能賭贏,通常賭輸機率是比較高的。
短片是讓你入行,讓別人看見你的潛力,而不是證明你有市場影響力,因為短片無法跟市場做強烈的結合,重點是呈現講故事的能力,這點做到了,對的合作者應該就會出現,所以不必用長片的做法、把結構講得多完整。
回想我在美國碩士論文的短片有點可惜,沒把有限的資源運用在一件事情上、讓它有更大的突破,想周全的故事不是不可以,但可能不是對短片而言最好的做法。
陳璽文:《波羅蜜的愛》是克發第一部長片,我們在 2015 年北影辦的南特工作坊見面,討論得不錯,那時候他有一部紀錄片《不即不離》要先介紹長片的歷史背景,所以我們先從紀錄片開始合作。 James 剛剛提到要對財務有責任,我覺得也要對未來有責任,入這一行之後,你不只是拍一部長片,後面還有很多事要做,所以能夠抓一個好的 timing 是很重要的。我聽到克發故事的時候,覺得需要先用紀錄片的機會,去實現台灣在亞洲裡的定位——你是怎麼樣的導演、要呈現什麼樣的題材,從這裡開始延伸到劇情長片,《不即不離》發行之後,我們就開始發展《波羅蜜的愛》劇本。
左:廖克發,右:陳璽文(Stefano CENTINI)
有些案子不一定需要國外資金,反而會帶來很多麻煩,不一定適合。但是我們和法國製片都認為《波羅蜜的愛》很適合找國外資金,因為它很需要國外觀眾去理解這個歷史。我們已經在台灣參加南特工作坊,第二步就想去一個更國際的。我們訂了幾個目標,向一些對這部片很有幫助的地方申請,幸好入圍坎城的世界電影工廠新導演工作坊,這對後來申請輔導金非常有幫助,因為它提升了我們的曝光度。《不即不離》讓我們有一個位子,而劇情長片就是要帶到國際,坎城的工作坊之後拿輔導金,這個 timing 是需要抓的,非常重要。
James 之前一直從事發行工作,後來是什麼契機下進入製作?
劉嘉明:我念政大新聞系,是離電影最近的選擇,後來決定再去國外念,回到台灣時是台灣電影最沒聲音的時候,台灣新浪潮已經沒有浪潮了,所有新浪潮的人都去拍廣告,不拍電影,所有電影都是香港電影。很多時候不是我決定要怎麼做,而是我喜歡電影所以沒有離開,一直在找可能性,我拍了一部輔導金電影《三十而立》,拍完之後我自己買票走進華納威秀去看,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再花四年拍第二部了。那時候就覺得看見台灣的困境,台灣沒有真正的 producer,沒有人在帶領年輕導演,年輕導演非常需要有經驗的人,即便他再有想法,可是實務經驗不行,還要面對產業裡的牛鬼蛇神,根本沒辦法應付。後來我有一個機會,進了當時國內最大的發行公司春暉影業,它還有一個 Sun Movie 電影台,很早就開始把歐洲、美國獨立製片的電影帶到台灣,我做了電影台的節目總監大概七、八年,讓我對產業更認識,某種角度來講是我在準備我自己,我心裡知道終究要回到製作來。
有一段時間我寫了好幾個舞台劇劇本,其中得獎的叫《結婚?結昏!-辦桌》,我一直在創作,可是沒有在第一線做導演,後來又進入另一家跟有線電視更相關的公司,三年之後我就成立佳映娛樂,我很清楚知道我必須要具備發行能力跟經驗之後,才會進來做獨立製片,不然風險太大了,所謂的風險太大是完全不曉得怎麼樣跟市場接軌,即便今天也是這個狀態,很多導演做完了片,找一家公司幫你發行,可是中間很多東西你可能並不了解關鍵何在。
左起:劉嘉明(James)、廖克發、陳璽文。
2007 年底,我決定試試看去做國際銷售,那時候台灣電影趴在地上很久了,我認為台灣電影往外走是一個關鍵,尤其是獨立製片,因為台灣太小、資源不足,文化、地理上跟我們最親近的就是日本,我在一句日文都不懂的狀態下到東京去敲門,手上帶了八部片,《最遙遠的距離》、《練習曲》、《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沉睡的青春》等,選了三家日本發行公司,都是自己有戲院的,終於有一家被敲開,我跟那家公司一直保持非常好的關係。
另一方面,我看到 Stefano 跟克發常常在一些場合一起出現,我心裡是很羨慕的,一個創作人身邊有一個 producer 可以和你搭檔,這是非常棒的事情,大家可以各自專精努力,同時又能彼此吸收想法,這對獨立製片的電影太重要,因為我們處在資源不足的狀況之下。
多年來累積了製作、發行到國際銷售,突然好像被打通的感覺,我知道一件事情後面會是什麼狀況,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幫助,當這個準備好的時候,我在去年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想映電影,佳映是發行,想映處理製作,目前我們在推的案子,一個是剛剛講到的《醬狗》,另一個是劇本開發階段的《指定曲》,接下來會去找合適的創投。
提案心法:人比故事更重要
相較 James 有豐富的產業經驗,克發和璽文比較是獨力去接觸國際市場,最初如何開始?
廖克發:《不即不離》一開始沒有資助,就是自己拍,拍了兩三年,素材拍得差不多了,是因為需要後期的錢,我才開始跑創投,最早是去 Asian Side Of The Doc,它是 Sunny Side of the Doc 在亞洲的創投會,每年在亞洲不同國家舉行。我自己申請 pass、自己買機票去,當時完全不知道這樣的場子是幹嘛的,只知道可以找資金,就印了名片,準備了很多資料,然後才發現在那邊的投資人一天時間就是這麼多,可是有幾百幾千個案子在市場上流動,你要怎麼在五分鐘內讓他對你有印象?他一天可能要見二、三十個人,他只要能記得你,你就算是勝利了。
去那邊看到別人,才知道真正的 pitching(提案)是什麼,怎麼樣在三分鐘內讓人對你有印象。我的 pitching 技巧是後來在台北電影節的南特工作坊學的,我去了很多創投,每天都要重複 pitch,每次 pitch 都會讓你不斷練習,不只是說服別人,其實你也在慢慢說服自己這個故事有可能,當你開始講這個故事、要求自己要講得愈來愈精簡的時候,你會發現有些地方講不下去,那就代表你自己都不相信,然後你會不斷地改,改到你真的很相信你講的每一句話都會成真、每個細節都是有可能的,整個過程下來,你才會有足夠的耐心、毅力把這部片子完成。

《不即不離》劇照。
我可以分享一些比較具體的技巧,因為你面對的人只給你三到五分鐘,過去我是初學者,會急著要在五分鐘內把故事告訴對方,你都覺得自己的故事超棒,講出來他一定會記得,其實在市場裡競爭是很大的,講完整故事是錯誤的概念,並不需要整個故事塞給他,只需要在故事裡找到最具體、最重要的一場戲、最重要的主題,讓他留下印象,之後他會再聯繫你的,你還會有機會把整個故事說給他聽。
另一件事是,故事必須個人化,全世界那麼多好導演,為什麼一定要是你來拍?可以買你的故事找別人來拍嗎?這個故事跟你自己的生命、人生經驗的連結點在哪?你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讓對方覺得這故事非你不可,才有繼續下去的可能。
陳璽文:我們去創投的時候,發現大部分人其實不想聽你講故事,反而他想知道你是誰。剛剛說到要規劃這個行業的人生發展,希望可以不只拍一部而已,同樣來找你的人也不希望只跟你合作一部電影,可能會希望長期合作,所以他更在意你是什麼樣的人。南特工作坊訓練 pitch 時會做一個遊戲,讓大家說自己名字的故事,大家一開始都非常尷尬,可是當你被逼著要講,就會講到很多自己背景的故事,這就很吸引別人,因為跟你個人非常有關,而且是真正屬於你的東西,如果可以把同樣的東西擺在你的電影故事裡,對方就會想繼續聽。
劉嘉明:發行商到市場展攤位坐下來,傳統的 sales 就是直接 pitch,我通常都會說:「不需要講,因為我都可以看資料。」首先必須讓人產生對你的興趣,他才會要了解你,沒有人會完全準備好自己、等著你來告訴他一個偉大的故事。他可能昨天晚上沒睡好,可能會被太多可能性干擾。但我們這行若不能勾起人家的興趣,不如不要做,你一定要有策略,每個步驟都要安排過,看起來很自然但都是練出來的。
我非常建議肢體有困難、表達有問題的人,先把肢體打開,只有肌肉放鬆、能夠控制時,你才能清楚表達,如果能做到這樣,不只是面對你的投資者,面對演員和工作人員都是一樣,你要能讓他們死心塌地覺得:哇!我參加了一個很棒的案子!
克發和璽文怎麼尋找合作夥伴?身為監製的 James 在這些場合中如何選擇能合作的導演?
劉嘉明:很有趣的是,經過十幾年的發行和買片工作,我發現我經常買到導演第一部片。譬如 Miranda July 的《偶然與你相遇》,當年在坎城得了金攝影機獎,還有印度電影《美味情書》,那個創造力太令我感動了,用這麼少的資源,竟然可以把一個故事呈現得那麼棒。所以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新導演的第一部片,把我的經驗運用出來,在有限資源裡拍出來,如果你希望得到非常多資源,可能我就不是很好的合作對象。
資源永遠是相對的,要更多資源表示承擔的風險更大,要考慮的市場因素更多;市場上人家出給你一千塊,就代表他想回收三千,你必須要有這樣的準備。新導演的第一部,如果不要賠錢、能賺一點、在影展得到好回應,就已經走了好的第一步,這樣就夠了。像克發等幾位導演, 一旦開始被國際重視,在某一段時間內就會持續受到關注,《波羅蜜的愛》去了坎城的工作坊,那邊就會期待這部片做完,然後一定會把你列入清單管理,因為坎城也不希望他們的寶貝被人家拿走,大家彼此之間是有競爭關係的。

劉嘉明、廖克發、陳璽文。
陳璽文:我覺得我們這工作有趣的點,是不一定在工作坊或公開場合,而是在外面吃飯喝一杯、聊天中提出的想法,會讓你更認識一個人。《波羅蜜的愛》跟一位法國製片合作,其實我們早在南特工作坊就認識了,可是後來去了坎城、巴黎幾趟,有天在他家吃飯聊天,聊跟電影完全無關的事,這讓我知道他不只是對電影,還有對生命的看法是什麼。因為我要跟他合作好幾年,我必須知道他處理事情的態度是什麼,遇到困難他會有什麼反應?我要怎麼面對他?這些事情不會在公開場合知道,反而是在比較休閒的時候,要更注意這些表現。
廖克發:我常覺得拍電影對創作者來說,很容易變成很自私的事——創作者想到一個故事,想找資金,覺得不幫我的都是混蛋,拍出來後對片子的佔有慾又很強,有時候強到會阻礙你繼續走創作的路。
現在社會很強調導演,好像大家都應該順從你,理所當然應該幫你拍片,但我必須說,我學電影十年,最大的收穫是一開始沒資源時願意和我拍片的那些人,他們到現在還跟我一起,最好的朋友都在最苦難的時候找到,所以如果你現在是最低潮,你有一個優勢,就是你可能會交到這輩子最重要的搭擋。
拍一部作品,我常常不只是單純想我要表達的東西,我很多工作團隊是固定的,我會想如何在每一支片幫助、提升他們,覺得這個人可能快要長大了,就給他一個難度去考驗他,拍片的一群人能夠一起慢慢往上走,不只是對你本身,對片子也是很好的。我能夠常常在沒有劇本的狀態下拍,是因為團隊跟我非常有默契,而且是很強的信任感,現場我要改一個東西,攝影、美術不會問我為什麼,那個信任感是需要多年去鑽研栽培出來的,跟這群人拍片會覺得走得下去,覺得很幸福。
要先了解故事適合在什麼市場發揮,才有可能知道目標、找到適當的資方,除了從導演個人特質出發,三位會怎麼設定故事定位?
陳璽文:如果能抓到故事的核心,你就知道最低底線是什麼,跟別人討論故事會知道什麼可以改,但有些東西不願意放棄。
劉嘉明:把投案分兩類,一是創作者導向,二是市場導向的類型片,先做粗淺分類比較容易看這件事。我這些年在做優良劇本評審,看類型故事的劇本和看創作型的真的非常不一樣,市場也不一樣,克發的東西去歐洲非常有魅力,可是亞洲除了釜山之外就非常困難,因為市場氛圍就不是聚焦在這種作品。香港就是在提倡某種有中國元素的東西,這些年更明顯;東京太小,根本沒什麼好提的,日本電影 80% 都滿無聊的,他們也都知道,可是日本人一旦開工就沒辦法停,所以他們會花很大力氣拍一部爛片;釜山 APM(亞洲電影市場展)在亞洲的位置是最高的,歐洲 producer 如果只能選一個去,通常他們會去釜山。
廖克發在 2015 年釜山國際影展獲得超廣角亞洲最佳短片。
我學得最會就是被拒絕
學員提問:我們跟投資人提案時沒有組織企劃或完善說法,而是直接講故事,講完就被問資金和回收的問題,想知道他們對故事有沒有共鳴但又很難開口,對方不是這行的人,他們說對案子有興趣,但不是就創作來討論,而是想知道可能的收益,面對他們好像沒有辦法談下去。
劉嘉明:跨不出第一步就回去練,這東西不是教的,像籃球罰球,講半天沒用,就是要站在那開始罰球。你也回答了你問的,你可能沒有準備好,首先你必須對故事裡外前後都想過,不能只想自己那套,好的故事,最厲害的部分不在寫出來的文字上,美妙的東西都在行間隱藏著。比如你要怎麼勾引一個人,這些是可以規劃的,要用很專業的態度去面對,否則立刻會被識破,因為大家都是江湖老手。故事真的不是最關鍵的,而是人家怎麼去認識你,他跟你成為熟識的人,才會再去聽你的故事。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有個建議就是去學表演,對於節奏、身體如何掌握,如果你連聲音都會顫抖,很難讓別人把兩千萬交給你去執行。
廖克發:不同的人有不同語言,你要能夠說他的語言,其實故事是需要試驗的,在台灣我也幫人家編劇,很多時候就是去找錢、去拍,並不常把故事拿出來給不同的人看。好萊塢的做法是有試驗會議,給不同人看、提出不同的問題,不代表你要吸收全部的意見,只是你要知道不同的人看這件事時的問題在哪。
被拒絕也是需要訓練的,我覺得我跑了那麼多創投,學得最會的就是被拒絕,被拒絕了沒關係,做朋友就好,不是所有來開會的人要不成為幫助你的人,要不成為敵人,人不需要這樣分類,你也會有下部片,以後可能會拍不同的東西,他雖然不投你的片,但他的看法可能是好的。
Pitching 時不要一味推銷,也要學會看人反應。讓 pitching 愈來愈精進的其中一個辦法,是每次大概準備一套三分鐘的說法,然後去注意講到幾秒時對方會開始晃動、講到什麼點對方會注意聽,慢慢觀察久了,你就知道你的故事魅力在哪,我對故事的掌握是從這裡來的。
我第一次去 Asian Side Of The Doc 時,跟日本老前輩導演提《不即不離》這故事,當時我非常菜,提完之後,他搭著我的肩膀說:「年輕人我跟你說,我不只不會投,我勸你不要拍,拍這部片可能對你的創作生涯不是太好,對你的家人可能不好。」當下我非常驚訝,完全不知道怎麼回,我後來氣自己沒有能力馬上回應,如果你很確定,就應該回說:「我還是要拍。」有人批評你的劇本,你應該要開心,表示他有聽進去,只是某些地方他不喜歡;如果對方只說:「嗯,很好,再保持聯繫。」那就是他沒聽。《不即不離》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知道大家怎麼看待,才有最後的故事架構跟呈現方法。
陳璽文:非常鼓勵大家去想「資料是交給誰」,而不是用同樣一份發給大家,我每次去申請國際的工作坊和國際資金,每次都要改,故事大綱有時候要兩百字,有時候要五百字。每個對象想聽到的東西不一樣,你要抓到他想聽的。例如《不即不離》因為有政治因素,找資金會特別注意,比如我們申請的是鼓勵華語紀錄片的單位,就會特別寫不一樣的企劃書,我覺得這非常有幫助。
劉嘉明:去年開始,我的公司幫賈樟柯做「柯首映」短片平台,我覺得台灣創作者有一個特色,就是從來不想規格,製作的時候沒有把這東西擺在腦袋裡,譬如片長、拍攝條件,如果要做 producer,一定要將這件事掌握得非常清楚,否則你連門都進不去,「柯首映」在台灣找短片就發生這個問題,二十分鐘以內的非常少,幾乎都超過。如果短片要曝光,就要透過一些有效的影展,它的規格你要很清楚。
三位曾經在哪些工作坊和創投市場得到很好的經驗?哪些比較推薦給新鮮人參加?
陳璽文:我建議大家去 Ties That Bind(歐亞合製工作坊),我覺得它可以幫助亞洲創作者集合,又有很多歐洲的片商、製作人、影展工作者,他們會提出對故事的想法,同時你也可以跟其他亞洲電影工作者討論,因為亞洲面臨的困境是一樣的。這個工作坊同時在亞洲跟歐洲國家舉辦,是讓導演打開電影世界的方法。
廖克發:很難給具體的建議,因為每個人來自不同背景,有不同案子,其實不同創投都有不同傾向。
我必須說案子有它的壽命,也許是兩到三年,所以先後順序要有策略。除非你找到很有經驗的製片或監製幫你規劃,如果都沒資源、案子也沒有一定會拍成,你就隨便買機票隨便去了,就像我當初那樣先去撞,先學會怎麼被人拒絕。我是固執的人,去了就要有收穫,但收穫不一定是錢,就算被拒絕了,你也可以問那個人:「你為什麼拒絕我?」那不一定會實際幫助片子完成,但是會讓你對想拍的東西更確定、更堅持,對我來說這是更難找、更需要時間去維護的。
劉嘉明:每年 11 月底 12 月初,阿根廷有一個西班牙外最大的西語系國家影片聚集的地方,他們雇了坎城影展做執行單位,也分享坎城資料庫,知道要找什麼人參加,這幾年來成長得非常有效率,主要是以賣西語電影為主,但是多了創投市場。去年我認識一位阿根廷的 producer,見面後發現他們真的有備而來,希望找到環境不一樣的 producer 加入他們的案子,變成亞洲跟阿根廷的製片人合作,導演又得到古巴工作坊的協助去那邊寫劇本。
這個故事我用自己的概念來講:一個三十多歲、準備結婚的阿根廷女人,有一天和老闆要來台灣出差,但是飛機延誤,他們就住在機場旅館等隔天搭機,隔天班機按照行程起飛,但這個女人卻沒登機,為什麼?我的 pitching 就講到這裡。
決定要參與國際提案會的時候,是否在劇本上就已經想到國際化的問題?我們最近常講「在地就是國際」, 以各位的經驗而言,在地化是優勢還是障礙?
劉嘉明:像柏林影展有它自己的屬性,案子怎麼呈現就決定他要不要你。很多時候我們故事就是不乾淨、結構不清楚、有沒被解決的支線,在我過往經驗裡,我發現德國人不能容忍這種東西。如果一個導演已經進過柏林的競賽單元,他們可能閉著眼就接受了,有些片子真的滿爛的;可是如果你是新導演,清楚的敘事線就是關鍵,這些年我觀察的柏林有這樣的特色,包括選片。很多台灣電影可能 80% 都很好,突然不知道哪邊歪一下,跑去了一個地方,又沒辦法用邏輯說明清楚,譬如在很寫實的片突然出現幻想,德國人就無法理解為什麼。
陳璽文:進行國際合作有點像「你想把片子推到哪個影展」,很多人都想去坎城,但你的片子可能比較適合別的比較小的影展,效果會更好;故事適不適合也有關聯,那個國家的人是不是可以接受你的故事?還是要先從自己國家的觀眾出發?寫劇本的時候當然要先思考,如果你決定要往國際方向走,你對故事要思考得更清楚,寫劇本時有些東西必須交代,因為面對的觀眾不一樣,資訊的接收程度也不一樣。
廖克發:同一個故事,用華文、英文、法文來寫,看起來會是三個不同的劇本,各國的切入點跟習慣的表現方法其實滿不一樣,國際化的時候有一個跨語言、跨文化的問題。但從創投 pitching 到最後要拍,不代表劇本一定要是一樣的,你要有不同的思維,寫給文化沒那麼相近的人時,需要把所有東西都寫在裡面嗎?還是只要清楚簡單地出現就好?
我覺得不管怎樣,有趣最重要。我常碰到一些學生編劇、新導演,他們提故事的時候,很執迷於想透過這部片表達對社會的洞見、對國家的想法,老實說那對初次見面的人來講一點都不重要,你的故事本身必須要先有趣,一場戲要有趣,他才會站在你這邊。
當他們沒有靠近你時,講很多抽象的東西會離他們很遠、一點都不具體,你要一提就中、讓他馬上覺得想繼續聽下去,然後你就說:「我不說了,你想聽的話再跟我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不是一味地給,有時候要像挑逗,要知道在哪個點停下來會留下懸念。
【2017 SHORT LAB 短片實驗室】
由中華民國電影創作協會(簡稱電影創作聯盟,TOFU)主辦的短片實驗室,是針對欲從事影像創作的電影新鮮人所籌劃的影像教育機制。一年兩季,春季班以前期製片及劇本故事為主;秋季班以後期製作及粗剪為主。希望在一般學校體制之外、以及各種徵件/補助/競賽之前,提供另一種開放/學習/實作的互動平台。短片可以天馬行空、自由創作;可以實驗各種可能、形成同儕關係;這是實踐的「培養皿」,也是一種「做中學」的精神。
【孫志熙】
曾任《CUE 電影生活誌》、《SCOPE 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