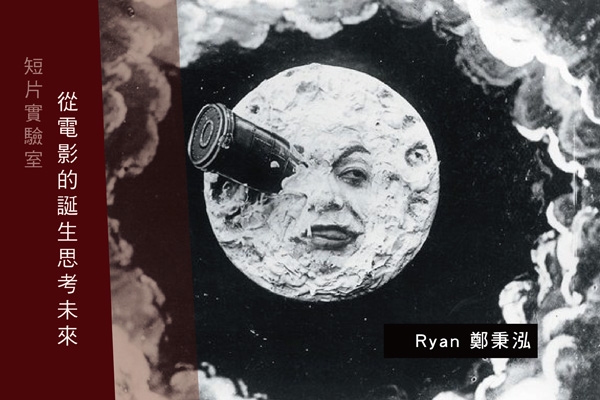短片實驗室|我的首作是金馬最佳短片——沈可尚、李芸嬋的業界心得
《與山》和《神奇洗衣機》分別是沈可尚和李芸嬋的第一部短片作品。1999 年完成的《與山》以十六釐米攝製,是大學畢業作品,也是台灣在坎城影展 CineFoundation 競賽單元的首次入圍,並獲金馬獎最佳短片,係為台灣獨立電影界傳說名作。沈可尚在座談裡自我揭露,該片從劇本到拍攝,實是一段漫長的流動與質變,左右腦不停交戰,還在開拍首日就把七成故事一夜推翻、打掉重練,一人待在半山腰的土地公廟裡一邊寫、一邊拍、一邊等霧來,如今回看,那是當時的自己試圖解答「到底什麼是電影」,亦是相對青澀、唯心的創作方法。
來自科學研究背景的李芸嬋,開始短片創作之前,其實已有八年電影業界資歷,擔任過製片與導演組的許多職位。一直希望有機會嘗試導演工作的她,從日常生活找材料,創造了一個愛看洗衣機轉動的女主角以及深夜洗衣店的奇幻故事,這部 2004 年的短片首作,同樣一舉獲得金馬獎。
沈可尚感性細膩,李芸嬋理性精準,兩位導演從作品風格到思考方式的大相逕庭,恰好提供了極佳的創作方法與觀點對照,讓這場座談充滿靈感火花。
.jpg)
沈可尚(左)與李芸嬋(右)。
《與山》敘述一女性影像工作者試圖追蹤一群亟欲逃離現世的信徒,但無論怎麼尋找,這群信徒卻如同消失了一般。在車子油盡之時,她遭遇男子挾持。片中有些符號,像是女主角看的麥田圈,或是最後的隊伍令人想到「玉山小飛俠」,你在創作時是否引用了一些台灣鄉野奇譚?
沈可尚(下略稱沈):你看服裝做得多差,居然讓人覺得是黃色雨衣(笑)。那時的大學畢業製作跟現在不太一樣,現在你可能知道需要好的服裝可以找誰合作,台灣 1999 年時拍片的人力其實不多。那個「雨衣」是組內人員連夜趕製的,它其實是道袍,所以完全沒有任何鄉野傳奇的成分。
故事設定中,這些信徒信奉的是一種非宗教的信仰,一種遁世的、不願意遺失的心態。女演員持攝影機要去探究神祕事物,我覺得像是一種「說理」,就像我們很習慣要把世界上很多東西講得很明白;不管是透過文字、攝影,她想要透過這個方式來解剖這個世界,這是很多文化的來源,但我某種程度不是很信服。
兩位發展劇本時,有創作或寫作的節奏嗎?編寫出來的結構到了拍片現場又會怎麼變化?
李芸嬋(下略稱李):我沒有受過編劇訓練,那時大概的構想是「要有一個開頭跟結尾」。之前跟其他導演合作拍攝的,多是沒有故事性的片子,所以期許自己未來當導演可以拍讓大家看得懂的片,當時以為《神奇洗衣機》是這樣的。也因為這部片,很快有了下一個案子《人魚朵朵》,它的故事也很簡單,但自己還是傻傻的,覺得有開頭跟結尾就是完整的故事、大家就會看得懂。

《神奇洗衣機》劇照
我直到第二部長片《基因決定我愛你》才有比較完整的學習。這部片有中國投資,主事者是一位從美國回來的製片,她看完劇本後覺得高概念的故事很有趣,但結構完全不行,於是她拿了一本勞勃麥基(Robert McKee)的《Story》(台譯《故事的解剖》,於 2014 年出版)英文版給我看,我把當時寫的四個劇本包括《極限燙衣板》,都拿來對照書中教的結構跟內容,我的問題就一一浮現了。
如果想拍商業片,而不再是玄虛的東西,有一些基本要素就要被照顧。用結構來說明我的問題,就是「前提永遠是最有想像力的,所以一部長片前五十分鐘都在發展前提,之後才開展,然後收尾很薄弱。」當然不是所有電影都有結構性,它可以有自己想講的事情。我近期開始看很多劇本,如果它是要講一個有起承轉合的三幕劇,我就會去看結構的分佈跟開展的部分有沒有處理好;但沒有自己去寫、去經歷過,就會聽不懂、以為自己都是對的,真的寫下去再回頭檢視,才能夠有所成長。所以,先寫吧!
沈:我大學是學電影的,也有修劇本課程,老師教的也是比較接近三幕劇的思考方式。大概從《與山》之後有一個習慣:寫出結構、分場、對白,跟著老師指導的方式把故事說得清楚。但我覺得我就是沒辦法把故事講清楚,因為我可能不是這麼相信故事,我比較相信「感知能力」。我進電影院不一定是要去看一個故事,我會想要感覺一個思考、一個氣氛、一個神祕事物、一種意圖。
我有想過可能我不適合拍電影,可能比較適合拍 video art。我會覺得也許不要說這麼清楚,保留一點空間給看的人,對我來說反而比較自在。
後來我拍了很多紀錄片,即使拍紀錄片我都還是會發現一種「被決定的空白」,對我來說是很幸福的。
很有趣的是我的劇情片,在開拍前都會有嚴謹的劇本跟結構,但是在拍攝現場及剪輯時都會出現質變,最後就會變成和劇本長得不一樣的東西。嚴格來講我並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會寫劇本的人,我可能會從劇本裡面提煉出與自己的關聯性,我的責任就是把這個關聯性呈現給觀眾。除此之外,我倒是不介意觀眾怎麼看我的影像。我會去拍紀錄片,也是因為展現出來的生活本質跟人的狀態,可能更接近我想講的。
李:那時候還在當劇組工作人員,利用空檔兩天就把劇本寫完送短片輔導金。後來的經驗是,我要在心裡先想好一個故事,一直找感覺,找到讓角色活起來、有影像以後再落筆寫。第一稿通常寫很快,大致的結構會出來,但痛苦會在後面,有很多邏輯、前後的調整,讓後面的修改變成漫漫長路。我跟沈可尚的方式不太一樣,拍攝時的有機調動只剩下演員。我是比較需要前製時間長、去醞釀的人;看景也需要看很細,常常會遇到看景時遇不到合適的,就要再修改劇本,也常常遇到預算有限、方向必須轉彎的情形,我會跟自己說,這些限制就是讓創意發揮的機會。我有完整的分鏡跟拍攝順序,現在拍很多廣告,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工作,可以幫助自己站得住腳、跟對方溝通。

電影學校出身的,作品大致會跟學長姊學弟妹一起完成;已經在業界工作的李芸嬋導演,狀況就不太一樣?
李:我那時候在劇組工作八年,已經做過十幾部電影的副導、場記,所以當我要拍片的時候,就把大家都凹來。攝影是秦鼎昌,也就是魏德聖後來所有片子的攝影師;美術指導是王逸飛,隔一年她做《人魚朵朵》在金馬獎拿最佳美術。有列在 credit list 的人,後來都有拿金馬獎或金鐘獎,他們當時都已經很獨當一面。短片時代比較少找知名演員演出,那時候因為我剛做完《求婚事務所》,所以就找了裡面的李康宜,多少都是從累積的資源裡頭去完成。
另外有件事情想講。我之前做過黃銘正導演拿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城市飛行》的副導,算是去幫忙,但他後來拿到的每個獎都會分錢給我們,就算是一兩萬塊他也會分二十份,讓人覺得他是個很有心、很善良的導演,所以《神奇洗衣機》就比照辦理。
在創作時會一直轉換自己的想法,但是常常回頭看作品,又會覺得太自溺,兩位有什麼看法?
沈:我後來把自己的特質跟弱項分得很清楚;我的弱項就是邏輯跟組織能力。有次看完片我跟夥伴聊,他會跟我說故事結構、角色建立等等,但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只說我珍惜從裡面看到的「共感」,整部片沒有故事,是用情節、人的交會去組合成一個活著的氣味,我一直對這樣的情感信任度比較高。就像我寫不出一篇好文章,我的結構能力是不夠的,但要我去拍攝,我可以直接從世界拿到東西,我相信透過手段從現實世界拿到東西,是一種重新創造,它會反映你的人格特質及關注的面向,可以說是一種跟世界的「直接交戰」。
我會把故事大綱交給信任的編劇,去結構成比較能閱讀的格式,但結構還是瑣碎的,因為想讓觀眾自己去體會、看看能帶走什麼。
我的亢奮感不是來自於完成,而是推翻。
我拍攝紀錄片時從來不打算去討論「真正的證據」,我一直都是在處理當下發生的情節,將瑣碎的情節拼湊為我認定的事實。跟我一起工作的拍攝團隊都有長久的默契,他們都知道我的 shot list 到後期會有很大調整,我的亢奮感不是來自於完成,而是推翻,所以工作人員有時候會很討厭我,尤其是製片組。我是個很不穩定的傢伙,但久了、習慣了,會變成一種滿有趣的有機。可能是我一直沒有受過片廠訓練,所以會比較自溺,但每個人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只要他的最終關懷能夠透過影像呈現出來就好。我記得之前拍《台北工廠》,烈姊跟如芬姊來看剪接,她們真的很生氣(群眾笑),她們說原本就有一個腳本,為什麼不能這樣剪出來?我就是會有一種反抗的打游擊心理,想要給你一個新的東西。
.jpg)
李:我以前也會想像自己是王家衛,可以一天剪、一天拍、一天想,一部電影可以拍三年,多美好!但我的個性就是,風暴只在前期產生,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是最大的風暴,等到自己穩定了,剩下就是跟外面打仗、說服別人。
照這樣的拍攝方式,拍攝比例(拍攝長度比放映片長)大概多少?
沈:「閱讀時光」的《世紀末的華麗》是 75%(拍攝長度)跟 25%(放映片長);以前用底片大概是 2 比 1,3 比 1 是緊繃了,因為太貴,十六釐米的拍攝,按下快門那剎那心臟都會抖。那時候還是因為學生所以可以拿到比較便宜的底片和沖印廠的折扣,但《與山》時在山上,你的子彈就那幾發,看到打板上寫 take 3 的時候,腦袋裡面真的會換算還有多少可以拍;當時只要拍攝前,都會去找學長姊學弟妹、冰箱到處翻,只要有超過 20 呎的都帶著備用。變成數位以後,我有個習慣是不太相信拍到超過 6 take的東西,已經不單純是技術問題,我會換一個方式處理。商業的東西當然不一定,廣告類的 demo shot 大概在 6 比 1 或 7 比 1 就緊繃了;紀錄片大概是 400 比 1。

《與山》劇照。
李:我平均都是 5 比 1。《神奇洗衣機》是第一次使用 HD,很多技術都不熟練,所以有很多調整;2007 年《基因決定我愛你》是底片末代,我大概都控制在上面的比例。
紀錄片大多是生活片段,勢必在腳本或後期剪接時有結構的考量,會怎麼處理?
沈:紀錄片讓我覺得踏實,但不是在還原事實,比較是創作一種看不到的東西。在前期做功課、田調時我有寫日記的習慣,這有點像拍劇情片要讓角色立體所做的功課,而這種習慣會讓我在進入現場前有一種想像跟推估,這個推估會成為我下次行動的準則。這種戲劇式的預想,也會決定我攝影機拍攝的方法。
無論紀錄片或劇情片,兩位有相信的,或想要捕捉的真實嗎?
李:我沒拍過紀錄片,我也無法拍。一個人要活生生把自己展現在我面前,我會覺得好可怕。我覺得要演員去掏出內在記憶、演某個生命片段是很殘酷的,所以我無法面對沒受過訓練的人、讓他做這麼殘忍的事情,這是屬於我理性的另外一面。
沈:我們三個人在台上,你們在台下聽,可能有一個真實存在:這裡多少人、氣溫多少度等等,但這是我認定的真實,每個人的真實和我不一樣。我會很介意攝影師進到現場決定的第一個鏡位,這跟工作人員理解的真實、以及我理解的真實有關。當你讀了腳本、進到現場後擺的第一個機位,就決定了整場戲怎麼運轉,這個機位會影響你們對真實的共識。
我會很介意攝影師進到現場決定的第一個鏡位,這跟工作人員理解的真實、以及我理解的真實有關。
我跟演員溝通時,也不會把劇本當作依據,我跟每個演員認識的時間非常長,我必須先認識他而不是這個電影,我必須先認定我們之間「你是誰」、「我是誰」,確認之後才有辦法工作,這種真實不是靠劇本建立起來,而是靠人跟人的溝通。我最常問攝影師的是:「剛剛這樣走一遍,你看到了什麼?」不管拍紀錄片、劇情片、廣告都一樣,我想要確定我們看到的差異在哪裡?如果雙方看到的情感是一樣的,就可以繼續工作下去,每個人認定的真實都不一樣,但透過電影,是在提煉並呈現作者認定的「真實」,所以我覺得沒有「真正的真實」。
成為導演後一路走來,讓你們成長的養分是什麼?
沈:我很喜歡看電影、討論電影,但當導演其實比較多是跟工作人員接觸。電影藝術創作上有個複雜性,是在於許多部門的集體工作。我從大一開始就到各部門學習技術,所以前三年都沒有做到導演組,大多是在完成技術需求,像是提供攝影畫面的構思及分鏡表,大家也因此樂於跟我合作。畢業之後,樓一安、陳芯宜的前兩三部片我都是攝影,攝影這職位對我來說是進可攻、退可守,決定了分鏡、焦段跟拍攝方法,其實就決定了觀眾怎麼看這個故事。在跟阿飽(陳芯宜)工作時,常常會為了「鏡頭為什麼要擺這裡」有很冗長的辯論,也因為這些以攝影機單兵作戰的經驗,造就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李:我是那種考試都要第一名的學生,很喜歡看電影,有次看電影時,突然希望自己的名字可以列在工作人員名單,這樣就人生無憾了,於是就應徵了《台灣靈異事件》的製片助理,一個月工作 30 天,一天工作 18 個小時,撐了兩個月後辭職,但也發現自己滿樂在其中的;接著去做了黃玉珊導演的製片助理,第一部電影是萬仁導演的片子。後來比較專心在製片組、導演組的場記和副導工作,是正規的片廠訓練出身。

在演員溝通上,有什麼心得跟我們分享?
沈:我滿喜歡跟演員溝通的,但是我已經決定不再拍功能導向的影片,因為那些在短時間內營造出來的效果太不合理了,那就是會讓我心虛的溝通。我對真實有一種渴望,有個我想突破、但不是每次都可以突破的困難,就是「演員自覺性的表演狀態」。有的演員對於要放下「自己在表演」這件事真的有困難,但「有意識的表演」是我希望可以藉由溝通去除的,「很努力的表演」會讓我不能接受,一個場景內如果有一個這樣的演員,那個 take 就毀了。
李:我很喜歡和很會跟演員溝通的導演一起工作,像王小棣導演,我甚至想去報名 Q place 的表演課。我的演員其實都經過專注訓練、聆聽訓練、放鬆訓練,只是在現場工作時,我還是想知道演員的狀態是什麼,所以我很想換一個角度試試看了解演員。演員可以被控制行動,但感覺是無法被控制的,你不能給情緒指導,要給動作指導跟氛圍塑造。
對當下的台灣短片有什麼觀察和建言?
李:前幾年我帶學校的畢製,關注自身、父母、家庭的片子都有出現,往內挖到的情感可能大同小異,但我覺得想像力是新生代比較缺乏的。我自己很期待題材創新或是表現手法幽默的片子,想想看如果你幾天之內要看完兩百部片子,裡面又全都在講憂鬱跟自殺,我覺得你會比創作者還憂鬱還想自殺。(群眾笑)
沈:創作者的作品對自己誠不誠實,其實會很明顯。
去符合台灣某種正確的意識形態會讓你覺得自己有價值,但這個正確跟你自己有連結嗎?今年做台北電影節看了很多片,我覺得真正的誠實,是表達你真正關注的事情,即使那跟台灣當下的氛圍是無關的。
座談尾聲,沈可尚表示回望十七年前執意要完成作品的自己,讓他明白這是持續滾動的過程,而過程中真正獲得的並非業界資歷,而是願意互相分享想法的夥伴。他說:「這些連結會讓一切變得有趣,不論台灣電影景氣與否,你們彼此分享的情感可以讓自己走下去,拍電影不只是完成產業鏈裡的工作,要試著開創自己的語境跟態度。」李芸嬋則說,即使相隔多年重看《神奇洗衣機》,仍可以看到自己當時很用力在拍的狀態,什麼樣的人就會呈現出什麼樣的作品,努力固然是好事也是必須,但自己的樣子很難被扭轉,「所以,先真心面對自己吧!」
註|本文為 2017 SHORT LAB 短片實驗室春季班課程「《與山》、《神奇洗衣機》映後座談」活動記錄。
【2017 SHORT LAB 短片實驗室】
由中華民國電影創作協會(簡稱電影創作聯盟,TOFU)主辦的短片實驗室,是針對欲從事影像創作的電影新鮮人所籌劃的影像教育機制。一年兩季,春季班以前期製片及劇本故事為主;秋季班以後期製作及粗剪為主。希望在一般學校體制之外、以及各種徵件/補助/競賽之前,提供另一種開放/學習/實作的互動平台。短片可以天馬行空、自由創作;可以實驗各種可能、形成同儕關係;這是實踐的「培養皿」,也是一種「做中學」的精神。
【孫志熙】
曾任《CUE 電影生活誌》、《SCOPE 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