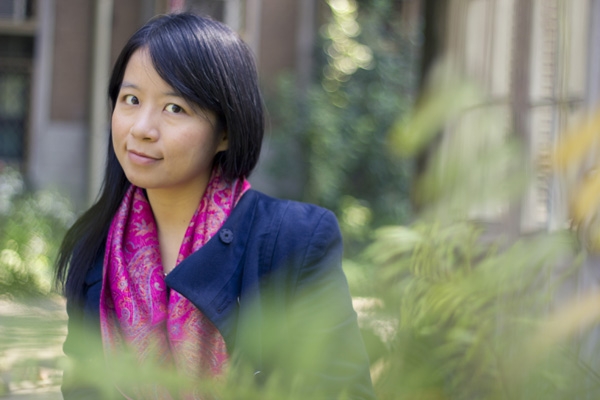凝視香港|對照記:從摩登上海看現代香江
我們要怎麼凝視香港?是單純去看它的高樓大廈?還是去看它樓房隙縫中的生活場景?現代的無根建築到處都是,而在城市中札根的生活卻是各有千秋。如果城市中最美的風景不是空間而是人,那我們看香港是要看它的什麼才好呢?
上述的問題其實說明了一件事情,當我們看香港這座現代化的巨型城市時,不僅要注意到它如何發展,更重要的是人在這發展之中的生活與應變。生於台灣、住在香港、長年研究上海現代文學的李歐梵先生,曾在〈香港上海的文化雙城記〉提出這樣一個屬於香港自深困境的見解:「上海畢竟有一個都市文化的背景﹐所以發展起來較容易,而香港引進的卻是資本主義影響下的商品文化,歷史的資源 似乎不足。」而他所著的《上海摩登》,就是在寫那個具有縱深的都市文化。
摩登,無疑是「現代(modern)」被扭曲的奇特發音版本,但在我看來,它實際上是「現代」的變形,而且是帶有某種佛箴的想像。摩登不只是 modern 的音譯,而其實是來自佛經的說法,在《楞嚴經》中有摩登伽與摩登女的愛情故事,是一則關於面對塵世慾望而最終遁入空門的故事。而我想舉一部以上海為背景的電影當作例子,我認為荷蘭新銳導演戴荻(David Verbeek)的《迷樂上海》(Shanghai Trance,2008)是一部有本事深刻體現這種佛僧觀看的電影。
孤峰高出雲,上有音色界。
識得普賢才,虛空猶窄隘。
悟明理性時,不作塵境界。
劫大或恫然,此山無變壞。
──唐僧鄧隱峰《隱峰十詠》之一:〈白銀峰〉
城市經驗的反芻與回憶本是一場蒙太奇運動,錯接的視覺中可能包括了一塊招牌、一失之交臂的少女,抑或是一場大完工或大破壞的驚鴻場景,都是生活中的片段記憶重新組合。只是這種經驗,沒能像電影經驗走得這麼遠,能在時空中跳躍又伴隨著發人深省的恫嚇力,如佛僧的靈視,看見劫大或恫然。《迷樂上海》的蒙太奇,極致地做到這點,它讓我們直接跳到重點,讓我們在一城中,原定的呼吸、身體循序的運動和都會景致的自然接連完全被打斷。然而,《迷樂上海》的蒙太奇卻又不只如此,這裡的剪接沒有前戲可言,總是直接進入時間核心,產生當下對事件的見證。這部電影讓原本只意味著運動變換的影像「調裝」(即法文動詞「monter」)之蒙太奇(Montage),流變作為另一個指稱:萌態奇(Montrage),時間的「呈現」(法文動詞「montrer」)。
電影一開場的兩個鏡頭就道盡上述這一切:片頭字卡名單的背後充斥流光的畫面,從抽象性翻譯 Trance 音樂的流明色線在幾個視覺破綻中,我們看到霓虹燈招牌簡字體,才驚覺那是高架橋上隔音板的破綻,原來流光幻覺是汽車高速行駛下的衍生物。發現上海這座大城到了沒兩秒,導演二話不說,直接剪接到死白的日間大工地,前景兩個民工掘著地基,背後襯著墓碑般的金茂大廈和環球金融中心(2006年還沒蓋完時,正巧與金茂的九重天尖頂一樣高)。導演用幾乎是絕對速度的萌態奇,讓我們「直視現實」並「陷於時間」,如佛的潛行換渡。
電影最讓人震驚、且很可能會讓觀眾從影院 Lounge 沙發危坐起來的鏡頭組構,莫過於張恒飾演的張儀那個角色,站在幾十層高的情夫豪宅家中的一雙畫面。上一個鏡頭是她走到窗邊靜默著,下一個 Take 就是鏡頭從玻璃窗外面拍下臉上愁容卻又斑斕疊映著都市蜃樓的霓光夜景,而那個 Take 也收入了整個市囂的聲音,轟隆隆的低頻音,像是一場現代性的大風,吹向那張美麗但又有些蕭索的臉龐,張儀隔於玻璃罩內,似乎無動於衷。室內和室外的兩個鏡頭(加音效)形成了極大時間樣態的反差,卻又神奇地貼合於當代城市的非協調感。然而,上海是沒有山的(蘇州也只有虎丘),只有高樓能出雲,與唐僧鄧隱峰《隱峰十詠》相比,江下上海正是光譜的另一端,於是追求促狹的虛空。
在這部電影裡頭,電影還不只是用視覺性跳接來呈現現代性的驚鴻與惶惑,更厲害的是,導演對聲音的處理(或更確切來說,是林強所作的音樂配置),讓戲中多線進行的人物情感,錯落於舞廳裡的一場長戲之中,然而,堆疊起來的情感卻不是所謂戲劇張力論式的陷入膠著,而像是每個主角不斷地進行各種形式的自我掏空,此情此狀上演在我們面前,電音充斥全場,但舞場散佈的雷射光束間卻是全然的空虛。這是情感內聚性宣告正式背離的絕對性時刻,故事情感線中從發生以來都沒有耦合之感,不過,若問這部電影的 Trance 精神何在的話,這場戲裡對所有情感一次性徵收的真空狀態,或可名之。
《迷樂上海》這番「蒙太奇 / 萌態奇」的視覺語藝,如電音軋斷的轉折,更像是現代人在舞場銳氣遂行之時突然遭逢的燈光全亮,全場一片狼藉、破落之窘境看得清清楚楚,這種如夢乍醒恍若隔世之奇,可能遠遠超過那些被醚香、仙樂貫穿之執迷者所能想像。「破完有空,空盡能出」,或許這是大隱市者戴荻,對這時代所下的一道佛箴。
最會將上海與香港進行身世對照的張愛玲曾經這樣寫過:「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她可能沒這麼說過,但若是破壞如此巨大,那麼我們要如何去觀看甚至親身經歷這場破壞呢?
據說佛之所以總是低垂著眼幕看著眾生,就是因為祂難以逼視這眼前的無常與災厄,如果許鞍華改編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最終讓一個城市的陷落小小成就了兩人的幸福,那麼陳果導演《香港有個荷里活》片中的周迅所飾演的那一位普渡眾生的應召女,就更帶有某種用凝視貫穿香港的特殊氣質。
拍攝上海、香港的導演如戴荻、許鞍華、陳果等人,則對現代亞洲城市帶有著一種特殊凝視方式,它似佛看破一切,但卻不帶著慈悲,它不止是將城市空間景觀進行蒙太奇剪接,而是對於「成、住、壞、空」的人生時間階段呈顯無遺,有著萌態奇式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