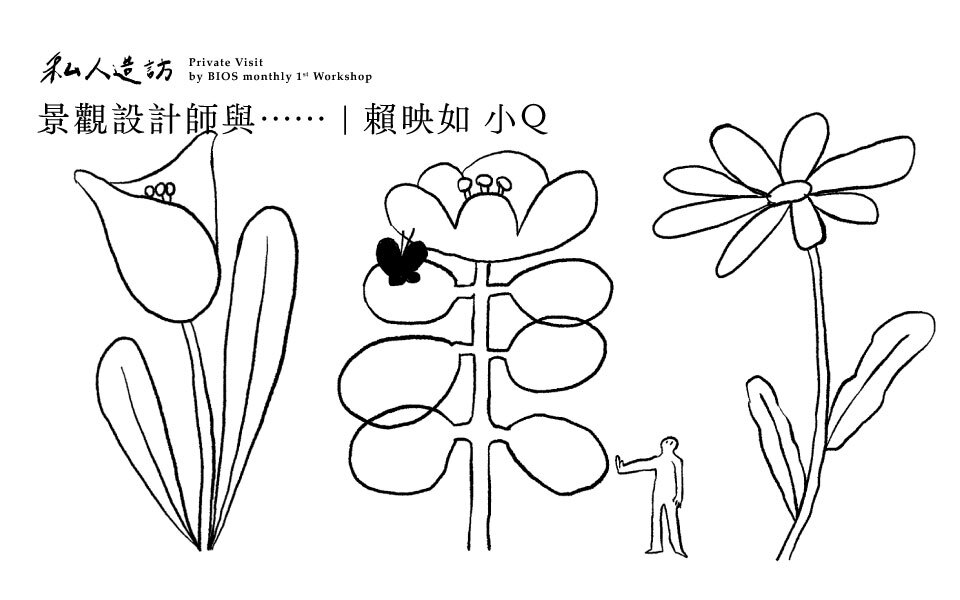
私人造訪・野再設計小Q|不管植物還是人,活著就是要扭來扭去啊!
野再設計成立滿五年,小Q(賴映如)的工作室藏身於信義區巷弄裡的公寓二樓,集寢居、辦公為一體,空間不大,員工也少少的。
她顯然不信奉所謂健全的組織發展或是上下班打卡那套,有會就開,有事就做,不進辦公室也不要緊,「我請學姐來幫我畫圖,不過她每天必須五點到家,要煮飯給小孩吃;暑假的時候也不能來,因為要陪小孩。一般公司很少能這樣,但我可以啊!反正她能力很強。」
再早個十年,那句「可以」的底氣恐怕還難以脫口。
景觀設計系畢業,十來年間小Q陸續待了幾家工程、園藝公司,技能純熟了,自知頂著資深設計師的頭銜受雇於人有其極限──學會了的東西沒意思,當不上管理職又不甘只做工具人。好像只剩下開公司了,如果,要自由的話。
「我跟之前的老闆講,結果他竟然說:『你早該開公司了。』」小Q調皮一笑,「但我從那時講到十年後才開,他很想扁我。」
最後公司是開了,接的卻都是奇奇怪怪的案子:到初鹿牧場比劃牛怎麼放、上美術館導覽畫中植物和壓抑的民族性,在穀稻秋聲會場又是綁稻草又是拉帆布……,外人霧裡看花,自己則笑稱不務正業。「還是有在畫圖啦!」她強調。
「乖一點,聽話」
剛畢業沒多久,小Q待過一間工程公司的業務部。上班如戰場,表定九點,但八點就會接到工地現場的電話,狀況很多,腦中全是待辦事項和沒到貨的磁磚。
工地五點收工,混亂的局面才稍平息,卻是她趕設計圖的開始。這樣有生活品質可言?「沒有啊,印象中我很少晚上九點前下班。畫圖畫到十點多,隔天一早八點又得開始接電話了。」
不過好處是每天都有工地可看。小Q跑得勤,一有好奇,或是圖形難放樣,工程部的前輩就讓她去工地看,不會的東西現場教。「不要看他們身上都是土,數學超好,還會跟你講 sin、cos。」
實打實的工地養成,鐵打的肝與意志。
這讓她回到設計崗位時,不用任人宰割、不用落入只會畫圖而無法執行的窘境。工班要求改圖?她可不吃這種悶虧,「有一次工頭跟我說圖要改,不然做不出來。我就說怎麼會做不出來?我做給你看。」她對自己的圖有自信,既然畫得出來就做得出來。
「後來他們看到我都很乖,覺得這設計師怎麼都看得懂。」
捕捉到對方心思的小Q也沒打算得理不饒人,因為她知道──難做,百分之百是錢的問題,工班會這樣說,往往是因為過去和設計師也有不好的溝通經驗。沒關係,我們好好談。
哪塊磚的價格報低了?那就換個材料;哪些地方要敲掉很麻煩不想弄?那就改個動線,不敲無妨,「所以現場就很喜歡我,因為我懂他們的困難;他們知道欠我人情,也會在其他地方還我。」攤開來講雙方都舒坦,工班無須唬弄,設計師也不用搞得沒尊嚴。
第三份工作在一家園藝公司,入職沒多久便碰上產業大事記──舉辦在即的 2010 臺北國際花博。不只公部門首次承辦,全台的園藝供應商攜手合作也是頭一遭,這中間有許多溝通的難處,問小Q扮演怎麼樣的角色,她直率地笑說,「負責去罵人的啊!當時老闆派我去開會,跟我說去生氣沒關係,大不了解約。」
台灣第一次辦國際花博,野心很大。光是百合花,契約上要求廠商進口近百種。國內可見的品種頂多四十,至於種得活與否,就連種球商也只敢保證二十,到底哪來的百種?
水土若不服,花真的就種不起來。她想爭取試種,但沒那麼順利,因為對公部門來說,預算把關、防止廠商鑽漏洞亦需謹慎。還好最後有試種,才發現很多品種的花期根本撐不了當初規劃的三十天,有的甚至第十五天就沒花了。
「我跟規劃的單位說:我們會這樣堅持,就是確保可以呈現出花博的效果。」回顧當時的忙亂,小Q有些打趣地笑道:「後來他們都很配合我,但我想應該也快被我氣死了,畢竟我一直恐嚇人家。」
有時候只是換一套玩法
小Q說自己有點沒大沒小。所謂規矩、限制,那些「不能做的事情」在她成長過程中的存在感偏低,連家長在乎的事都和其他長輩不太一樣。
有件事她印象很深,小時候拿打火機去田裡焢土窯,回家後被臭罵一頓──居然不是因為玩火,也不是農地怎麼了,而是:家中月曆還沒過完欸,怎麼可以拿去做火種?
「我們家沒有典型權威啊!所以我人生也沒怕過。」
這大概就是為什麼面對身價上億的業主,也絲毫不磨損她對案子天馬行空的興致,「除了景觀專業外,我也常常在會議上表達對基地營運的看法,或提一些有的沒的點子,可能對他們來說我很好玩吧。」
那些趁著玩心大起,每天在腦中橫行的「有的沒的」,在成立野再設計開始自主接案後有了實踐的可能。小Q說建案接得比較少,「有機會嘗試的話,我不想要全部都是同一類型的案子。」
景觀設計師除了建案還能接什麼?
「我遇過幾個業主想找的是可以跟他們一起發想、一起玩的人,但是如果我的公司已經很有規模,通常會希望案子執行能在一個框架內,沒辦法一直開外掛,所以有時候公司規模小也算是好處,就可以保有彈性。」
小Q也發現許多業主找上門,希望用景觀設計來替自己解決問題,「在他的腦子裡或許是這樣,但你不一定要給。要去想他為什麼來找你?當他說出『我需要景觀設計』時,真正的動機是什麼?」景觀不佳也好,遊憩內容單調、來客率低也罷,景觀設計是一途,但除此之外不乏更適合的路徑。
台東初鹿牧場的案子就是這樣互相腦力激盪出來的。業主明確表示想做景觀設計,但小Q實際走訪,眼前一大片坡地做起來預算很高就算了,日後維護更是驚人,效益也可能不太好,等於把錢丟進水裡。當天,她就和業主說:其實你不需要景觀設計。
「當時業主問那需要什麼?我想一想就開始亂講。」要增加牧場豐富度的方法很多,最直觀的是定時導覽,其他諸如設計遊戲包、密室逃脫也新穎好玩,專業不在此的她只出一張嘴,以為可以置身事外。沒想到兩、三天後對方又打電話來,說還是想找小Q做──
做什麼?就妳講的那些啊。但我不會啊?妳會啦妳會!
「什麼跟什麼啊。」情節發展莫名,小Q哭笑不得。
問題也可以是資源
案子終究是接了下來。
接了案就得生團隊,當時她心想慘了,大家都在上班哪有空一起玩這齣。煩惱之際迎面巧遇先前活動認識的志工,對方還是碩士生,聽了小Q的計劃覺得有意思,順勢就被延攬,還乾脆搬到池上住──核心團隊就是這樣組隊來的,兩、三個人捲起袖子開始做資料盤點、田調訪談,而後也集結台東當地的合作夥伴,陸續辦了聲音地圖製作、野草膏採集、野土捏陶等系列活動。
隨著動線調整、籌辦工作坊逐步成形,小Q發現自己在做的,其實是品牌體驗,於是與團隊共同發想了屬於牧場的世界觀,「初鹿牧場有牛奶饅頭嘛,設定是這樣的:牧場有一個平行宇宙,裡面的居民都是饅頭,叫作饅饅,他們的能源就是牛奶。乳牛神會提供牛奶給大家,但需要這些饅饅們認真耕作給牛吃⋯⋯」她說,日後園區還有很多事情等待發生,但不急,故事先放在心裡。
過去初鹿牧場收到最多的 Google 評論是:沒有牛。
其實不是沒有牛,而是基於食安考量,泌乳期的牛無法跟遊客接觸。於是硬體設備改善再多民眾也無感,因為沒牛可看總是掃興。怨聲傳到業主耳裡,他們買了幾隻塑膠牛擺在牧場──評論就變成:都是假牛。
理解畜牧業的生產規則與限制,也明白作為觀光場域自然想要拓展營業的亮點,小Q跟牧場的管理部門來回討論,初步有了一起努力的共識,「母牛放牧風險高的話,那放公牛也好。」而牧場目前也已經依照氣候條件,開始讓尚在待產的母牛或小女牛進行放牧了。
「放牛」固然重要,放哪更是學問。她想像自己是遊客驅車直上時,一眼就鎖定遠處那塊空置的坡地,「天氣熱你可能會懶得走,但看到牛群就會讓人想要下去玩。」
過去業界的工作經驗讓她累積解決問題的能力,案子進來就處理,可以說是完全的目標導向,雖然很有效率,但有時候連她自己也不太知道在服務什麼。透過近年執行的各個專案,小Q也開始在邊做邊玩的過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設計哲學。
「很多人說設計就是要解決問題,可是現在的我有其他的看法。看起來是問題的,或許是資源。我想要成為把問題變成資源的設計師。」

為初鹿牧場規劃品牌活動,讓在地人、遊客重新體驗新的初鹿牧場宇宙
停留是為了相遇
大學時期,老師上課播萬仁導演的《超級》三部曲,電影圍繞在現代化下的城鄉關係,以及都市更新所造成的人文、商業震盪,小Q想起裡頭男人乘著計程車,沿著高架橋縱覽整個台北都會的片段,滄桑清冷。
高架橋看似解決了交通難題,很容易被視作象徵進步的符碼,但從系統另一面切入的小Q知道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高架橋不會帶來進步,一旦我們能快速通過,幹嘛還停留?我去富里就發現這件事,舊台九線經過富里,新台九線卻是從外側穿越它,所以大家就忘了富里在哪。」
為了抵抗遺忘,小Q想要停下來──於是富里成了她的第二故鄉,太麻里則是近年往返台北與花東間的生活據點。
農村待的時間一長,她觀察到:身邊不少嚮往花東移居而來的朋友買不了建地也住不起農舍,「他們只好蓋一個小小的資材室住在裡面。」原本是用來存放農具、肥料等資材的空間,拿來住人顯得將就,卻又因這樣出格的共同經驗,形塑出另一種兼有荒謬與詼諧的認同。居住型態迥異、生活模式有待挖掘,在東部生活到底還需要什麼?
也許只是山泉水的管線被土石埋掉需要清淤,也許只是想找人除草、想有一張製作精良的木桌,想找人聊天。小Q和伙伴們決定以「移居生活資材室」為名,建立花東移居者們的交流平台,把這幾年看到的需求跟資源做整合的實驗。
「有需要你就進來資材室,高興你們兩個就認識。」團隊找來物理治療師分享農民保健,也請建築設計師談談國土計畫後的土地容許使用。活動反響熱烈,光是把人兜在一起,就能期待新的火花。小Q赫然發覺,原來資材室就是與人相遇的地方,既未知,又自由。
更早之前,她就習慣了身邊總是有人。北漂在外租屋朋友都愛來,生活空間被他人佔據已是一種常態。「我還住在小套房的時候,朋友就常常來,而且床上一定會坐人。」野再開工作室後,陣地轉移了,卻不影響大家還是愛待在她的空間裡殺時間,與其說抱怨,更多的是拿他們沒辦法的笑意,「都待到半夜啊,捷運都沒了還不走。」
一切非刻意安排,但小Q就是有本事將這套「交誼廳系統」隨處複製,這或許得追溯到她生長在一個慷慨家庭的血脈:老家在台中大坑的鄉下,家門沒鎖,下課後客廳裡面永遠都有別人;如果說家裡像里民活動中心,那媽媽就是沒牌里長。
生活空間裡有外人,以前多少覺得不便。更大一點後,才明白停留所帶來的理解、互信有多珍貴,那些無心促成的交流正是她能量的蓄積。「原本以為自己平常在瞎忙,但其實是很有凝聚力的,誰有了什麼事,大家會想辦法一起去幫他。很奇怪,會被這種東西感動。」
想起來
大學以前的小Q喜歡畫畫,但讀了景觀設計系後才發現:這不只是「畫畫」而已。被課業追趕的日子,讓沒有設計底子的她一度萌生轉系念頭,「但後來去苗圃打工,發現我好喜歡跟植物相處,就留下來了。」

初鹿牧場活動,帶領小朋友們認識牧場的植物
今年剛滿四十歲的小Q,在等待捷運的空檔還會謎樣扭動,她說自己長大得比較慢。然而心智成長的維度取決於一念和恆常練習,有時無關年齡,她也知道。時至今日,她不只喜歡植物,也越來越能掌握,植物如何作為與人交流的共同語言,比如:剪一枝迷迭香可以增進記憶力;或是一株檸檬馬鞭草,它可以解宿醉──就是喜歡這種信手拈來都可以聊的東西。
前年北師美術館展出《不朽的青春》時,邀請她來會場導覽,「看展的時候找植物是我的興趣,所以我很能亂兜。我可以講植物科普,也可以講植物人文。看到畫,我會想這麼日式的畫風,裡面為什麼出現台灣的本土植物?」
畫榕樹、畫月桃,畫日本都沒有的植物──這是日治時期的台灣畫家,迂迴排遣民族壓抑的方式,「如果懂植物,一看就知道這是台灣人畫的。」
能替一段失語的歷史辨識出發聲的位置,是一種難言的感動。
「我最喜歡的景觀設計師是 Burle Marx,一名巴西籍的老爺爺。他為了找到巴西的原生植物做造景,把自己變成一名植物學家,甚至還有一座植物園。」曾被葡萄牙殖民的巴西,景觀風格多有對稱的歐式花園,「大家都覺得對稱才是美,整齊才是文明,但 Burle Marx 覺得巴西的靈魂是森巴舞,就是要扭來扭去啊!怎麼可以做整齊的事情!有沒有很皮?他是我的心頭好!」
講到這位老爺爺她笑得很開心,這位改變巴西地景的設計師一直到過世前都只在巴西做景觀設計。「他說一個景觀設計師,怎麼可以去做你沒住過、不熟悉的土地?」那想必是深愛土地的人才能擁有的覺悟吧,不為留名、不急於在短暫的生命裡必然實踐些什麼。
「因為他,我開始想做一件比生命長的事情,我想要找回跟土地重新連結的景觀。」比生命長意味什麼?小Q說:「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但影響還在,這就是比生命還長。」
需要連結是因為早已失聯,「我們已經太習慣用工業產出的東西,忘了相思木其實是拿來做礦坑結構,楓香可以種椴木香菇;楓糖就是楓樹的樹脂,那潤滑油、蠟燭的油怎麼來的?植物身上來的。可是我們現在已經忘記這些事了。」
除了植物的名姓,忘記的事物還遠遠不及,小Q說一位經營療癒品牌的友人提醒她的公司規模停滯,「別人可能覺得我公司開得很料小(liāu-siáu,不起眼之意),但我不是很在意別人怎麼想。我就反問他,做這些事情你快樂嗎?」對小Q來說,設計和療癒,或許不脫是門生意,但自己踏實享受也是很重要的。
為了保有自由與彈性,小Q形容案子確實常稀哩呼嚕、不太在路上的樣子,但成立公司的目的本來就不只是為了營利,如果還能交朋友,創造更多好玩的事物,那就真的太好了。
她繼續講著荷蘭人引進阿勃勒的故事,談樟腦貿易和原住民遷徙,也從植物談王永慶跟孫海,「不用扯到政治或敏感議題,光是講這些,大家聽了就會『瞳孔地震』。」
小Q沒有要改變什麼,和植物一起,她說,「我只是要讓人們想起來而已。」
【私人造訪 Private Visit】
BIOS monthly 首度開設媒體寫作工作坊,真是辛苦了(自己說?)最後一份稿件,由 BIOS 及講師群媒合(=通靈)陌生相遇可能帶來的火花,讓學員們走進專訪現場,展開一場私人造訪的交流與寫作練習。
*本工作坊獲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藝文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