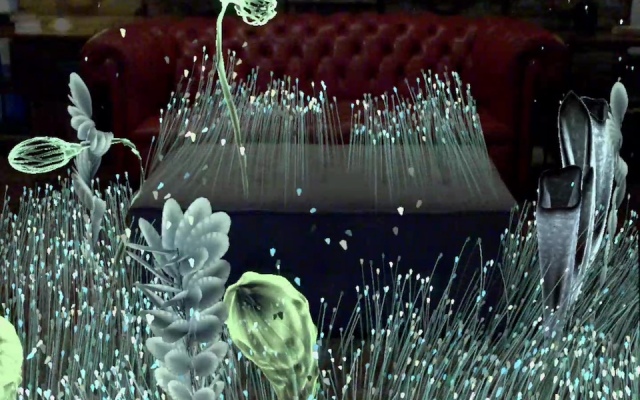找愛的通俗劇:專訪周東彥「國家級約會計畫」,相約一起孤獨
影像詩人、創作才子⋯⋯周東彥擁有許多離地飛天的稱號,最近兩廳院駐館活動「國家級約會計畫」公布,主旨與念想卻很世俗。愛在哪裡?愛是什麼?以及——敢愛就來。如同陳玉慧《徵婚啟事》的軒然大波,同志版徵婚行動引發熱烈關注,讚聲裡也夾雜些許異樣的眼光。一切行動的內核裡,其實站著一個平凡的,找愛的人。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逃不出通俗劇。」做藝術的人有比較崇高嗎?年屆三十七,他說感覺到身體漸老,以及無可避免的願求:「通俗劇會存在跟感動人,有它超越的意義,就是因為我們都很通俗、我們都不特別。尤其我爸在四五年前中風臥床,看到我媽照顧他,還有家裡的狀態⋯⋯真的是很現實的。」
沒有伴的日常,隨著年歲漸長有了暗影:「漸漸會覺得,如果一個人老去真的有點可怕,我是害怕的。」
|
|
美麗少年
《徵婚啟事》已面世三十週年。2019 年的今日,當初以「生無悔,死無懼」求有緣人的陳玉慧已經歷離散,出版《德國丈夫》,書寫與前夫明夏一日內的天雷地火,結褵及外遇;而周東彥動用昭告天下的層級拋出「國家級約會計畫」,也像是給同志們一個遲來的拋繡球大典。
這樣的大動作,其實最初萌芽於同婚公投失敗收場的焦慮:「那時候就覺得,到底要怎麼做得更多?如何活得再更 queer、如何真的被看到?」國家級約會計畫將向來隱匿、幽微的同志情事放到最大,對周東彥來說:「行動本身,應該就是它的 statement(聲明)。」
採訪前一晚宛如命定,他因北影有機會重看陳俊志《美麗少年》。放映結束後,台上聞天祥和楊力州理性爬梳,但台下的周東彥,以這部電影感性複習了自己的同志史。二十一年前,高二的他才剛開始跑劇場,在耕莘文教院裡遇到一個拿著攝影機的人,讓他對攝影機產生興趣。那個人就是陳俊志。
放映那晚沒說出口的是,他想讓琪姐知道自己曾被她點亮:「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家裡很支持我。做為一個 artist,我基本上沒有什麼偉大的悲痛,沒有從小殘酷的經驗諸如此類的。然後,竟然有一個人在 1998、1999 年那時候就拍了三個同志擁抱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坐在一個小小的放映廳裡就覺得,原來可以這樣子喔。他給了我一個很容易接受自己的方式。」
《美麗少年》聚焦摩根、小羽、小丙三人的經歷,如影片簡介所寫:「透過三個 Y 世代青少年同志生命史的真實紀錄,我們也聽見了來自社會角落的邊緣發聲。」陳俊志讓孤絕的同志們見到彼此的生命經驗,也讓尖銳不可碰觸的邊緣變得可以站立。二十年經過,那股強勁的支持力道千絲萬縷化進周東彥的創作:「我不想太快帶到說,是因為《美麗少年》所以想要做些什麼,但是其實它有很大的成分在裡頭,就是男同志也可以長這樣;男同志不一定要蓄鬍、beefy,然後很 muscular⋯⋯」
|
|
「國家級約會計畫」的意義,外層是對著世界說「男同志也可以徵婚」,更內層則想說:同志族群裡,無論哪種性別特質,都有尋愛的能力與權利。《美麗少年》像是即時的提醒,讓周東彥重新回溯自己的創作意念:「看到這個二十年前的片子讓我覺得,不論是拍片或是創作,就是想要說點什麼,想要被理解,想要創造更多對話的空間。」
被責難,也要先說愛你
「國家級約會計畫」線上公布後,填寫表單自介報名者有 117 人,最終 35 位有緣人在七月某個週末抵達國家戲劇院,與周東彥來場十分鐘的快速約會。
很狂的計畫,源自他與任職兩廳院的閨蜜之間玩笑話。好友說,駐館最重要就是發自內心的渴望,周東彥的回應很真實:「我最需要的就是伴侶,可不可以辦一個約會計畫?結果這個人(好友)就認真了。」去太原路買繡球、拍婚紗照、公開徵婚⋯⋯,周東彥說,這些前置作業可說是計畫裡最接近「表演」的部分,再往後,就完全無法預料了。
約會前兩天,周東彥嚴重失眠。他不是不知道這個計畫可能引來的批評,看著廣場上自己身著西裝的海報,他腦中有鄉民八卦小劇場:「大家會說,欸那個誰誰誰跟他怎麼樣過、我聽說他怎麼樣⋯⋯」有人半開玩笑說他高高在上「在選妃」;也有人問,周東彥你是不是有點在消費男同志。「看到的時候我在哥本哈根。那整天走來走去,其實都在在乎這句話,居然會有一個人,而且他是相對和我在同一個族群裡的,他會問我是否在消費男同志。」

「國家級約會計畫」進行實況。

「國家級約會計畫」進行實況。
帶著困惑,他回去徵詢大學老師意見,甚至問了林懷民。原本有點怕:「我就很擔心說我做這個事情,會收到他(林懷民)的訊息說搞什麼這類的,決定先跟他講,他就說太棒啦!快去做!」兩廳院總監聽聞計畫也發難:東彥,要做就做到底,「我就想說,那我在怕什麼?」
拍婚紗照前幾天,他看到蔡依林分享 Brené Brown 的影片,有了完成的力氣:「通常這種心靈雞湯我們就會有點害怕,但是我看了一下,就覺得這個心靈雞湯有 work。」Brown 最知名的 TED 演講〈脆弱的力量〉說明脆弱與勇氣的雙生關係,她分享自己的研究結果,那些全心全意熱愛自己及世界的人,與總是掙扎著的人之間唯一的差異只有:他們相信自己是值得被愛的。他們相信,自己的脆弱是美的。
Brown 說,那是一群願意先說我愛你的人。因為敢於暴露脆弱,讓他們擁有勇氣。周東彥的約會計畫也是如此,把自己丟在眾人面前,面對批評與未知。他複誦即時到來的小小啟示,像提醒自己:「就是因為危險的事情,所以你才要去做,不是嗎?」
事後他也被問,公開徵友,不會顯得很可悲嗎?他心裡有了答案:「其實,這不是很重要嗎?可以顯現出脆弱,這件事情它幾乎是我最近對 intimacy(親密)研究的第一步。你可以在這個人面前脆弱,在這個人面前什麼都不會、或者是很笨,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覺得大部分的藝術作品其實都在 expose(暴露)這個部分,只是其他人相對沒有把自己拿出來。」
把自己拿出來,不會只是消耗。約會計畫裡,即使有人質疑他在消費同性戀議題,「但是也有人問我說,『到底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舉辦這樣的活動?』所以我就覺得,還是會有被瞭解的空間。」
找愛,沒有答案
把自己拿出來,是周東彥埋藏在眾多作品裡的特質。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你找什麼?》以一句普世皆知的交友軟體招呼語為題,探訪 60 餘位男同志的網路交友狀況與使用心得。最讓人驚愕的一幕,是其中一位受訪者拒絕回答愛是什麼,甚至帶點情緒反問:「拜託,你不能問我這個問題。我要怎麼回答?」
下一幕我們才發現,那是周東彥的前男友。
他在紀錄片裡剖析自己的愛情,問前男友什麼是愛。一如這次約會計畫,以身試情,勢必得消耗自己。他總結約會計劃那天,就是一個累字:「精疲力盡,超級累。因為你又要準備自己,但又不知道怎麼準備。你問別人,也被問,在一個一直互相觀看的狀態,非常消耗,精氣神都被搗毀的感覺。」
暴露私我,搗毀自己,把「周東彥」放在檯面上做餌,實則是對人與人如何相遇與相戀抱持疑惑。如這次行動公/私界線模糊的展演,從前《非常男女》一路到現在《王子的約會》、《非誠勿擾》其實都是:「private 跟 public 這件事本來就是在媒體、全世界各個領域都被一定程度的搬演過。我對這個搬演沒有太大興趣,我是對於怎麼樣遇到、怎麼樣選擇一個人的過程有興趣。」
隨著《你找什麼?》去到各大影展,時常有人把他當戀愛顧問,問他交友 app 生態或是如何應對,但其實他才是最困惑的人:「我就說,我真的不是感情的專家,就是因為我不是專家,我才拍了這部片。」集體而來的提問,讓他感受到一股願念:「我覺得大家都很想要答案。」

「國家級約會計畫」進行實況。

「國家級約會計畫」進行實況。
還未找到真正的解答之前,有關愛的線索,都可能是偽裝。周東彥以肉身拆閱龐大的、難以理解的愛,但無論紀錄片、徵婚行動作為線頭,卻似乎還無法觸及核心。從《你找什麼?》到「國家級約會計畫」,許多人反問他:周東彥,那你在找什麼?為什麼要做這個計畫?他僅能回答:「我要找的東西,感覺一直在改變。」答案如此開放,但唯一確定的是,他還在找答案的路上,還要繼續問下去。
「國家級約會計畫」中請參加者填寫基本問題及照片,試圖更看清楚,與一個人相遇的過程有哪些因素?但經歷一整天的 meet-up,周東彥的心得是:「文字並沒有比照片不膚淺,文字也可以是偽裝。」那天也有曾經閱讀文字時感受過共振的人前來,但真實相遇那一刻,卻感覺依然遙遠。
原來我們是一樣的
《你找什麼?》裡收錄一小段他在巴黎駐村的錄像作品《迷走地下計畫》。他在巴黎各個地鐵站吃法國麵包,遊走,不時與人邂逅。粗糙畫質裡,他吐露異鄉人的漂流心緒,說人在台北時聽法文會話,到了巴黎,卻是聽張惠妹、王菲⋯⋯當時有個觀眾在噗浪上分享這個作品並留下心得:「原來有人跟我想得一樣」。一直要到五年後,周東彥才意外遇見這則評論,他說:「我覺得,那就是做作品、創作最重要的事情。」
原來有人跟我想得一樣——一路走來,他像是在作品裡佈下寂寞的線索,等候回音。「我們常說,藝術是要提出問題、不是給予答案,這是真的。但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渴望被理解。」
我問他,介不介意我用孤獨串連他的作品核心?周東彥說不會,不過孤獨也隨著年紀轉化了。「以前孤獨這件事情就會三不五時出現在我的文字、proposal 或作品 synopsis 裡面。現在漸漸沒有了,但它還是不斷地在作品裡面擴散。」從前異鄉裡的失根經驗,到如今發聲被原先以為是同類的人們批評⋯⋯周東彥特別容易站在疏離的視角說自己的事,透過不同的形式變化,其實內核都是被理解的渴望。
甚至連拍婚紗照那天,他都很疏離。「沒有任何浪漫的想像,花啊,角度啊,都在想怎麼讓鏡頭拍比較順⋯⋯我是一個很抽離的人,非常跳出地在看所有事情。好比我覺得現場大家都比我感動,我自己,把感動放在好裡面喔。大概要三個月、兩年後,我才會把它拿出來感覺。分手的痛苦感,我也要延到大概一年。」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孤獨的藝術家這樣說。因為:孤獨是很多人可以共感的情緒。創作可以讓大家可以一起,即便是一起孤獨,那也很好。
寂寞的漫漫長河裡,他用創作理解人,接觸人:「我最近漸漸覺得,其實人是很不理解人的。所以我們透過藝術創作,來理解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兩部紀錄片《剩女,真的》《你找什麼?》也有許多異性戀者給予反饋:「他們會覺得,其實他的世界也是這樣。這個『找什麼』的不確定性、情感跟慾望的一個曖昧跟模糊地帶,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他甚至覺得感謝:「很謝謝大家願意這樣看它,也覺得很好,我們又做到了一點什麼。」
|
|
|
|
尋愛之路,幸好不只有困惑。因為創作,周東彥與世界也有了理解與被理解,孤獨與一起孤獨的可能。約會計劃那天,有位參加者因為膚色白皙,他隨口問對方有沒有擦防曬,對方說沒有,你可以摸摸看。周東彥觸碰了他的臉:「就覺得好有趣。我就請他也摸我的臉,然後在我們互相摸完之後,我覺得有一些⋯⋯我不會說是喜歡或者是怦然心動,甚至不是賀爾蒙,但是有一些東西,讓我覺得很好。」孤獨與孤獨,在他的作品裡相遇,至少讓彼此有了一點「很好」的感覺。
一個媽寶戀愛的可能
「⋯⋯真的是很開心的,讓有情人終成眷屬,不管他是什麼樣的性向。我覺得,人需要有愛。來這個世界上,要有各種的,比方父母的愛、兄弟姐妹的愛、朋友的愛、男女之間的愛,或是同志間男男女女的愛,這一些,不是讓我們活得更精彩嗎?活得更有意義嗎?這一點很重要。所以祝福,祝福天下的有情人。」——周媽媽
「國家級約會計畫」宣傳影片裡,周媽媽現身應援,說出 524 同婚法案通過後的祝福。周東彥有一點點小驕傲的樣子:「她怎麼這麼會講?」他描述母親的背景,這樣一個為生計拼好幾份工作、沒有念國高中、都以勞動工作為主的母親,還是基督教,集結了許多保守的元素,卻很懂得給予:「小時候我真的是什麼都想要學。除了鋼琴、小提琴這種比較常見的之外,還有一些比較獵奇的,捏麵人,還有演講、作文、寫書法。」他笑自己:「我沒有一件做得好的,基本上,我彈鋼琴我的手就是⋯⋯(講不下去)我竟然沒有這樣的自知之明!所以我現在就做劇場,她也非常支持我。」
同志路上,母親其實也曾驚訝抗拒。周東彥在大一時選擇和母親出櫃:「她沒有到超級 drama,但一定是驚訝、不能接受、很難過、責怪自己、稍微想要改變你或幫助你。」那是長年的拉鋸與進退。例如《你找什麼?》裡現身的義大利前男友來台灣玩時,周東彥很想介紹給她:「我想說沒問題我出櫃了!我可以跟我媽介紹我男朋友了,結果媽媽的驚嚇程度非常大。」起初母親說很忙,就不見面了吧,直到前男友最後一天要離開時。
已經十年了,周東彥還是記得很清楚細節:「我說我們要走了,她說你再等我一下。我媽就騎著摩托車,從木柵到鹹花生旁邊的那個 7-11。然後她就看著我的前男友,叫我跟他講些有的沒的,很高興看到你啊諸如此類的。然後,她就拿出了一條金項鍊,給他。」
「這是我媽媽的價值觀和感情觀,然後我媽媽覺得她支持她的小孩、她愛她的小孩,跟她小孩的另外一半的方法,所以就有這條金項鍊。每一次無意間跟別人分享這件事情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這媽媽真的太瘋狂了,這個愛太瘋狂了。」
嘴上說瘋狂,周東彥其實很理解媽媽的擔憂與行動:「她會擔心你,是因為她知道年老、她知道一個人的狀態,她接收到所有的資訊,就是覺得伴侶是重要的。」單身久了,他坦言不知道婚姻是什麼,但愛情、家庭、伴侶讓人如此心動:「『男同志一個人也可以有寶寶喔』的廣告之類的,有時候會感覺到那個吸引力。」講到想幫他介紹人了,他又打臉自己:「但我是一個連寵物也不敢養的人,我覺得我比較自私。」
採訪那天,我們重現招親場景,請他再穿一次西裝。走在往西服店的路上我們聊感情,他說自己基本上就是個媽寶,很難啦。我說應該也還好吧,總是會遇到有緣人。他立刻反問,難道你會和媽寶交往嗎?
我總覺得,其實不是媽寶不媽寶的問題。那麼多人報名前來,但他還在質疑自己因為太媽寶沒人要。找愛路上慣於孤獨,難免喪失豢養愛情的信心。他在計畫裡暴露自我,更像是寂寞邊緣的呼告,誰來愛我?周東彥在創作裡思考愛,理解愛,接近愛,脆弱地愛——或許這次,我們可以期待一齣美滿的通俗劇,主角帥氣說完台詞,真愛現身:
「就是因為危險的事情,所以你才要去做,不是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