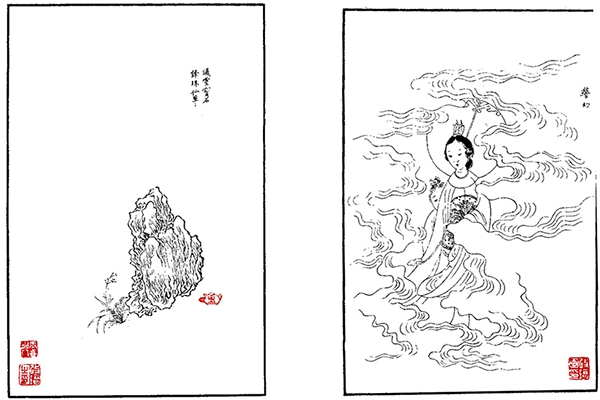夢與幻的救贖(一):
從《駭客任務》談起
「你是否曾作過那樣一種夢,那種你確信那就是真實的夢?如果你再也醒不過來呢?」
「什麼是真實?真實該怎麼定義?如果你指的是觸覺、嗅覺、味覺和視覺,那全是大腦接收的電子訊號。」──《駭客任務》
以六小時為度,人類終其一生約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在睡眠中度過。然而,無論腦神經科學、心理學等實驗科學作了多少努力,夢對於我們來說仍然如同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些夢中的種種經歷,它們的意義無法確知,它們的來源漶漫無稽,這種確確實實存在的生命形式是如此神祕而又切近,遂使「夢是什麼?」這個問題成為古今中外的一道「大哉問」。
.jpg)
不消說,人類對於世界的認識建立在一套信念之上,據此我們形成了一套感知、分類事物以建立秩序與世界觀,從而成為生活實踐的判準。沒有意外的話,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同意這一套信念可以被表述為「眼見為憑」。當然,這個立場背後的意義遠比表面上看起來的深遠,它其實意味著:我們可以運用邏輯與理性來整理感官接收的訊息,從而掌握真實與幻覺的分際;在邏輯的作用中,世界可以被我們以正確的方式認知。在這個「常識」的支持底下,那些不合邏輯、不符經驗法則的夢境,將被歸類為不真實的混亂心象,與真實世界之間有根本的不同。
然而,我們賴以進行認知的「邏輯」,作為這樣一種真假判斷的絕對基礎,是否無可置疑呢?如果邏輯提供了我們形成對於感官經驗的「表徵」(representation)所必須先行建立的概念系統,讓我們得以在理性的導引下以「概念」整理這些來自感官經驗的「電子訊號」,進而透過並列或從屬的判斷來安排事物在概念系統中的座標與相對關係,從而得以形成一個清晰的「世界觀」。那麼,我們其實是以概念及其具體形式──語言來建立一個可以被認知的世界,這就是為什麼有哲學家會說: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
.jpg)
我們活在語言/邏輯的世界中。有了這一層認識以後,或許這樣的提問便不算過分:邏輯等同於真實嗎?透過概念「表徵」(represent)出來的是世界本身嗎?如果世界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如果我們的感官經驗不必然得依照「邏輯」那樣地被整理,那麼這些「大腦接收的電子訊號」在不同的「表徵」引導之下,我們是否可以活在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之中呢?當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1999)中,莫菲斯(Morpheus)對尼歐(Neo)說,「真實」其實是「虛擬世界的投影」,「常識」是「電腦程式」的運作,而「我」也是這投影當中的一種「影像」,「世界」更只是一系列「代碼」的「模擬」時,背後的意義就在這裡。
人類以身心靈等生存載具逐漸形構而成的社會體制、倫理價值與世界圖像,形成了一個是非、真假判準的集合,從而形成文化與器物文明的立足點,「母體」(Matrix)就是這樣一種無所不包的強大宰制,它可以被視為人類意識用以「創造」更多的「表徵」以加強所投影出的「世界」真實性的根源,而活在其中的人們過著洋洋如常的日子,無非就像柏拉圖「洞穴譬喻」當中那些未曾見過光明的人們,「世界」已經成為一種「事實」,而不是「可能性」。相對的,當邏輯不再是唯一答案,感官與真實之間的鏈結有了不同的可能性,「母體」對於人的宰制就不再是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事情。這就是電影《駭客任務》原文片名 “Matrix” 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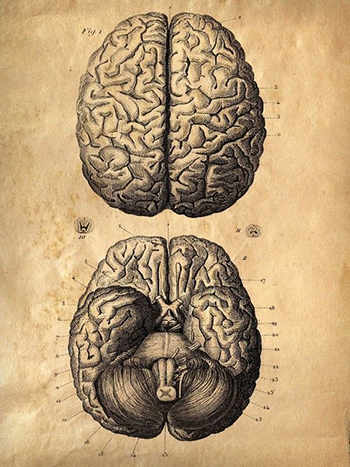
然而,擺脫「邏輯」思維的生活可能嗎?二十世紀上半葉,一位叫作列維-布留爾(Lucién Lévy-Brűhl,1857-1939)的社會學家,即透過大量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成果以及傳教士、航海員、博物學家以及旅行家所寫的民族誌等大量材料,考察了亞洲、非洲與中南美洲等原始部落的文化,得出一個重要的發現。他認為原始民族有著一種相當不同於邏輯思維的思考方式,在他們的世界中,事物不是以一個個確定的「概念」被劃分開來,而是被包融在一種「集體性」的「力量」之中。
布留爾把支配著這種思維的原則稱為「互滲律」,在其中人們經驗到的不是被「概念」表徵為界線清楚、不容模糊的個別事物,而是體驗著一種強大、具體、切身的「力量」穿透於不同存在事物之間。在「互滲律」的思維中,「邏輯」所在意的客觀性、同一性、不矛盾性並不重要或不存在,甚至因為沒有某物「是什麼」、「不是什麼」的觀念,所以「自我」並不存在。因此,建立在「主客對列」的基礎上進行的「認知」、「分析」、「抽象」、「分類」等心智功能,在原始部落是不可思議的褻瀆。在當時,人與物被聯繫在神祕力量的共生中,神話、巫術、宗教儀式與禁忌就是他們的真實,而「夢」也被他們視為實際的知覺,和清醒時的知覺別無二致。原始部落與歐洲白種人有著同樣的生理構造,卻發展出了不同的世界觀,我們不得不承認腦內「程式」投影虛擬世界的能力,其影響深遠。

正如我們無法證明「邏輯」與絕對真實之間的聯繫,我們其實也無法以進化論的立場把原始思維合理地視為一種落後的、未充分發展的初級心智表現。更何況,當邏輯思維當道的當代社會中,人類的心靈仍有許多實驗科學無法解釋的現象與需求,我們便不得不鬆動「邏輯」的世界觀,用更開闊的眼光來審視「夢」的意義。「夢」正如感官接收的「電子訊號」一樣,它是一種經驗的發生,而我們該以哪一套「程式」來解讀由夢而來的「電子訊號」,答案從來不只一個。因此,我們也不妨將「夢」視為我們經驗世界、認識世界、詮釋世界的一種生命形式,它是我們能夠對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作出思考的基礎之一,因而從夢當中,我們可以碰觸到世界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落。
事實上,中國向來被視為夢文化的泱泱大國,從百代浪漫文學之祖的《莊子》,到集小說美學之大成的《紅樓夢》,「夢」不但是一把劃破人生之虛幻並揭示理想世界的哲理之劍,更是文學家用以渲染愛戀愁長、掀起情節波瀾的妙筆。在進入現代化啟蒙的短短兩三百年前,在那相對漫長的幾千年中,中國對於「夢」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因此,對於夢幻與現實的分際以及理想世界的烏托邦該從何尋找,這些亙古以來不絕於響的話題,我們也不妨回到古人所體現的另一個世界,透過另一種常識窺探「夢」的意義,以領略一番不同的思考風景。
基於以上的原因,本專題將首先以《莊子》當中的幾個「夢」切入,循線耙梳中國哲理中透過「夢」以建構的真/幻思辨,並從中呈現古代哲人對於生命安頓、超越虛幻以進入真實世界所提出的構想;其次,則由基本上以「夢」為全書骨幹的《紅樓夢》這部承接夢文化傳統的顛峰之作,呈現文學家對於情欲、生命與真實的想像,看看在文學家的筆下,人們如何超越「母體」奴役從而進入真實世界。
參考書目|列維.布留爾著,丁由譯:《原始思維》,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