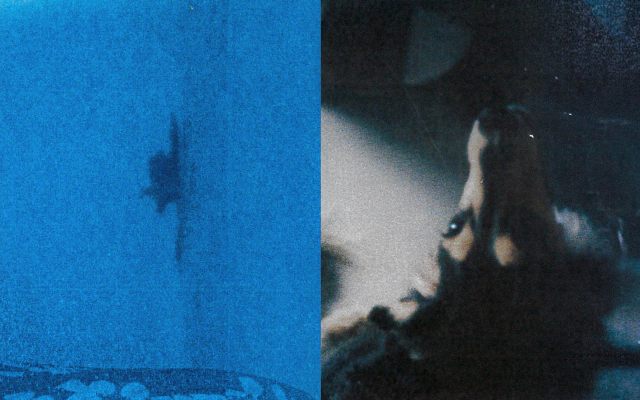長江燒不完這餘燼|醜陋的雪
我一直在用自己不喜歡的字,追求養活自己的食糧,吃著讓我忘卻回憶的米,走上鋪著白樺樹的路。夜晚時,這裡沒有歸屬於悲傷者的一畝影子,悲傷在街燈下顯得廉價,因為佔據高樓閃爍的都是奮力咆哮的金錢和歡笑。仔細聽,有聲音,是他們用所流逝每一時刻存在的生命正一齊奮力大叫:「成功!成功!成功!」
入冬。
上海某一天據說下了雪,也就是已經過去的某一天,哪一天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當天我正好待在家沒出門,聽說是下在浦東一帶。住浦東的人信誓旦旦跟我說:「真的是雪啊。」我家在靜安(一個離浦東很遠的地方)屋子陽台外面下方,綿延的街道種植的不是上海典型常見的白樺樹,是那種看上去很青翠,十分有朝氣的樹。如果是白樺樹,雪落在上面想必更蒼涼。
這幾天倒是下了幾次雨,這我是有記憶的。只不過我有點想不起雨的味道。上海的雨不像台灣的雨,還沒下,你就聞到空氣中飽和的潮味,彷彿海浪一般。我懷念海浪。
記得去年上海下雪時,我正要拿到一份新工作。我與 CEO 在一家中國典型很莫名其妙的茶館還茶餐廳還是根本沒有茶這個字的某種餐廳裡,也就是類似台灣的泡沫紅茶店。裡頭,什麼都有賣:牛肉麵、蓋澆飯、各種飯、小火鍋、義大利麵、各種麵(廚師到底是誰啊)、滷味、各種茶飲、酒、王老吉,甚至還有提供紅牛。(其實這裡我應該不能用「甚至」敘述,因為大陸只要是中式料理且不是特別高級的餐廳幾乎都有賣紅牛。我真的不懂這些餐廳與外賣到處充斥著紅牛兜售的概念是什麼,是太害怕人睡著嗎?)桌上擺了幾個骰子,用罩子罩起。桌子玻璃下壓著菜單,桌面有點黏膩,沒擦乾淨。
CEO 是個很「接地氣」的人,大陸用語意思即是具備草根習性,同時也不會高高在上地端架子。他總是周遊列國談生意,常一下飛機,行李一拖,就風風火火跑去見客戶,也不會追求非得去米其林餐廳。我記得當天的客戶因為也很草根,我們老闆也願意草根,於是大家就草根在一起,來到一個草根百分百的餐廳。談生意,也順便跟我談我的新職位。
我出去打了一個電話,看見竟然下起雪。
我在電話中雀躍地邊叫:「下雪了,下雪了」像個孩子。
雪從天上紛紛飄了下來,落在外面很醜陋的擋雨板上,落在很醜陋的餐廳後門出口。這些都很醜陋。上海很多地方富麗堂皇,一個比一個高級,但不美。雪是無辜的,但下在上海也不美。在我心裡,那天的雪還是醜的。只是那天晚上,有一個更強大、美麗的東西額外存在那裡,那力量蓋過了一切,使我忘卻了醜陋。那是不可置疑的美。

我害怕今年目睹上海的雪,我希望下雪時,我最好正待在家。如果不幸我人在外面,我誠心希望當雪落下來時,我會覺得自己是幸福的。正如過去某一段歲月裡,我深知他人的死亡、他人的關懷、他人的不幸、他人的眼淚、他人的幸福、他人生命中的每一抉擇,都與我有著關係。正是我確信這些都與我有關係的時刻,我就是幸福的。這就是我幸福的時刻。
我希望下一次下雪時,
我在很醜陋的街道上,再也聽不到入夜高樓上的咆哮。我希望看到最失敗最失意最頹喪的人,像個馬戲團小丑或唐吉訶德裡某個滑稽卻注定睿智的勇者一樣出現在所有人眼前,我希望我會深深惦記著他。
我希望我依然會惦記著他,並給予他身為一個人該得到的尊嚴與關懷,與上海緩緩飄落醜陋的雪一起。
【長江燒不完這餘燼】
關於上海,有時關於倫敦,但其實多數我只想寫台北。
那些小公園裡閃閃爍爍像是童年被你丟在身後的陽光、夏日燙了發亮的水泥路、半夜咖啡館裡溫暖繚繞的香煙與蒼白殘破不堪牆面,還有吉他聲堆起的音牆,比永恆還早一步佔據了我。在每一個城市的時候,我想的都是台北。
好啦但這專欄還是關於上海。
【廖乙臻】
曾任報紙與電視記者,後赴英國 UCL 攻讀碩士。在倫敦經歷一場火災把所有資產都燒成灰燼包括一個剛買的限量 Prada 包,組織過一場革命叫別人在冰天雪地中躺著為了體現行為藝術,現在上海工作。
追求自由,真正的自由。追求無懼,無所畏懼。其餘的,只是在對存在的質疑與對未來蒼茫的仰望中,
期待面朝大海,春暖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