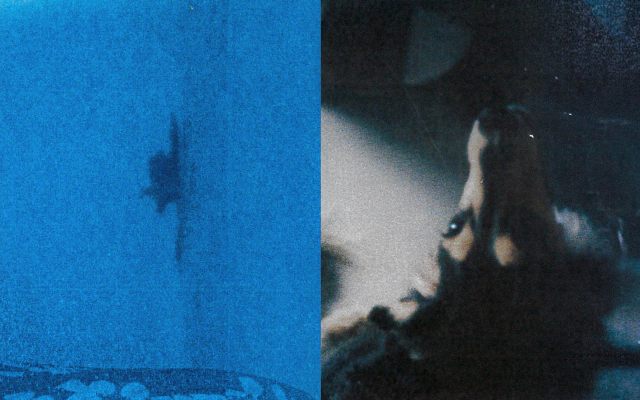長江燒不完這餘燼|那天晚上,倫敦對我們承諾幸福的月光
我正蜷在床裡用電腦,邊放歌。時間已經非常晚了,將近凌晨四點。我反覆放著同一首歌,這首歌彷彿把我與過去某個哀傷柔軟的東西像麵包與奶油般融到一起。
總是在一天的這時刻,我跟夜晚、跟世界,達到最溫柔的彼此理解。
我想到那夜的倫敦街頭,那是好幾個當下感覺平凡回想卻蘊含無比神祕難解訊息的倫敦幾百夜晚其中之一夜。我們踏著前方鬼魅般的影子,走在號稱治安最差的地段之一 Elephant Castle。我與幾個朋友去某朋友家煮火鍋,朋友是個性情溫和的蘇州男兒,對藝術電影熱情著迷,身材魁武,雙眼卻不知為何總是水汪汪地,講話時如同某種小鹿或是柴犬的小動物,眼睛閃著水,也閃著光。
我不斷嘲笑著 Elephant Castle,開著一些關於這區域有多可怕多慘澹的玩笑。他走在我旁邊,面對我摻雜人生攻擊的針對性幽默言語,我看得出來,他是真心真誠地感到快樂。透過他的應答反應,我很確信有些辭意他並不了解,但我幽默的氣場與對氣氛營造天賦般的掌握,還是強勢地超越一切語言所構起的短暫屏障。他不時靦腆笑,不時哈哈笑。我記得那晚的月光純白,沒被任何擔憂與猜忌遮掩,大方地純潔地灑在每人視線裡灑在每人對未來的期盼裡,彷彿在釋放一個安詳平穩的承諾,承諾每一個人永遠都會好好活著。
這樣的月光,如童年的鄰家玩伴,如兒時的清風,也如回憶中冬天溫熱的一碗湯,不會帶來任何災厄。然而邏輯上是,科學上是,本質上是,真理上也是——災厄是現實,是人生,是生命無法迴避的一部分,比月光還強大。
.jpg)
這位名校電影系畢業的同學,我的好朋友,他爸爸去年因為大陸整肅貪腐被政治鬥爭牽連,關了入獄,將在牢裡待上紮紮實實的十年。
去年我剛到上海,他在北京工作,被生活折磨著,正好來上海出差。他熱情地邀約我見面。他眼裡還是閃著光,只是多了一陣哭過後的滄桑,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家裡的事。酒後,他主動對我提起這件事,語氣平平淡淡。那晚我們去了一家不怎樣的新疆餐館,連大盤雞都不是熱的,我卻對那一晚毫不突出的雞味道印象深刻,那味道彷彿還黏在我舌頭上拔不下來。我朋友坐在我身旁,坐在一個小凳子上,承受命運的重。隔壁一桌死白痴客人大聲喧嘩,渾然不知這桌我朋友的命運,以及我正在對命運的見證。
當下,我與我朋友之間的連結,就是那隻難吃的雞,以及我們盡力死命去抓著不放使其不受現實摧毀的,記憶中在倫敦那一晚我們所踏上的道路,以及預示美好未來的月光。
我想到他的臉,他每次聽到什麼好玩的事,都會立即如孩子般笑開,笑容在他臉上像漣漪一樣化開來。我想到他的父親,儘管我不認識,也沒見過。我想到他每次去監獄裡探望他父親的時刻,他必須穿過長長的陰暗走廊,陽光自然是不被允許的,靈魂也死在那。我想到他揣測著接下來看到父親憔悴臉龐的表情⋯⋯他眼睛裡還會閃著水,閃著光嗎?
歌曲還在進行,同一首歌,我沒換,因為我不想停止想起他,我想把這些保留。
保留他眼睛裡永遠閃著的可愛的光,那是一種對於人性所信賴的光。
我想保留誰也奪不走的那晚倫敦街道上
短暫屬於我們的
永恆屬於我們的
對我們承諾幸福的
純白月光。
【長江燒不完這餘燼】
關於上海,有時關於倫敦,但其實多數我只想寫台北。
那些小公園裡閃閃爍爍像是童年被你丟在身後的陽光、夏日燙了發亮的水泥路、半夜咖啡館裡溫暖繚繞的香煙與蒼白殘破不堪牆面,還有吉他聲堆起的音牆,比永恆還早一步佔據了我。在每一個城市的時候,我想的都是台北。
好啦但這專欄還是關於上海。
【廖乙臻】
當過報紙與電視記者,在倫敦經歷一場火災把所有資產都燒成灰燼包括一個剛買的限量 Prada 包,組織過一場革命叫別人在冰天雪地中躺著為了體現行為藝術,現在上海工作。
追求自由,真正的自由。追求無懼,無所畏懼。其餘的,只是在對存在的質疑與對未來蒼茫的仰望中,
期待面朝大海,春暖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