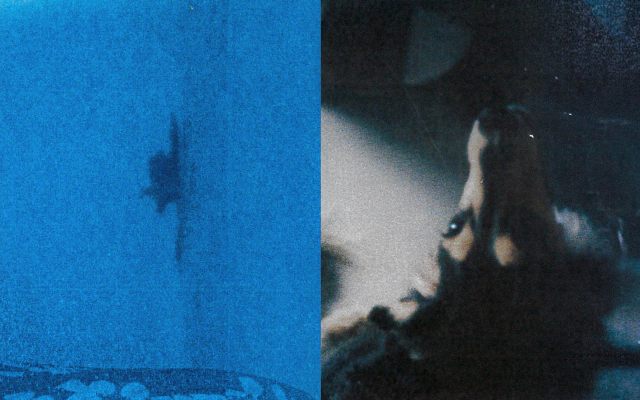長江燒不完這餘燼|我還是會愛你
沒有什麼佔有欲,沒有什麼切割不下的必須抉擇心理,就這樣活著。你不需大聲叫喊,不必流淚,就這樣活著。今天開始,早晨給自己煎一顆蛋,晚上聽一首簡單的歌,就這樣活著。
從一個城市走進另一城市,睡在看不見的星子底下,醒在不知名的白天,與記憶中的自己相互對抗,就這樣活著。
我希望就這樣活著。
在上海的時候,很容易生厭。為什麼?首先,先不論這裡物價不合理的高、生活品質不合理的兩極化、競爭激烈到讓你噁心、貧富差距血淋淋地放無比巨大在你面前提醒你想要好生活嗎就給老子掏出錢來⋯⋯以及,在夜上海風華絕代絢麗至極男男女女都梳著油頭用鮮豔的紅唇對你笑在香檳比水還要貼近你生活之迷醉金錢的化身之地—人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其中幾人如黃昏時一陣曾給你溫柔寬慰但已不復留存的餘香清風;在酒杯中,你談著你賺多少客戶是誰而誰又可以給你什麼利益沒——
你如何清晰分辨,自己究竟在哪?你又到底是誰?
上海生活可以被濃縮成以下:「這些事兒呢我都會,我畢竟是呢 Berkeley 畢業的嘛,這間公司專不專業我瞧一眼就知道了!」「那個什麼台的領導誰誰誰嘛,我跟他很熟,我們在何時何地還一起吃過飯!」「那個誰誰誰是富二代,那個誰誰誰又是官二代,那個誰誰誰替馬雲開過車,開過車就很了不起了好嗎是馬雲耶!」「沒有高大上我不要啊,高大上高大上!」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不是所謂社會集體定義的富二代官二代,你說話時無法立即讓眾人知道你身價有個千萬幾億或是你認識馬雲范冰冰李冰冰高圓圓還是什麼台的領導什麼公司的 CEO,你穿的不是 Prada 也不是 Chanel(就算是假的也好,但要假的很真)那麼,
你就等著吃屎吧,退場吧,回到你老祖宗的家鄉吧管他是哪裡。
港澳台來的?加十分。說流利英語?加二十分。歐美名校畢業?加三十分。白人臉?加五十分。白人臉但腦殘?沒關係還是加四十八分。家裡超有錢?喔你不用在這裡跟我們比賽你可以直接晉級了,sorry keep you waiting。
在這些粗暴不堪裡面,在這些每日真實扎進你皮膚的競賽裡面,你眼看著菁英、投機份子與身著畢挺西裝的人類在裡面翻來覆去,眼睛發著光燃著火,手拿長槍刀劍,吼著自己的生命意義必定是要死在這裡,帶著鈔票覆蓋他的屍體。
你也拿著長槍,甚至你也殺死過不少人了,你卻感到無助。
那感覺彷彿是,在熊烈長江的想像之下,也許一個偉大的帝國正在崛起,對於這些,你卻只希冀一條寧靜的河流。
我曾經幻想自己被喚醒,從一個遙遠的夢中醒來。醒在溼漉漉的空氣裡,醒在師大小公園斑斕的顏色,醒在豆漿店旁邊的公車站牌,醒在咖啡店破舊的書本與吉他溫暖的音色中,
醒在台北。
我每日行走,想著要吃什麼,工作,然後一天就過去。我每天也許愛過、無動於衷過、恐懼害怕過,也起身抵抗過強加我身上無論是什麼不屬於我的一切。我明白,我所流失的每一個現在,都用冷漠、卻又不時強烈重擊你的方式,在未來返現。人生可以是一場騙局,特別是在上海的人生。
但就算是騙我吧,
我想,
我還是會愛你。
溫柔地愛你,
細膩地愛你,
義無反顧地愛你。
在總是模糊閃現的陽光裡、在永遠被大樓擋住的月亮下、在擦身而過匆匆行走流動不已的影子裡。我會像一首卑微的詩,像一個夜晚開在腳邊的白花,像一個記憶中夏天迫不及待灑到身上的浪花,在忽明忽滅令人不安的遠方,靜靜地愛你。
如同我愛生命中每一個當時誤以為黑暗,實則是溫柔的光明日子。
上海。
【長江燒不完這餘燼】
關於上海,有時關於倫敦,但其實多數我只想寫台北。
那些小公園裡閃閃爍爍像是童年被你丟在身後的陽光、夏日燙了發亮的水泥路、半夜咖啡館裡溫暖繚繞的香煙與蒼白殘破不堪牆面,還有吉他聲堆起的音牆,比永恆還早一步佔據了我。在每一個城市的時候,我想的都是台北。
好啦但這專欄還是關於上海。
【廖乙臻】
當過報紙與電視記者,在倫敦經歷一場火災把所有資產都燒成灰燼包括一個剛買的限量 Prada 包,組織過一場革命叫別人在冰天雪地中躺著為了體現行為藝術,現在上海工作。
追求自由,真正的自由。追求無懼,無所畏懼。其餘的,只是在對存在的質疑與對未來蒼茫的仰望中,
期待面朝大海,春暖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