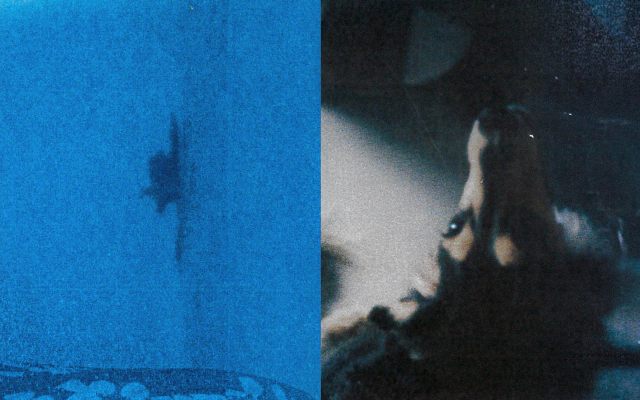獻給地獄廚房的情書|廚房生存之道(一)薄切生牛肉 Carpaccio
透早的廚房有種煙硝過後,濃霧漸開,晨起的露珠落入土地的清新感。火爐一個個被重新點起,煮麵鍋嘩啦嘩啦注入清水,那聲音總讓我想起午後的泳池。
大夥兒帶著淺淺的睡意,以王者檢視屬地的姿態,仔細清點各自工作檯的狀況,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早上的地鐵狀況,一邊比對前一天值班同事留下來的待做事項紙條。這樣的清閒對廚房的一天來說是非常難得的,因為直到你發現前晚值班同事只替你留下一份烤茄子,或是兩份薄切牛肉而陷入恐慌前,每天都是新的開始。主廚通常不會一大清早就出現在廚房,所以你能趁機跟同事們打打屁,喜歡狐假虎威卻又愛跟人稱兄道弟的副主廚,這時往往會放任你們適度的嬉鬧。
我將切成 0.8 公分的圓茄一片片鋪平在烤盤上,撒上鹽、胡椒、橄欖油與新鮮百里香,將它們送進烤箱後,開始煩惱我的薄切生牛肉,這是餐廳的暢銷品,一場 40 人訂位的午餐,至少要準備 15 份備用,而它切片擺盤又特別耗時,在出餐前你可以沒準備好炸櫛瓜、可以沒把沙拉醬汁調完,若是沒有備好生牛肉,就跟帶一把無法上膛的槍上戰場一樣穩死無疑。
負責主菜區的資深同事在一塊塊肥美的牛肉送到後,會親自將牛肉分切,將漂亮的菲力送到我手上,我先將它扎實地用保鮮膜捆成圓筒狀,再送入冷凍庫中,待它確實凍透,才能用那台切片機切成 1 釐米左右的薄片,之後再小心翼翼將薄嫩的生牛肉鋪在盤上。這種專業的切肉機是很多義大利餐廳或家庭的必備品,它的精準無情成了我這廚房裡的唐吉軻德最大的風車敵人,在跟它混交情時,曾讓我血流如注,西西里島來的強路卡把我扯到一邊,秀給我看他多年前被切肉機劃過的傷口:「被這麼傷過一次妳就一輩子都不會忘了。」繼續接手我的工作。
廚房工作是這樣的,不管私下你有多討厭一個人,工作時你們都是一條船上的戰友,任何一個崗位有人落後(或陣亡),整艘船就注定沉沒。在桌數精簡的高級餐廳工作,70 人的晚餐就如驚滔駭浪襲擊,每個環節與人員都必須依照節奏穩定前行,這代表著 mise en place(備料)必須確實在出餐前完成,出餐時才不用被未完成的醬汁、未切丁的番茄拖了腳步。在客人點單被那該死的機器緩緩吐出、主廚唸出:兩份主廚沙拉、三份薄切生牛肉、燉茄子、老帕瑪森起士燉飯、燉牛頰後(然後你還不能請他大老爺重複),你要直覺地將該用的盤子、配料一一拿出,該炸的放油鍋,該烤的入烤箱,問問負責主菜的同事大概幾分鐘後能出菜,一邊還要仔細聽新的點單,以及主廚不時的催促:「快!茄子放烤箱沒?起士有放夠嗎?還要多久?」「五分鐘,Chef!」而即使你已自身難保,分不清到底還要再做幾份焗烤茄子、炸鍋裡的櫛瓜眼看要炸過頭了,看到麵區同事因為早上剛做好的麵餃用完而淪陷時,也不得不幫他跑腿去主冰箱拿材料。
「妳知道在廚房裡誰是妳最好的朋友?」尼爾問我。下午兩點半,敵軍氣勢漸緩,我們總算有時間喝水喘口氣。他指指我們手上的燙傷,抓起我掛在腰間的布說,「廚房裡最好的朋友就是這塊布,只有它能保護我們免於燙傷,妳知道怎麼善用它,廚房的活就能成一半。」尼爾跟大部分廚房的夥伴一樣,十幾歲開始進廚房當學徒,賺了錢就到別的國家廚房去遊歷,年紀輕輕就身懷絕技,他們有著歐洲青年那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性格,胡鬧起來誰都攔不住,幹起活來則比誰都拼命。在冗長又極度濃縮的工作養成下,每個人都有著自成一格的生存守則,只要你不太討人厭,他們都會用各自的方式教你各方面的事。
廚房裡兩個大型烤箱,必須應付麵包、甜點到熬高湯的大骨,大夥兒總得依需求緩急,互相協調用烤箱順序。那時我還菜得很,急需用烤箱時怯生生不敢跟前輩討來用,強路卡性子急,把我的烤盤一托就領著我找前輩說:「這笨傢伙不知道你要用高溫,不小心把烤箱溫度調低了,你這不急,先借她用 20 分鐘吧?」回頭對我說:「要裝傻、裝迷糊,假裝妳錯了,壓低姿態,別人以為妳傻,很多事情就過了,妳時常笑臉嘻嘻,這是妳的優勢,善用它。」
「但這裡,」他敲敲我的腦袋,說:「要比誰都清醒。」
【獻給地獄廚房的情書】
憑著對美食的熱愛前往歐洲學廚藝,從此掉入萬劫不復深淵。廚師這行原來跟美好生活毫無關係,比較像是一場意志力與體力的考驗,「不是瘋子當不了 廚師」,在一天 18 小時超時工作累積身心各種傷痕後,一次順利的出餐便能喚回骨子裡躁動的成就感,繼續甘之如飴在廚房中揮灑血汗。
【Yen】
前電影編輯、公關。因產生燉肉比煮字有趣的錯覺,到義大利學廚藝後,轉戰倫敦成為菜鳥廚師。在髒話滿天的義大利餐廳、米其林地獄廚房及英國電視 名廚餐廳皆留下足跡。飽受各種震撼教育後,從問好程度的義大利文,到在充滿義大利人的廚房中用義文帶菜鳥出餐。早已放棄用各式妙方淡化燒燙傷痕,仍把鑽研 最愛的義大 利菜視為第一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