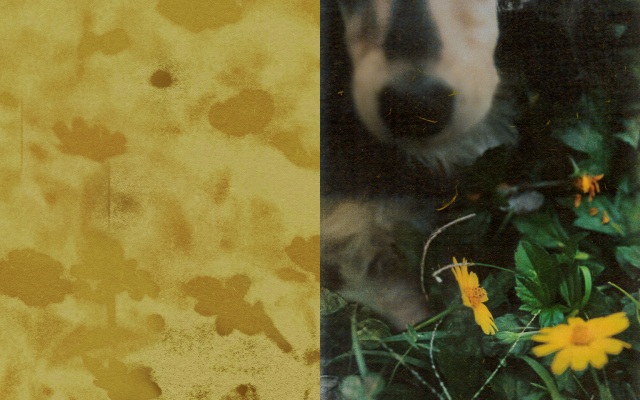早洩的塵世樂園|幼女
我是一名幼女,我是說,我曾是一位幼女。我現在的年齡,怎麼樣都不能說是年幼了,而我也相信我並不畏懼年老,然而,我的激情、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場情事,確實是在我年幼時,還穿著國小黑白相間的制服裙時發生的。
這樣的開場白很老套嗎?是不是有點像那句話:「在我的人生中,很快就太遲了。」但其實,我覺得我現在還算年輕,就是一個普通的接近三十歲的女子。我過了好一段日子,一直到二十歲左右,才重新回憶、「正視」我那段年幼地陷入恐怖的愛的時光;在那之前,我被迫分離,穿上新的藍色制服裙,我的精神進入不一樣的世界,我好像被迫害般地遺忘過往曾是那樣用盡生命地愛著,又好像一個受到重大打擊而自願忘卻舊情的小女孩──總之,我是那樣遺忘了。
她把自己比喻為釣手,Angler,這個字有個美好的音韻,那麼,我就姑且稱她為安格樂。安格樂,她是我的釣手,捕捉的是什麼,我就不必明說了。
一個國小六年級的女生自然不會認識 Angler 這個單字,這是我二十歲時幫她取的名字。我讀了一首詩,一首美好的詩,詩人將自己比喻為釣手,所以我將她取名安格樂。對,抱歉,我說了謊,安格樂沒有將自己比喻為釣手,這單純只是我為她取的名字。
我猶豫了一段時光於要不要促成這「女性的書寫」,終究還是寫了。我已經想不太起來究竟是什麼時候學會用中指自慰、又是到什麼時候才真的在其中得到愉悅。莫約是國小升國中時,那時候我知道安格樂已習於自慰,她偶爾和我分享她如何使自己舒服,而我總是困擾又愛惜地聽著。最初我仍隔著內褲不斷摩擦,因為當時好像還無法順利分泌液體,隔著內褲比較舒適,過了一陣子,才能順心地脫下內褲直接用手指接觸。
用中指,其實只是因為最順手舒服。用中指,按壓陰蒂至濕潤。在我年幼時,幾乎不渴望將什麼東西放入體內,只著迷於刺激陰蒂。也許是恐懼、也許是本能,陰蒂高潮已使年幼的我歡愉快樂,即使也仍有空虛無聊時。國中結束,進入高中,讀小說與寫作的渴望越來越強大,我大概也開始減少刺激陰蒂的次數,不像以往常在書桌前、或偶爾興起全裸躺在冰冷地上看著鏡子自慰,反而像個百無聊賴的人乖乖地在睡前溫暖的床上,彷彿只為了舒壓似地按摩陰蒂得到小小的普通的高潮,什麼也不想地進入睡眠。
安格樂從未直接示範給我看她如何自慰,她似乎暗示過她可以這麼做,但都被我迴避拒絕了。以當時我投注在她身上的龐大精神,若真的看到她這麼做可能會加速崩毀,我必須在每個上課鈴聲響起前,以及在午餐一同吃便當短暫的聊天之間,在眾多女孩之間求得她對我的一點點愛意,我才有辦法呼吸和思考,繼續每一天無聊的生活。
她當然是美麗的,即使因為她偶爾怪異的言行而使她不是班上男孩子最愛慕的女孩,課堂間也總能聽見她有點刺耳詭異的笑聲,與男孩 A 或 B 調笑著。事實上,我不想再這樣試圖描寫安格樂,若無法忠實呈現我與她度過的那樣熱情恐怖的時光,我寧可不再贅述。
在我與安格樂短暫的最為親密的那一年,國小六年級,我們當然都還不是與男性有所經驗的女性,或者說,都不是「嘗過男人滋味的女人」。安格樂確實一直想突破,她愛戀班上一位黝黑俊秀的男孩子,但同時也引誘生活中的年長男性,她曾被一位圖書館男義工變臉似地破口大罵,那不可置信之臉想來也令人有點不可置信,似乎從未看過擁有情慾的 12 歲少女。安格樂仍輕浮地笑著離開,貌似不以為意男人的惡言。那時,我記得我忍不住狠狠白了那個男人一眼,我認定那男人為生活中的怪物,比安格樂醜陋的怪物。
但男人不都是怪物。即使據我所知安格樂在國小畢業前仍保有她的貞美和純潔,仍是一位活潑大方,令我心動喜愛的正慢慢要轉變為女人的女孩──會在等我上廁所時,輕輕靠在牆上哼著流行歌曲的女孩。
※※※
安格樂是會吃人的,她有吃人的意念。她總是叫我陪她玩很多奇怪的遊戲,但我總半途而廢,只有她能堅持下去。她曾經試圖控制自己的呼吸,想要改變自己呼吸的頻率,當然最後只是弄得自己無時無刻不在意自己的呼吸。一旦開始意識到這樣本是無意識的舉動,就無法擺脫「原來我無時無刻不在呼吸」的念頭。她開始害怕,怕自己不再呼吸、怕自己一直在呼吸。她因為這樣和學校保健室的校醫聊過好多次,當然只能叫她多讀書、運動,讓她「真正投入」生活中,以去除她腦中奇怪的念頭。
寫到這裡,我也不禁呼吸急促;不只是因為我也再度意識到我在呼吸,還因為另一件事。抱歉,我又說謊了──我就是覺得有什麼不太對勁,就忍不住扯謊。
我的生活裡從來沒有安格樂。我是有過一兩個曾經親密分享瑣事、傳紙條傳簡訊的女孩密友,但沒過多久,我們就因分班、離校等正常原因不再那樣親密,像一般的女孩子。老實說,我也沒有太過想念她們,我實在太無聊了,才虛構出這樣一個通俗劇中致命的蘿莉女孩。
在我的生活中,我甚少和女孩分享身體秘聞,這方面我甚至是有點閉俗的,當然也沒和哪個女孩一起洗過澡。我的身體與情慾慢慢地發展,像一顆普通的植物朝向陽性雄性的那方,晚熟而遲緩地迷戀男體,在我孤好的世界中滿足於少少而安靜的性。
開始覺得前面敘述的故事現在看來,怎麼看都像一場「謊言」嗎?開始覺得疲累沒耐性了嗎?
用中指自慰對「安格樂」來說,可能是像彈鋼琴那樣投注情慾地優美;對我來說,有時樂於沉醉於各種不同情節、不同觀看角度的性幻想之中,有時只是粗魯地情緒發洩。有一種說法是小女孩在學會以刺激陰蒂得到高潮後,逐漸成年卻又要從與男人性交中學習「陰道高潮」,易使女性得「歇斯底里」症。網路文章仍不乏這樣的標題:「妳一生應該有一次這樣的高潮」、「神秘的 ABCDEFG 點」,我感到混亂,不只是因為不知道自己身體哪部分可以得到愉悅,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男人也不知道。因為不知道,我曾經覺得羞恥,或許曾有不少女人也覺得羞恥。安格樂不是我,我寫下她,但她不是我;那麼,我是「我」嗎?我現在還是前一個故事中的「我」嗎?
我想我曾有過一段時期有性交恐懼或大量渴望性,如今,性可能已對我不具那樣特殊意義,而轉為另一種能量。
我曾擁有很多愉快的性,也曾擁有很少;我曾快樂地自慰,我寫字,我發覺「原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性」。世界被性建築,被一劃為二;而今,二是不是太少,還是根本太多,樂園內外的人不論結伴或獨一,都是那樣踽踽而行。
我想起我曾聽過一個「放棄性的男人」的故事,在我真的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放棄性,一如沈迷性,有可能是相同的孤獨,追逐解放。放棄性,放棄的可能是經驗,他說,你渴望經驗嗎?我說,我為經驗而活。他送了我一顆蘋果,我笑著離開了。
※「在我的人生中,很快就太遲了。」出自莒哈絲《情人》。
下一篇:國王的兒子
【羔子】
台北人。喜歡從男孩的視角來寫,也寫女、慾望、生活。
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lamblin.no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