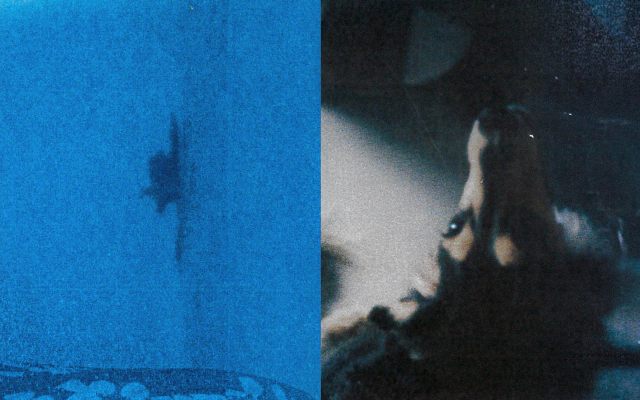對話|凝視真實——評《正宗哥吉拉》
庵野秀明的《正宗哥吉拉》(《シン・ゴジラ》)之所以受到重視,不僅因為其在設定、製作上全面回歸哥吉拉原始的設定與初衷,更在影像、及各種元素的使用間,展現出這部電影獨特的美學、與價值態度。
電影對政府體系、國防單位、官僚機制以及兵器使用的考察,做到了鉅細彌遺、且盡可能擬真的地步,包括自衛隊的使用時機、以及美軍單位的介入;過程中拍攝出逾 40 種具象徵性及代表性的武器。與將這些設定與物件簡單地視為電影「吸睛」的手法,不如在敘事方法上做出更複雜的解讀:這是為了將巨大災難壓進現實感知裡,最有效、且最直接的方式。不同於過去的哥吉拉電影,《正宗哥吉拉》的時空捨棄原初的五零年代設定,直接轉移到觀眾身處的當代。在經歷逾半世紀的時間後,哥吉拉象徵的核能、以及自然問題,因為福島核災等新事件讓人更有反思與共鳴的空間。

電影前半因減少對於哥吉拉本體的刻畫所營造出神秘感,並不是庵野秀明的專利。同樣的手法,在 1954 年初版的《哥吉拉》就已經被妥善運用過。然而讓人無法不注意的是,2016 年的《正宗哥吉拉》在怪獸畫面減少後,取而代之不斷出的,是大同小異的室內空間。這些不斷轉換的會議、對話場景,僅有周遭的擺設可讓人稍微做出區隔,整體而言,空間的性質大同小異,容易造成疲憊與混亂。而若仔細回想整部電影,則會發現,過程中這些場景都沒有被「出入」的畫面。我們只看見一間間複製品般的房間、與狹窄通道並列。沒有出口。
在這樣的設計下,「建築物」儼然成為另一頭隱身在電影裡的怪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不斷穿梭、遷徙其中。這是現代文明所形塑出的空間怪物。大衛.哈維在《資本的空間》一書中曾提到:現代文明與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地理景觀——也就是都市建築物本身——在創造資本與價值的同時,也一併禁錮了人類活動,創造出更多的不自由。這是電影壓迫、窒息感主要的來源,人類以自身文明戕害自身的現象。兩者相提並論下,大衛.哈維的分析成為解讀《正宗哥吉拉》空間景觀的最佳註解。每座城市成為自己打造的克里特島,所有人困在自己所生產的迷宮裡,當有一天災難來臨,原本相安無事的隱憂便一一浮現、崩解與放大。
如果維繫現實的真實性,以凸顯批判、反思的力道,是庵野秀明施力的重點,那麼哥吉拉在電影中特寫畫面之少,便是在維繫整部電影「觀看災難」的角度與現實生活的我們盡可能相同的手段。電影並沒有因為「災難」的作品定位而創造一個「神的視角」,美化、或遠觀災難,相反地,大多數拍攝視角都來自「事發現場」。從預告片開始,當觀眾有機會近距離看見哥吉拉,便幾乎都是攻擊、逃難的場景,在中距離的武器攻擊中偶爾可以窺見哥吉拉全身的樣貌。簡而言之,沒有「微觀」災難來理解災難的機會。這點跟現實中的我們是一樣的。無論作為當事人或第三者,我們都仍找不到最適當的方法來切片與呈現災難,其中牽涉包括倫理、以及形式上的問題。這也是報導文學不斷面臨的困境。二〇一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在她的作品《車諾比的悲鳴》中試圖透過拼貼當地聲音,來還原出災難的本質。艱辛的過程與其發散的形式,揭露出大多時候,我們其實對災難一無所知。
因此,在這樣的限制下,電影留給我們的並不是哥吉拉的特寫,而是大量第一人稱的攻擊畫面。而攻擊本身,也是期盼的意思。這也是電影為什麼能在缺少怪獸畫面的條件下,堆疊出另一種巨大悲傷的緣故。大量攻擊,等同大量的期盼。電影在前半段一度動用文學方法加強、深化對哥吉拉本質的詮釋,美國特使對主角說:「Godzilla 在字源上,原來是『神』的意思。」因此,當電影後半再度出動槍砲、直升機攻擊哥吉拉、以求生存時,這則現代寓言便更加深了它的荒涼、警世、與恐怖感。
.jpg)
.jpg)
全片僅有三次跳脫「現實視角」,顯露出敘事者「上帝」姿態的片段。其中兩次是電影畫面出現近似「圖章」的手法;而另一次,則是哥吉拉展開史詩破壞的那夜。在敘事過程中,電影兩度出現圖、文以印章的方式直接覆蓋在故事時空上的場景,首先是官員們討論災難應變的方法時,螢幕突然佈滿法律條文的畫面;再來是學者理解、分析哥吉拉組成的過程中,螢幕所出現的動態生物結構圖。比較這兩幕在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難看出庵野秀明對於兩種理解途徑給出評價:前者是故事停滯、挫敗的片段,後者則是故事開始出現曙光的轉折。規範永遠大於理解,是導演以判官的姿態,對故事時空所蓋下的戳記。
而唯一一次,哥吉拉不再透過任何角色、兵器視野來進行特寫,是牠大行原子吐息、破壞全城的夜晚。那是電影唯一一次「詩化」了這場災難。如果要有一幅具代表性的圖像來代表一切,那就是庵野秀明心中災難的全貌。也只有在那樣的夜晚,以及其他攻擊進行的畫面裡,希望、與絕望交織,電影才會有配樂。因為現實是繁瑣、沈悶,只能倚賴偶發的幽默感來化解時間重量的過程。因此,導演在平靜的對話裡盡情地展現諷刺,在大型的場面調度裡節制地抒情,透過這種方式,盡可能從畫面與時空設定上承載最多現實,這也是《正宗哥吉拉》勝過其他哥吉拉系列、與好萊塢災難片的原因。它不只要是一部電影,它同時要是一座經過嚴密考察、推算的現實模型——無論在設定、以及敘事手法的意義上皆然。
.jpg)
【對話】
作品、現實、個人、與理論間,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動。對核心概念強的作品進行精讀、對核心概念弱的作品進行偏讀,並視為特定文化現象詮釋,可以加深不同場域間的關係。此為本專欄寫作之目的,也做為作者自身創作理想方向的追尋路途。
【張敦智】
「Frank 是對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顆星星。一顆代表自己誠實的星星。我們花了一輩子在黑夜中想抓住它,但是他一旦熄滅,就永遠不再閃亮了。我不認為他會跑多遠。他大概只是想自己一個人,看著他的星星熄滅。」──Arthur Miller《All My Sons》。
希望我的星星可以燒久一點。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1993 年生,天蠍座,台中人。